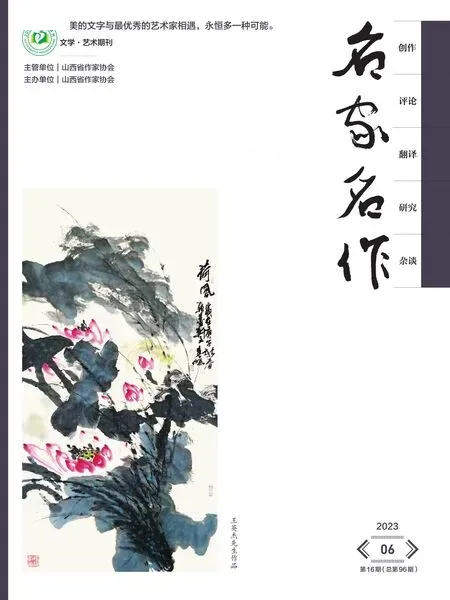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社会学探因
张斌斌
“邺下文人集团”之“邺”,即邺城,在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汉末属冀州,袁绍为冀州牧时曾治于此。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攻占邺城,邺城从此成为曹魏的重要根据地。依据现存史料,对“邺下文人集团”的恰当定位大约是:以邺城为主要活动地点,以曹操为创始者和领袖,以曹丕、曹植兄弟为实际组织者和核心,以“七子”为骨干,包含众多文人作家的文学集团。正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集团。
其时,“邺下文人集团”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其贵游生活与文学创作日益热烈繁荣,使中国文学在质朴刚健、慷慨激昂的“建安风骨”外同时呈现出“诗赋欲丽”的审美追求。
究其成因,这与文人自身的天赋与才华密不可分,更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借助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特殊的时代环境与士风学风则是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一、宽松多元的时代环境
(一)社会经济
汉末是个大动乱的年代。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交替专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以一批士人官僚为主体的“清流”集团的结党抗争,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党人的集体奋争使得原本已日趋衰落的汉室更加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接踵而至的便是军阀混战,导致社会残破、民不聊生。
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攻占邺城,自领冀州牧;建安十八年(213 年),立为魏公,定府为邺。后来曹操相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在曹魏统治区内,逐渐呈现较为平和繁荣的局面。
曹操在《蠲河北租赋令》中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命令免除河北当年的租赋。随后的《抑兼并令》要求“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他改革租赋制度,抑制豪强兼并;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大兴屯田,扶持小农。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人民暂时安定下来,战乱时的萧条局面得已缓解,经济上也渐有起色。
再以人口为例。中国人口从东汉桓帝到献帝时期曾急剧下降,而在三国前期却又由减少而趋于稳定,魏、蜀、吴三国均如此。这当然与三国逐渐分立、战乱减少、经济发展有关。三国时期,邺城作为曹氏的政治、经济重镇,人口颇众。曹操在《选举令》中提到“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确实如此。一者,这是曹操的改革措施使然;再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曹魏也需要将周边地区的人民逐渐迁往心腹地区如邺城、洛阳、关中等地,以便统治和管辖。据《三国志》所载,梁习任并州刺史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李典也曾“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杜袭“任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时,“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至于邺城本身,则发展得相当繁华。“古代邺城在漳水南岸。战国时,邺城就以魏国西门豹和史起引漳水灌溉田地,促进农业生产而著名”[1]。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开始精心规划修建邺城,城市布局初具规模[2]。《水经注·浊漳水》中载,“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城中为一条大道,通往东西城门。道北为宫城,包括宫殿、官署区及贵族居住区;道南为外城,是手工业、商业区及平民区。文昌殿为主殿,其东为听政殿,其西为铜雀园(即西园),园中有荷花池,园西有三台,“中曰铜雀台”“南则金虎台”“北曰冰井台”。邺城以西有玄武苑,苑中有玄武池,系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为训练水军而辟,“有渔梁、钓台、竹木灌丛”(《水经注·洹水》)。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曾详细描绘了当时邺城的盛况。由上可见,其时的邺城,街道林立,市井繁荣,手工业、商业活动都很发达。
作为曹魏集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邺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优美的亭台楼阁水榭,为日后邺下文人的贵游生活和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二)思想文化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3]随着统治政权的摇摇欲坠,儒学的正统地位也一步步动摇、削弱,最终丧失了其独处一尊的地位。
首先,汉魏时,地域的不同导致文化教育状况和文化意识上的差异,这是曹魏文学兴盛的大文化前提。其时,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教育较为发达,官学、私学都相对繁荣。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五月,曹操“作泮宫”,“泮宫”即相当于太学。地处北方的曹魏一直活动于汉室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的主体是从东汉晚期以京洛为中心的迅速变化的文化中发展出来的”[4],故文化意识相对开放活跃。而南方地区包括西南、江东等地则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故地处边远的东吴、西蜀两国,在思想文化上就较为保守。
曹魏文化意识的开放带来了其变今从古的治学方向。在曹魏,古文经学日兴,而今文学派渐趋衰落。许多曹魏文士均尚古文经学,如刘桢习《毛诗》、李典习《左氏春秋》、苏林“多通古今字指”。再如曹操,他年轻时曾因堂妹夫被诛而免官,而两年后却“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
士人学子一旦从烦琐之学中解脱,其思想文化上的解放和兴盛势必加剧,亦可能以更实用、更进步的文化姿态进行艺术创造乃至文学创作。这或是曹魏文学“彬彬之盛”局面的有力注脚之一。再者,古文学家大都博学多览,这也为他们驱才骋词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次,东汉在思想上“虽以经学为统治思想”,但“各种在野、甚至外来的学说,一直比较活跃”,“士人的思想也呈现多元的色彩”[5]。儒学的崩塌、其他学说的崛起,尤其是神仙说、道家、道教思想的流行,为士子文人逐渐建立起新的人生模式,也为儒家教义里一向处于附属地位的文学摆脱政教而走向独立提供了前提。如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张衡亦儒道兼修,蔡邕在《释诲》中也流露出崇尚黄老、神仙的倾向。
再说曹操,虽然其思想杂糅多家,但其主体和底蕴仍不出传统儒学范畴。纵如此,身处这样一个道家、道教、神仙说等种种学说思想蔓延的社会人文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除了在政治行为中以黄老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外,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中,曹氏家庭成员亦表现出追求真率自然的精神风貌。这一现象,可视为黄老‘无形无名’学说在人生哲学方面的表现——不拘一格,自然而然”[6]。或许可以这样说,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在思想渊源上主要沿袭儒家精神;而道家的自然逍遥之旨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人生行为、文艺态度和处世哲学,他们在整体上是矛盾的共同体。
同时,儒学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失去信服和影响力,其文艺思想和理论也会同时被质疑和推翻。如《后汉书》载,仲长统公然表示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儒家教义的崩溃和毁灭可见一斑。试想,若没有两汉儒道的此消彼长,或许就不会出现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邺下文人集团”重才使情的文学创作,“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未必会在曹魏时期到来。
二、任诞重才的士风、学风
世风必然影响士风。在汉魏特殊思想文化的氛围下,士人群体形成了一种崇尚个性、任诞重才的士风与学风,以惊世骇俗之言和有悖常俗之行开魏晋风度之先声。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任性纵情、通脱放达的行为风貌既获得了自身生命和心灵的解放,又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单就文学层面上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能文博艺
汉魏文士普遍注重包括文学在内个人多种技艺的掌握和艺术才情的培养。如,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孔融“性好学,博涉多该览”,等等。
至于曹操,据《三国志》载,青年时期,便曾“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后来在南征北战的军戎生涯中,他也是“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文学之外,曹操在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亦颇富才华。“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操现存二十二首诗歌全为乐府,这离不开其对音乐的热爱和精擅。此外,曹操亦看重诸子的文学才华,如他曾送五枚宝刀与诸子,“先以一与五官将(曹丕)”,并称“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百辟刀令》)。
曹丕亦不输乃父,文学、骑马、射猎、击剑、游戏(如弹棋)样样精通。而被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更是自小聪慧,“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以才见异”“几为太子者数矣”。“七子”如王粲、阮瑀等人亦博学多才,其他如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人,“亦有文采”。
(二)竞技逞才
东汉时,重才之风已露端倪。范晔《后汉书》首创《文苑传》,传有东汉文学名士二十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意识为文人所立的本传。建安年间,曹氏集团的领导者一向重视文学乃至文化、教育事业。如曹操“唯才是举”,曹丕三番五次地称赞“七子”“于学无所遗”,对于多才多艺的邯郸淳,他与曹植争相拉拢。人才愈加被重视,个人的才性、才气、才能也愈加被看重。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文以气为主”,从侧面也反映出曹丕对文人之才性、才气的重视。曹魏时,还出现了以品鉴人物才性为要旨的理论著作,这就是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从人物外在的言语、形貌等方面,对人物的才能与性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和探讨。可以说,《人物志》的出现既是汉代人物评论的产物,又反映了汉末学术的重才风尚。
在日常创作上,邺下文人颇为重视个人的写作才能。他们经常以书信方式相互品评、修改文章,进行文学交流。如曹丕的《与王朗书》《又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与吴质书》《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等,均可见他们在信中与友人进行文学上的交流。此外,陈琳、吴质、卞兰等人在与曹丕、曹植二人的书信中也常表示出歆羡称美之意。
“魏晋南北朝之士常以才地自矜。”[7]文学创作日渐繁荣,负才任性之士甚众,“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一时,竞技逞才、展示个人才华在文人中间蔚成风气。
例如,建安十七年(212 年)春,“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操命丕、植兄弟二人各作《登台赋》,实为有意测试二者才华之举动。而曹丕、曹植为争太子位,竞相拉拢文才之士以为羽翼,便也是在暗中较量各自集团的文学才华和力量,进而在政治上以分伯仲。再如“七子”之一的陈琳,虽长于章表但不擅辞赋,却常自称能与赋家司马相如媲美,被曹植讥为“画虎不成反为狗”(曹植《与杨德祖书》)。
建安时期,赠答诗作以及命题创作与同题共作之风颇为热烈,现存邺下文人的赠答诗和同题诗赋尤其是咏物赋、公宴诗甚多。“逞词使才的色彩很重,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8]
综上所述,经历了大动乱之后,在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一群怀珠抱玉之士从四方齐聚邺城,他们有着超绝的文学才能,怀抱建功立业的个人理想,一边欢宴达旦,一边洒笔酣歌,用空前的热情和辞采创造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