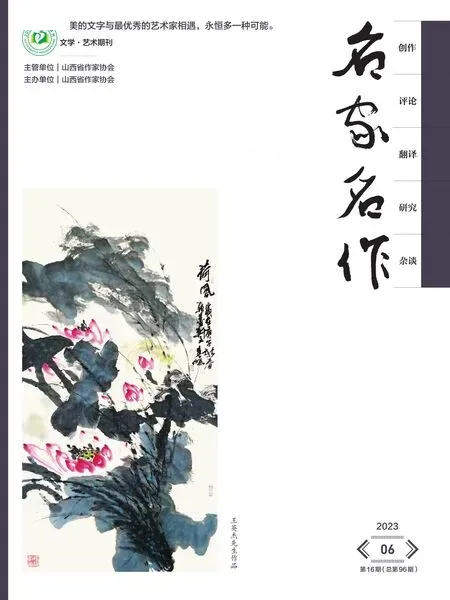空间理论视域下保罗·奥斯特《4321》的叙事探微
陈 超 李代丽
自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问世以来,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爱德华·索贾等国外学者在文化空间上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叙事学研究也经历了一场空间转向。国内学者诸如程锡麟、龙迪勇、王安等对此做过相应探讨,尤其是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从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结构与类型、叙事作品的空间书写、图像叙事的类型等多个维度做了系统分析,为国内空间叙事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读者的空间心理及奥斯特的空间书写两个维度探讨《4321》的空间意义。
一、读者的空间心理建构
奥斯特热衷于非连贯叙事,致力于将毫无关联的时刻拼凑在一起,试图累积成一个“类似故事或者超越了故事的东西”。因而,奥斯特十分重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与合作,他鼓励读者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并引导读者经由复杂的文本,主动建构具有独立意义的阅读空间。《4321》分为七章,每章由2~5 节构成,“1.0”是四个弗格森人生的起点:弗格森的祖父远渡重洋到达纽约,直到1947 年3 月16 日斯坦利与露丝的儿子阿奇·弗格森出生。从“1.1”开始,讲述了平行世界中的弗格森1 号、2 号、3 号、4 号在偶然性的主导下,走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奥斯特将弗格森所处的时局比作五个同心圆,弗格森处于“同心圆”的中心,借弗格森的四重人生表达了对自我、他者、时代、国家的思考,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了人在偶然性和可能世界中的存在。
小说分别用了七章叙述弗格森1 号及弗格森4 号,而弗格森2 号仅用了两章,弗格森3 号则用了六章。具体如下:
弗格森1 号:1.1—2.1—3.1—4.1—5.1—6.1—7.1
弗格森2 号:1.2—2.2
弗格森3 号:1.3—2.3—3.3—4.3—5.1—6.3弗格森4 号:1.4—2.4—3.4—4.4—5.4—6.4—7.4
对于读者“创作”的看重可视为奥斯特在读者维度对于空间书写的探索。在奥斯特的小说中,读者常常能“按图索骥”成为其迷宫般叙事文本的解密者。《4321》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创作空间,读者需要自觉进行空间阅读,将碎片化的情节重新组织为清晰的叙事逻辑,从字里行间还原奥斯特的空间书写意图。在完成“1.0”的阅读后,读者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方式:同时阅读弗格森的四重人生,如1.1—1.2—1.3—1.4,以此类推,由于情节的相似和主题的同构,读者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在头脑中将每重人生对应;第二种方式:分别阅读每个弗格森的人生,如1.1—2.1—3.1—4.1—5.1—6.1—7.1,以此类推。无论何种阅读方式,弗格森的四重人生皆可成为独立完整的故事:弗格森1 号家庭拮据,但父母感情甚笃,其顺利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名记者的同时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法国诗人作品选》,24 岁时因楼下邻居引发火灾不幸殒命;弗格森2 号的父亲在“三兄弟家世界”烧毁后经营南山网球中心,母亲则经营玫瑰园照相馆,初具写作才华的弗格森2 号成为《石子路改革报》的创刊人和发行人,却在13 岁参加夏令营时被大树砸死;弗格森3 号的父亲因参与大伯烧毁“三兄弟家世界”骗保计划而被烧死,母亲成为职业摄影师,弗格森3 号是一位热爱写作的双性恋者,完成了自传体小说《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31 岁时死于伦敦因浓雾导致的交通事故;弗格森4 号家境富裕,但父母感情破裂,极具文学才华的他陆续写下《脚底的伴侣》《马利根游记》《猩红笔记本》《废墟之都》《绪言集》等作品,并宣称在《4321》中虚构了三个不同的自己,加上弗格森4 号虚构版的自己,成为“四个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的人”。
文本脱离叙述者进入文本的阐释视域后,追逐文本意义的任务便交付给读者,读者在反复阅读中重构了文本的意义。奥斯特的空间书写中潜藏着其对于读者空间阅读的鼓励,在《4321》的章节内容安排上,已经体现出奥斯特在读者层面考虑文本空间形式的努力,并强调读者并非从细节层面对一部空间形式作品进行理解,而是通过反复阅读在抽象层面进行理解,正如约瑟夫·弗兰克认为,作者“不是鼓励读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人,而是鼓励读者体验由小说人物之间以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创造的一种形式——比如一个正方形或一座迷宫——的人类精神,与那些特殊的人物发生认同”①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78-179 页。。具有空间叙事特征的小说强调读者的空间阅读,即文本经由读者的解读、回溯、整合而成为具有独特的空间形式的小说。奥斯特正是在此基础上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文本的空间意识,而读者做出何种阅读的选择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读者心理空间建构也具有多种可能性。
二、分形叙事下的空间效果
具有“空间形式”的小说往往不重视文本线性序列,而注重文本的同在性,文本“按照某种空间关系组合成一个抽象的、虚幻的就像‘宫殿’‘剧场’‘圆圈’那样的‘形象建筑物’”②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356 页。。龙迪勇曾将分形叙事视为空间叙事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行探讨,他认为,在分形叙事类文本中,事件与事件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序列的因果联系,事件在某个关节点上叙事的线条产生“分岔”:一种是作为“后果”的事件是由多个作为“前因”的事件或事件链条所导致;另一种是作为“前因”的事件可能导致多个“后果”事件或事件链条。③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215 页。《4321》正是一因多果式的分形叙事,并指向了一种“时间关系”,即一个“过去”与多个“现在”之间的关系。
分形叙事文本所叙述的事件往往是“共时性”的,奥斯特以弗格森的四重人生呈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4321》的叙事逻辑正是建立在人能够存在于平行世界中且能够同时进行两种以上的选择。正如弗格森2 号在6 岁时想象:“同一个男孩,住在不同的房子里,有一棵不同的树。同一个男孩,有不同的父母。同一个男孩,有相同的父母,但父母做的事和他们现在做的不一样……是的,一切都有可能,事情是这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④保罗·奥斯特:《4321》,九州出版社,2017,第51 页。在《4321》中,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但弗格森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弗格森在“分岔点”上所做的选择,每个选择都引导弗格森走向不相同的命运,甚至在某种选择之下继续呈现选择的多种可能。小说的第一次分岔是自弗格森出生,四个拥有同样DNA的弗格森在四条分岔的小径开启彼此独立又非截然不同的人生,随后在第一次分岔后呈现出进一步的分岔,如弗格森1 号的父母始终陪伴左右,17 岁时的车祸导致其失去两根手指,他被迫放弃了最爱的棒球,但也因此免去了兵役;弗格森2 号想“疯狂一把”的举动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弗格森3 号因同性恋身份而遭到辱骂、歧视,却因“既爱男人也爱女人”而免除兵役;弗格森4 号因好友阿提去世而放弃了棒球,却与阿提家人结缘,并受阿提的启发写出《脚底的伴侣》。分形叙事将复杂的世界简化,分形叙事文本中“分岔点”昭示着人生的无限可能性,这正与《4321》的叙述形式相契合,四个弗格森的人生完全处于偶然的“抉择”中,而偶然性中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分形叙事的基础上,《4321》采用了“中国套盒”的叙述结构,随着主层叙述的进行,故事得以延展。在“套盒”结构下,奥斯特一如既往地采用元小说模式,有意揭示小说写作的过程,并突出小说的文本属性。奥斯特借弗格森4 号之言表态:“我喜欢那种承认自己是故事的故事,而不是假装是真相,全部真相,只有真相,上帝作证。”⑤保罗·奥斯特:《4321》,九州出版社,2017,第474 页。由此小说呈现出犹如棱镜般的空间效果。
三、视觉书写下的空间特征
奥斯特的艺术创作横跨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等多个领域,其小说视觉书写体现在奥斯特对电影叙事、绘画艺术、摄影技巧的模仿上。
尽管小说叙事与电影叙事有诸多差异,但奥斯特热衷于将电影元素融入小说叙事文本中。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奥斯特热爱电影,将好电影视为“和最好的书一样好”,他笔下的人物也热爱电影,如弗格森1 号因车祸失去两根手指,在电影中寻求安慰;弗格森3 号从15 岁到17 岁发表了十几篇电影评论,写完书籍《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后,计划写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二是奥斯特小说中常常出现电影剧本,如,弗格森3 号与安迪看电影时插入了电影《敖德萨阶梯》的片段。三是奥斯特将“镜头意识”代入小说创作中,运用蒙太奇、分镜、快切、光影、色彩等镜头语言将文字视觉化。以蒙太奇为例,弗格森1 号想象着三个人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进行着三件事——波比·乔治说了我愿意,而弗格森伸出左手给一位美国军队的医生看了看,艾米则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永远地退出了这场运动,此外,奥斯特以九个分镜镜头的形式叙述了弗格森3 号的父亲去世前后发生的事情,以六个分镜镜头的形式展现了战争对弗格森4 号及周围人的影响。
《4321》中也存在对绘画艺术的模仿。如,小说叙述弗格森1 号从1966 年秋到1968 年6 月的经历时,写道:“如同脑海中的一幅油画,一些区域沐浴在一片强烈、明澈的光线中,另一些则淹没在阴暗里,形状模糊的人影站在画布蒙浑的褐色角落……画布上另外一个明亮的点……画中所有其余的光线,全部照在了艾米身上。”①保罗·奥斯特:《4321》,九州出版社,2017,第591-592 页。此外,《4321》的文本中有多次对摄影艺术的模仿,如,小说在叙述弗格森4 号对罗森布鲁姆夫妇的印象时以摄影手法“快照一”“快照二”的方式完成了文本的叙述。
作为一个对于视觉书写有自觉追求的作家,奥斯特将视觉艺术的叙事手法应用到小说的书写中,小说由此呈现出空间特征。
四、多重主题及文本互现下的空间意识
《4321》是奥斯特的又一篇实验之作,其空间形式也体现在多重主题的建构上。弗格森1 号关乎政治与历史、战争与反战、诗歌翻译等主题,弗格森2 号关乎写作才华、世界荒诞、人生不确定性等主题,弗格森3 号关乎宗教信仰、婚姻与家庭、同性恋、双性恋、摄影、运动、电影、音乐等主题,弗格森4 号关乎种族对抗、社会动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选择与责任”、写作实验等主题。尽管每个弗格森的人生轨迹不同,但偶然性中存在确定性,多重主题下暗含的是四个弗格森人生追求的目标所在,而四个弗格森的经历正是现代人的寓言。
掩盖在多重主题之下的是小说文本互现。弗格森的四重人生中,婚姻家庭、友情与爱情、种族对抗、战争与反战、死亡与存在、电影艺术、文学创作、偶然性、不确定、无限可能性等主题一再出现在两个及以上弗格森的人生中。譬如,在奥斯特的笔下,命运是由潜藏“必然”的“偶然”组成,人的存在也不是必然而是偶然,平行世界中的前三个弗格森是现实世界的弗格森4 号虚构的人物,弗格森4 号如同上帝一般操纵了弗格森1 号、2 号、3 号三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存在意义与死亡方式,这种文本形式的设置强调了人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偶然性。
《4321》中多重文本的互现不局限于主叙述层中,还包括主叙述层文本与次叙述层文本间的互现。如《4321》与弗格森4 号所写作品之间的互现:《格雷戈尔·弗兰姆的是一个人生时刻》与《4321》同构了世界由偶然性主宰的主题;《往右、往左,还是直直向前》与《4321》同构了选择与承担责任的主题;《马利根游记》与《4321》同构了对于写作实验的尝试;《废墟之都》是一部沉重而无情的小说,通过亨利·诺伊斯医生的故事展现了他生活在残破之国的荒诞,而弗格森所生活现实世界何尝不是如此;小说的最高叙述者宣称弗格森4 号所写的《猩红笔记本》是“一本关于一本书的书,一本读者可以阅读也可往里面写的书,一本就像三维实体空间一样可以进入的书,一本关于世界也关乎心灵的书,一个谜团……”②保罗·奥斯特:《4321》,九州出版社,2017,第698 页。。事实上,《4321》正是这样杂乱无章、毫无关联的碎片,也是一部可供读者进入“三维实体空间”的作品。通过《4321》的文本互现,读者既能深知文本的个中滋味,又能形成出位之思,向上向下还原作者的意图。
后经典叙事中叙事形式本身构成了叙事内容。在奥斯特的小说中,主题和内容是从形式技巧中演绎的内涵和意义,读者经由形式通达内容解读了小说的命题: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偶然性作为《4321》要表达的主题之一,不仅是情节“巧合”、多重主题和文本互现的重要体现,还是奥斯特窥测世界本质的手段。
五、结语
《4321》线索众多,情节破碎且交叉重叠,小说不断插入和并置弗格森所写的作品、翻译的诗歌、与家人的信件内容、历史事件、时政要闻、人物自由联想(弗格森1 号被困电梯长达7 页的意识流),从而使故事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由此,奥斯特将小说的过去、当下、未来杂糅,将情节置于真实与虚构之中,建构了小说文本的空间形式,也让文本意义呈现出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书中的世界栩栩如生地展开,被各种可能性、各种秘密和互相抵悟的状况搅得翻腾不息。书的中心内容无处不在,直到全书结束之前没法画成一个圆。”③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玻璃城、幽灵、闭锁的房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第8 页。奥斯特对悬疑小说的评价之语也适用于《4321》,不难发现,奥斯特在《4321》中进行着一以贯之的写作实验,以“偶然性”“可能性”“不确定性”建构笔下的逻辑世界,那些看似毫无联系的内容和毫无意义的形式中却潜藏着打开文本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