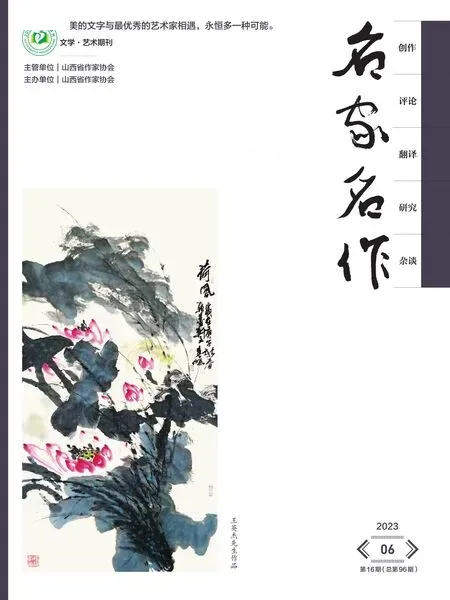原乡、故乡与家庭:《河上柏影》的故土观
井水明
《河上柏影》作为“山珍三部曲”之一,历来都被学界认为是生态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正因此,学界对其讨论也始终停留在生态文学的视域内。翻开《河上柏影》的前言我们不难发现,在表达生态的忧思之外,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也是作者阿来力图表现的重点。正如阿来在《河上柏影》前言中所强调的:“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的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河上柏影》以两代人的故土迁移为背景,对个体生命存在空间与灵魂栖息之所进行了深度表现,个体面对原乡与故乡双重缺位的那份踌躇与不安,是现代人共有的精神危机,生命要如何自救,灵魂又向何处归依,阿来用小小村庄一家人对精神原乡的重建给予答案。小说深刻揭示了个体对生命曾经或正存在于故土之中的那份复杂感情,同时又为现代人故乡缺位下精神危机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可能。小说虽以柏树为名,但其内核远非学界认为的生态美学指向这般简单,有关人的延伸才是其要旨所在。正如书中所说,“柏树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而是这个故事的尾声”。同时,以人为本的创作倾向也与阿来一直强调的“人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的文学创作观念不谋而合。
一、原乡之痛
“原乡”是指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由宗族文化与家族记忆共同建立起对先祖居住之地的认同。当代文坛早期的“原乡”书写颇具寻根意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贾平凹的《商州》小说,他们的小说不仅扎根于原乡的地域与文化,肆意描绘和缅怀故乡的风土人情,同时更饱含对自我根的追寻,颇具追寻精神原乡的意味。近代以来,“原乡”的概念不断扩大,诸多海外华人笔下的原乡指涉的范围也从过去指代自己宗族起源的故乡扩展到广泛的民族概念上。“原乡”包含的特定宗族血缘关系也转化为普遍的家国情怀。而余华的新作《文城》所指涉的原乡则更具精神原乡的意味,“文城”虽不存在,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永恒的精神“原乡”。所以,“原乡”的指涉范围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域与文化属性上的:人们对自己或祖先曾存在过的地理空间上的某种眷恋或思念的情感。二是精神属性的:人们对自己精神寄托之处的某种向往与眷恋之情。传统意义上的乡愁,人物经历的是身心错位的苦闷,换言之,人物面临的困境是有归宿但无法回归。《河上柏影》中人物的“原乡情结”则表现为一种不可得的原乡之痛,人物身处异乡与原乡分隔,其面临的不仅是无法回归的现实困顿,更是无乡可归的精神困境。
小说中,王泽周一家两代三口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原乡之痛。王父十几岁时为了给家人省下一点救命粮,跟着老木匠外出逃荒,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路做工乞讨,最后在这个深山中的村落中停留下来。三十年后,听闻母亲死讯的王木匠赶回了自己几十年间思念的原乡,却发现生养自己的故土并不能带给自己精神上的归依感,生命无所依附的感觉又催促他回到生活了三十年的藏族村寨,回到了相依为命的妻儿身边。血缘关系与宗族文化共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伴随着母亲的死亡而减弱,作为地域的原乡无法填补王木匠精神的空洞,唯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唯有妻儿才能重新治愈其心中的原乡之痛,并构建起新的精神原乡。王母虽为村寨的原住民,但被没收了祖屋,只能独自一人生活在破木板房里,同时还要面对村民的欺辱,直到她救起倒在羊圈里的王父,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可以抵御危险的家。当摘掉“地主”的帽子,可以搬回自己先辈居住过的宅院时,王母出人意料地选择拒绝,她继续和丈夫儿子住在这个破木板房里,憧憬着丈夫会为自己和儿子盖起一座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温暖小屋。血缘与宗族记忆建立起来的原乡情感随着族人的离去已被消耗殆尽,老宅早已不再是王母的心灵寄托之处,伴随着婚姻关系的缔结与家庭模式的确立,小屋取代了老宅,成为王母新的精神原乡,那个在漆黑夜里,一个人蜷缩在破屋角落思念老宅亲人的王母也变成了安然躺在小屋火堆旁的妻子与母亲。在父亲的指引下,王泽周与父亲一起回到了那个与自己有着血脉联系的原乡,当他从父亲怀中的信中得知,自己与母亲被血亲称为蛮妇、蛮子时,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原乡,他只在心里告诉自己“只把他送到村口,却半步也不会踏进这个村庄,也不会去见这个村子中那个把自己的家乡叫作‘蛮中’、把他的母亲叫作‘蛮妇’的家族的任何一个人”。王泽周与原乡的联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但不被原乡接受,这份血缘所产生的原乡依恋就会大打折扣,王泽周自然也无法单方面产生对原乡的归属与依附之感。
所以,原乡虽以血缘和宗族文化、记忆为基础,但主体对所谓“原乡”的认可与依恋才是原乡情结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当血缘与地缘因素弱化、文化与身份认同消减,原乡情结最终还是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能唤起原乡情结的社会关系已经消失,人们又在新的人际关系中建立起了又一个精神原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王泽周一家各自过去的原乡已经消失,三人又以家庭为单位建立起另一个原乡。与其说过去的原乡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解体而消失,倒不如说是伴随着新的家庭关系的确立而被重构。
二、故乡之梦
故乡的意义往往要在“离—归”的空间转换中才能得到凸显,故乡这一概念也往往在主体离去之后才被提及,无论是鲁迅的《故乡》还是余光中的《乡愁》,其对故乡的书写都建立在离去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远离故乡、距离感已然产生的基础上,作家才能宏观地描绘故乡的面貌,总结对故乡的感受。基于此,人物才能代表作家,言说对故乡的情感。与原乡不同,故乡对应的是一个确定的空间,同时夹杂着诸多零碎的记忆。王杰泓认为“‘家’‘乡’的概念首先对应于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物,人赖以居住并为其优化、完善而劳作。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超实体的精神性象征,是与母亲的皱纹、父亲的背影、童年的游戏、木屋前的溪流等一系列事物和行为相联系的灵魂栖居之所”(《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
因此,在失去故乡的感受中伴随的是空间的割裂与记忆消亡的危机,是过去某种稳定关系的打破。对王泽周一家而言,这个小小的村落无疑就是他们的故乡,王母与王泽周自不必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这一方村落既承载了他们人生的所有记忆,也是其唯一的存在空间。王父自少年离乡便一直生活在这一方村落,原乡的社会关系已然断绝,可被称为故乡的旧时村落也早已不能承担其灵魂栖居的功能,如今这小小的村落方才可能称为其真正的故乡。但作为故乡的村落,其合理性依旧存疑。费孝通认为,个体要确立其在村落中的归属,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村子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乡土中国》)。显然,王泽周一家在村中归属的合法性是存疑的,王母是原住民,但其一直作为村落中的边缘人而存在,在王木匠到来之前,独自生活的王母是一个“只要有人愿意就可以肆意轻薄”的边缘人,她不属于这个村子,也不被村落这个社会关系所接纳和保护。直到王木匠到来,他用锋利的工具保护起这个女人的尊严和作为人的权利。因此,王母并不属于这个村落社群,而只是徘徊在其外围的边缘人,作为其婚姻对象的王木匠自然也无法在这个村落中获得合法的身份。因此,王泽周一家只能算是寄居在这个村落社群中,而绝非存在。正如费孝通所言,“这些寄居在社区边缘的人物并不能说已经插入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信托”(《乡土中国》)。不被村落接纳的王泽周一家,显然无法建构起“属于”的身份认同,其对这一村落的故乡感受自然也存疑。
从文本来看,王泽周一家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生活的,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王泽周一家的生产模式是封闭的,他们既不与其所生活的村落社区发生关系,也不参与村落的日常活动。正如书中所言“他们一家像飘忽的影子”寄居在这个村子,与之相伴的是存在却不属于这里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文本中村落很少被提及,木屋成为一家存在空间的依托。当描述离乡的痛苦时,并未出现任何社会关系断裂的痛苦,对故乡的不舍也都寄托在一栋木屋之上。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王泽周一家或许并不存在什么故乡,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对故乡的依恋都收归于这一栋木屋,家庭成为他们社会关系的依托,是其故乡人际关系的全部,木屋则是其故乡的具体存在空间。
三、家庭之实
家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是一个充满感情的社会单元。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分为两类,一是大家庭,二是小家庭。当家庭的容量超出了夫妻、父子的范围,这个家庭就不能再称其为小家庭了。与之相对,小家庭则指家庭容量限定在夫妻、父子范围内的家庭。从这个层面来看,所谓大家庭,更接近我们惯常认为的“家族”概念。而家庭则倾向于现代家庭一般意义上的三口之家模式。本文关于家庭的论述也侧重于小家庭的范畴。
在小家庭模式中,存在三对关系,即由父、母、子构成的三角关系。夫妻通过契约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结构,子女则是这一基本结构建立之后的产物。在家庭关系中,所有家庭成员都应有归属同一集体的认同,这也是家庭这一社会单元得以稳固的基本条件。王泽周一家属于典型的小家庭模式。对一般家庭而言,家庭关系一旦建立,身份上的归属认同也随之形成,简言之,夫妻关系一旦确立,二者对归属于同一家庭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建立,子女对家庭的归属认同也是同理。与一般家庭不同,王泽周一家对归属于同一家庭的身份认同则要复杂得多。王父作为一个流浪汉被王母所救,随之与王母生活在一起。王母则患有精神疾病,在生活趋于平静之后才慢慢恢复正常。二者的婚姻关系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程序合理性与个体自觉性。二者最初的关系建立在恩与共生的基础上,一方面王母在王父生命垂危之际搭救了他的性命,王父则在暴徒的手中保护着王母;另一方面二人共同生活、互相扶持,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建立在恩与共生基础上的关系无疑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另外,二者婚姻关系的最终确立源自一种自觉的爱与责任。当王木匠回到原乡却找不到心灵归依之处时,他选择回到妻子与儿子身边。书中有一处细节,王木匠在计划回家后虽急切却没有径直回家,而是在村口的工地上打完短工方才回到家中,对王木匠而言,这一天的短工意味着重拾起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也正是对妻儿责任的重拾,才真正确立起自己与妻子的实际婚姻关系,直到王木匠离去而又归来之后,这个家庭才在一次分离的危机中被真正确立起来。作者虽未明说,但从文本的细节处我们不难看出端倪。在这次分离的危机之前,王泽周一家三个成员总是各自出现在作者的笔下。在小说对王母的前期表现中,王母总是与木屋旁边的五颗柏树绑定,作者着力塑造的是一个对柏树与宗教有着强烈执念的少数民族妇女,她整日都在重复着虔诚的祈祷,似乎现世的一切都与她无关。王木匠则总是在提到王母与王泽周之余被一笔带过。作为文本的主要人物,对王泽周的前期书写多为交代其身份与生长环境服务,对其双亲的描写也多是点到为止,但在这场分离的危机之后,作者一改先前孤立式的人物表现方式,每每表现人物关于自我归属的矛盾时,家庭的现实存在与家人命运的联结就频繁出现。王木匠重回家庭,文本出现了一家人的第一次同框书写,这场家庭被确立的“宴会”上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被作者第一次细致地描绘出来。木屋拆除时,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目睹独属于他们故乡的消亡。有关王泽周一家对家庭的真正确立,正是在这一次次家人之间的互动中于相携中被作者勾勒出来,而家庭的稳固性虽不靠重大危机的解决来表现,但绵长的温情却也足以支撑起对家的最终确立。
因此,王泽周一家三口的家庭关系虽缺乏一般家庭模式建立程序上的合法性,但却有着远超一般家庭结构的稳固性,其家庭内在的合法性也正是基于这种稳固。对夫妻而言,二者不仅满足传统意义上夫妻关系中“恩”与“爱”的最高要求,同时又包含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互助等诸多必要条件。也正是这种“超稳定”的家庭结构才能让每个成员在面临“原乡”与“故乡”缺失的时候,能够寻到让灵魂栖居的居所。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在之中”不仅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其更包含有“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存在与时间》)的意味。阿来在对王泽周一家三口对“原乡”与“故乡”认知的阐述中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血缘、地域与文化显然并未成为桎梏主体对自身归属判断的阻碍,面对“原乡”与“故乡”追寻的难题,三者不约而同地在家庭中寻得了答案。在对原乡与故乡的缺位中,家庭承担了二者让主体灵魂栖居的功能。正如阿来所言:“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动,风过时动。……人是动物,有风无风都可以自己行动。”(《河上柏影》)人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的能动性,人对归属的渴望与追寻从来都不应该被限定在某一概念之中,栖居灵魂的故土并非必须是“原乡”或“故乡”带给人无限温暖的家庭,也可作为灵魂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