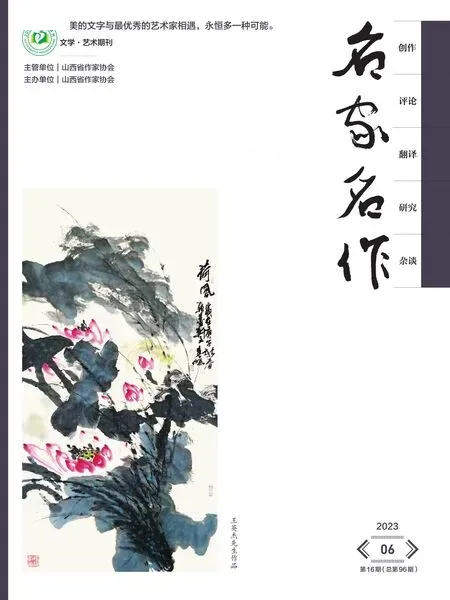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白蛇》中“徐群山”的性别操演和身份构建
阙诗惠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提出:“性别是一种行为,构建了他所意味的那种身份,而非只是先于它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再现。”[1]就此,巴特勒提出“性别操演理论”,认为性别是受人类社会规则下的话语权力作用而被规训的结果。身体被社会性别化后,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与表意符号,生理性别进而成为文化压迫的实现形式,成为文化形态形塑出来的意识产物[2]。
《白蛇》是严歌苓于2018 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通过细腻、戏剧的笔法,描写了20 世纪70 年代的两个女人徐群珊、孙丽坤在社会大环境下内心世界的压力和变化,以及在巨大社会压力下对生活的态度和选择。在社会环境和个人身世际遇的双重影响下,主人公徐群珊进行了两次性别置换,每一次转换都可以借助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解读。以此为出发点,文章重点分析了“徐群山”如何实现身份构建、性别规范,如何规训“徐群珊”致使其女性身份回归,并跳脱文本探讨此类贱斥者在重建主体意识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以期消解传统规范下的男女性别二元对立文化模式。
一、“徐群山”身份构建
《白蛇》中的徐群珊本为女性,自小随母亲长大,天生具有男性气质。在插队当知青时由于女性气质匮乏得以逃脱生产队男性群体的凝视,在用男性刻板的体力劳动换取不再被视为性资源的自由之后,徐群珊开始了探寻“超越性别二元对立”的初步尝试——穿上哥哥留给他的毛呢子军装。穿着军装的徐群珊被陌生人称呼为“大兄弟”,就此徐群珊开始思考“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3]作为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生理属性的他者,徐群珊的反叛意识在此刻彻底觉醒。
这种反叛主要体现在徐群珊的“易装”行为中。易装也称异装,是一个男女二元性别框架下的概念,指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在特定文化语境下通常与另一性别相关的打扮和行为模式,如男性选择偏女性气质的打扮,或女性选择偏男性气质的打扮等[4]。在《白蛇》民间版本和孙丽坤主观视角的不为人知版本中可以窥得徐群珊“易装”的一角。
在穿上军装后,板正的毛料和笔挺的走线遮住了徐群珊的女性线条,配合雌雄莫辨的短头发,“徐群山”变成了一个“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5]的正气“干崽”。徐群珊无法摆脱她生理属性带来的秀美,如雪白纤长的手指、漆黑油亮的美发,为此她在言行举止中加倍补充男性气质。比如把宽大的裤腿掖进牛皮短靴、用白眼珠子看人、语言干练不吝于和人起冲突,以及在自我介绍时称呼自己为“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通过外貌、言行举止各个层面的“易装”,徐群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让所有人彻底相信了他是一位中央特派的男性调查员。
一方面这可以作为性别操演理论的反向例证。世人认定徐群珊为男性时并不是认定他的生理自然属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观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男性气质”。就戏剧角度来说,性别的生成似乎更像是一种表演与扮装的表意行为。在巴特勒看来,当一个人被指称为是“一个女人”的时候,绝非是在描绘生理自然属性方面的事实,与之相反的是,这句话试图将“女性气质”带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场域中,使之成为一个戏剧中的表演角色,通过表演来展现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特质。[6]就此我们可以推断:通过表现性实践,一个人其实可以实现性别的流动,突破男女二元性别。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易装”其实正是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符号呈现。清秀属于女性,阳刚属于男性;长发属于女性,短发属于男性;谈情说爱属于女性,家国情怀属于男性。在表演过程中他者通过“易装”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相悖,来凸显非常态的异性特征。但这种异性特质其实也是在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建构的。进行“易装”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加深性别的刻板印象,对性别气质进行具象化。
巴特勒认为:“‘性别’是一种最终被强行物质化的理想建构。”她认为性别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意识形态创建的行为,为特定的目的与机制服务,是可以被改变和解构的,具有虚构的稳定性。在她看来,社会性别是重复行为的操演性结果。[7]《白蛇》中,徐群珊扮演男性的过程就从反面表现了女性主体在历史中的构成过程。女性性别刻板印象被父权制法则所支配,所呈现的是对她们所接受的约束性性别规范的操演。通过将美好品质赋予男性,女性形象自然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并在父权制文化中不断被刻板化弱化,最终导致女性主体的分裂与迷失。
二、“徐群珊”对性别规范的认同
文本中徐群珊由“易装”男子到异性恋妻子的回归过程是女同性恋群体努力寻找自我性别与身份建构而不得的时代悲剧,再现了男权中心文化之下男性主宰的社会制度对女性性别与命运的控制,充分体现男性社会话语权力下他者群体对性别规范的忧郁认同。
当“徐群山”的女性生理性别被识破,此前误以为“徐群山”是男性并已经深爱于他的孙丽坤陷入了精神错乱。为了获取正当理由前去陪伴孙丽坤,徐群珊初步改变了自己的外貌,丰神俊朗的男性“徐群山”让位给“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的女性徐群珊。
此时的徐群珊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精神内核,以女性的表现形式和孙丽坤继续交往,但是当孙丽坤第一次称呼她为“珊珊”时,徐群珊“渐渐变成了真正的珊珊了,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身上。她不再是个造作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她的爱抚和保护也纯粹是珊珊的。珊珊的嘴唇,比徐群山柔软、微妙、温暖。”徐群珊的身体在性别话语的视域中逐渐开始压抑性地进化与发展,此前模糊的“超越化自我性别”因受到话语权力控制而转向话语者期许的方向分化。
至此徐群珊回归了女性的身体认知,但社会普遍的异性恋霸权并不会放过她身上剩余的异性气质,尤其是同性恋倾向。当孙丽坤被平反,两人的恋情无疾而终,因为两个人都深知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同性恋”,哪怕是“双性恋”,都会因为和异性恋相悖而被视为“不正常”。为了躲避这种来自世俗的“不正常”判定,女性主动进入父权制社会规范建构好的性别身份,向主流的女性气质靠拢,认领一个安全的性别角色。实际上,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异性恋话语所产生的“规范”与“普遍性”的压力,孙丽坤和徐群珊都是因为无法承担这种压力,选择了屈从于规范,掩埋自己的真实欲望,进入异性恋婚姻之中。
巴特勒指出:“性别认同是一种抑郁心理。”性别认同是一种幻想与虚设。根据性别规范,那些“正常”的性别认同和行为得到肯定与自然化,那些 “不正常”的性别认同和行为得到惩处和污名化。《白蛇》中“徐群珊”的性别置换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女性性别认同的过程。父权、夫权致使女性屈从于男性,剥夺了女性真正的身份与主体性,而这些压迫更为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主流话语霸权。《白蛇》的文本中没有出现正面可视的男性角色,但是隐形的男权文化笼罩着整个社会,出于掠夺资源、巩固统治的需求,限制女性自由、遏止女性发展。
三、“贱斥者”重建主体意识
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贱斥者”(the abject)的概念:“‘贱斥者’指的是那些被驱逐出身体……被打成‘他者’之物。”“贱斥者”这一概念表示了一种身份在社会中被贬损或剥夺的状态。认可主体并强制将主体和贱斥者区分开来的是社会文化秩序。然而,性别操演总有缺陷和失败,主体只能接近于合乎性别规范。这样就肯定存在着不符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第三类人——反常者、另类、他者。[8]《白蛇》中的徐群珊就因为不符合性别规范而成为典型的“贱斥者”,这种第三性别超越了性别范畴向霸权提出挑战,重建主体意识。这种作用不只体现在贱斥者本人的认知体系构建上,更体现在对其他交往者的自我意识重建上。
文本中的孙丽坤自小修学于舞蹈学院,不知晓男女之事,不清楚个人性取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地和无数男人发生性关系,但并不记得“到底是谁先解的扣子”。直到遇到“徐群山”,孙丽坤沉寂的情欲、爱情彻底喷薄而出,她整夜温习“徐群山”触摸她的身体的丝绸感觉,“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1 颗纽扣”,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开始爱上珊珊,“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9]孙丽坤误以为“徐群山”是男性,但她爱上的都是“徐群山”未进行伪装的女性特质。可以说,孙丽坤的生命、身体与热切的情感都是因为徐群珊而被触发的。女同性恋之间的感情与性欲都是真实的,这种情绪并非是异性恋的错位,也不是女性有益的变体,而是像异性恋情欲一样,由身体引发的真实的渴望。经此一遭,孙立坤这位早已被社会性别规范长久规训的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彻底认识到女性能够拥有独立于男性之外的性欲和爱情,妇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而挑战男性的性特权,这对强制异性恋话语中单一的性欲观念起到了反驳的作用。
此外,在徐群珊结婚时,孙丽坤送给她一个充满暗示性的玉雕:白蛇和青蛇怒斥许仙。在《白蛇》一文中,孙丽坤是白蛇的扮演者,进行性别置换的徐群珊则扮演着青蛇的角色。表面看来,许仙指的是徐群珊此时的丈夫,然而更深层次上,许仙其实是男性中心地位的代表,是社会规范的代表。由此看来,这个玉雕其实是白蛇孙丽坤在和青蛇徐群珊一道怒斥许仙,一道怒斥男性中心地位,并做出最后的抗争。囿于时代限制她们无法成功消解男性中心地位的统治权力,去颠覆这个社会的规范,但这出悲剧因为两位参与者超前的意识而显出崇高,再一次展现出“贱斥者”对主体意识重建的巨大作用。
四、结语
“性别操演”理论一定程度上使性别呈现出流动状态,消解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度。《白蛇》中徐群珊这一角色的身份构建过程是性别操演理论的一大力证。在《白蛇》中,徐群珊经历了两次性别置换,从具有男性气质的怪异女孩到“易装”男子再到被磨平棱角的妻子,徐群珊追寻的自我“超性别化”的可能在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秩序之下不断地消磨,性别的复杂表演性质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文化机制对个体性别身份的规约以及个体在颠覆机制时所遭遇的遏制。通过“徐群珊/山”的性别操演,严歌苓揭示了女性性别身份是社会历史与文化建构的,预设的性别规范的意识形态导致女性分裂的自我,而贱斥者能够向男性霸权机制提出挑战,有助于重建女性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