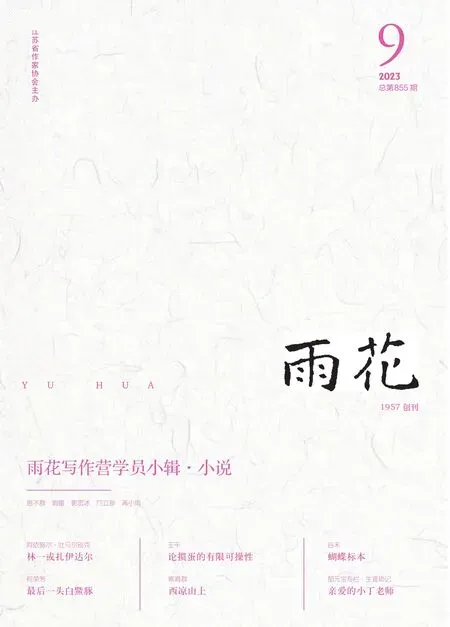西凉山上
熊育群
山脉从北延伸到昭阳区的西面,绕过山的南端才是向西的路,大山包镇就在西边。乌蒙山莽莽苍苍,只有昭阳这块盆地把山推远了。奔波在崇山峻岭中,我体会到了平原的可贵。平地被当地人称作“坝子”,昭通人说到“坝子”都带了一种感情,那实在是大山的恩赐。
然而,我急匆匆赶去看的还是山!这个决定是在大巴停靠服务区时做出的。那时我跟沈洋才认识,他从昆明一路陪同。他说,不到大山包等于没到昭通。他是大山包人,说话的口吻一半是骄傲,一半是为我惋惜。
离正午还有一个小时,离我乘机的时间还有六个小时,我们在威信开往昭通的路上,按大巴的速度,去大山包哪怕看一眼都来不及了。沈洋叫我把行李拿下来,他陪我坐小车去。于是,我们一路狂奔。这感觉不是去看风景,而是去见藏在大山深处的绝世容颜,只为惊鸿一瞥。“大山包”这么一个平实得几无想象空间的名字,真的有什么惊世容颜吗?
昭通海拔高,去大山包还要爬坡,接连180 度急转弯,转来转去人就转晕了。我望着云朵,山坡向着天空飞升,大地倾斜,直插云霄。我的脑子像浸入了凉凉的液体,感觉血液沿着毛细血管在往外渗透,有些恶心。我的高原反应上来了。
这面山坡属于横断山脉。一条山高谷深的大山脉延绵几千里来到昭通,巨大的山坡向着西面俯冲,在昭通坝子前戛然而止。山坡就是横断山脉的终结之地。隔着平坦的昭通坝子,东边隆起的是乌蒙山脉,一座座山峰观者一样环列,远处的山脊泛着幽蓝之光。山与山的对峙,横断山脉的气象显得尤其宏大,钢蓝色山体帐幕一样升起,星月有如帐幕顶上点亮的灯。
宏伟的地理总是令我静穆。有生之年我走过了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天山,它们是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是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奇迹。唯有横断山脉我一次次奔赴,几乎走遍它的高山峡谷。
1998 年进藏,我走到了横断山脉的起点,又从滇藏线进入山脉深处,渡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爬过分开它们的三大山脉: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他念他翁山——怒山、宁静山——云岭。那时,投身荒野是那么决绝,我欲从一种精神的惑乱中解脱。雄浑苍凉的山脉祛除人的妄念,让人心神安宁。我从然乌湖进入,像到了另一个星球,红得发紫的岩层刀削斧劈,其荒凉抹去了所有生命的痕迹……
二十多年里,在滇西北,我一次次深入怒江、澜沧江大峡谷;在川西北,走过锦屏山、邛崃山、岷山、摩天岭,那里是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涪江流过的地方。
想不到,在昭通遇见了横断山脉的终结之地,金沙江又在眼前出现:牛栏江在大山包鸡公山山脚往北奔向大凉山,在一片淡蓝色的山影间汇入了金沙江。这条黄色的江绕开昭通,由东往东北方向奔去,在不远处流入四川盆地,与岷江汇合。
牛栏江切开一道深深的峡谷,犹如大地的一条裂缝,四处皆为玄武岩绝壁,江面如一条银线穿过。
眼前的景象让我想到科罗拉多大峡谷,牛栏江峡谷的深度超过那条大峡谷1000 米,垂直落差达到2600 米。其深其阔,气势磅礴。昭通最高峰巧家药山雄峙对岸,当年红军长征从药山下走过,“乌蒙磅礴走泥丸”恰是其诗意的写照。峡谷升起的风,人着翼装可沿着弧形峭壁滑翔。这里曾举办过两届全球翼装飞行大赛。
站在悬崖之上,俯视下方,脚下一座山,三面悬空,一条窄窄的山脊线通到天幕似的悬崖下,想不到山顶竟然住有人家。沈洋说,小孩子腰间要系一条绳索。村里杀年猪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猪一挣脱就会直坠崖下。
大山包连同田坝、炎山、大寨子皆称西凉山,海拔最高达3364 米。它叫山却非山,是小小坝子、草甸。大地如毯,到处是起伏的曲线,太阳照到了每一寸泥土。云雾在牛栏江峡谷里爬不上来,悬崖间经常云海翻腾,大山包却一直是艳阳高照。四季也被困在大峡谷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疑惑,这是青藏高原的飞地吗?高原上的人皮肤黝黑,戴大大的头巾,穿羊毛披毡,草地上放牧牛羊。这样的情景也在大山包出现了。
远处一个放羊的女孩,穿着羊毛毡子,她的皮肤就像笼着一团夜色。沈洋指着她说,他小时候也是这样,整天看着羊群,天上是风在放牧白云,地上厚厚的三叶草和映山红在风中摇曳,羊就是白云落到地面,缓缓移动着。那时,他的脑海里飘着无尽的幻想。回家的路上,草地上浮了一层月光,感受到月升日落交替的时光,跟天空一样无边无际。
草原是寂静的,却不孤独,因为孤独无处不在,孤独就成了一种习惯。走在大地上的只有人的脚,羊、牛和骡马的腿。人靠一双脚,到磨坊磨面、草原放牧、上学、种地,来来去去,脚步声只有附近的虫儿听得到。那年沈洋九岁,他独自走在偌大的草原上,就像虫儿爬过,他去替父亲看守跳墩河水库,湖上的风声和黑颈鹤的鸣叫使恐慌的夜晚幻影幢幢。
草原上长满了松木,后来被砍光了。没有木柴了,他们发现了海垡。海垡是树叶、枯枝与垃圾的混合物,年长日久,在低洼处受到雨水、积雪和阳光的作用,形成了腐殖土一样的可燃物。土地下户的时候,沈洋第一次放牛,分到家里的飘痧母牛和小黄母牛由他放牧,他用网兜装了一兜海垡和洋芋,饿了他就用海垡来烤洋芋,先将海垡敲碎,铺在地上,上面放上洋芋,洋芋上面再铺海垡,一层一层堆高,然后点火。上学了,他仍会烤洋芋,但吃得更多的是母亲用燕麦做的炒面,苦荞做的荞粑粑。洋芋、苦荞、燕麦是这块土地上仅有的农作物。
小车从镇中穿过,砖混结构的房屋大都没有粉刷,露出红砖,路过的人走得极慢。一转眼小镇就不见了,草原回旋、起伏,尽管快立夏了,可车外呈现的仍然是冬天的景象,大地一片枯槁,不见半点绿色。
山包后面出现了一个小村庄,几栋低矮的草房,墙是泥巴舂的,人字形的屋顶由燕麦秆一层层整整齐齐扎成。沈洋说,这就是他出生的村庄,他的童年和少年都在这里度过。
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小时候沈洋经常去砍柴,松林消失后,土地开始沙化,春天的狂风卷起黄沙如同大雾一样弥漫。夏天,屋顶上长出了燕麦、苦荞和青草,遮盖住了房屋,村庄就像一片片摇摆的“庄稼地”,袅袅炊烟从绿油油的“庄稼”下面冒出来,升上苍穹。冬天,屋檐挂着冰柱,火塘屋里家人团团围着一堆火取暖、抽烟,享受最自在的时光。从此,看到火,沈洋心里就觉得踏实、可靠。哪怕到了坝区学校,天气炎热,他依然要在房子里生火。
一路上全是回忆,沈洋既沉湎又感慨,阳光和风带着往昔的味道,让岁月失重,时空混杂,情绪一忽儿高一忽儿低,暗合了坡地起起落落的节奏。正当小车飘似的有如滑行,路却突然消失了。牛栏江大峡谷在前方垂直塌落下去。地貌突变,偷袭一样让人猝不及防,只看一眼脚下的悬崖就头昏目眩。
悬崖上出现了松树,峡谷里绿色与青灰、赭褐、铁黑色的岩石交叠,色彩丰富。一片巨大而空荡荡的虚空悬挂在前方,鸟翅也不能掠过。这是大地的奇迹。
我想到了人的命运,放牛娃沈洋从这片土地走出去,从茅屋走向了阔大的世界,如同奇峰拔起。他从村到乡,从区到市,后来到了省会昆明,从事宣传工作。他写家乡,从牧羊女、赶场人、大山包云海、磨坊记忆、洋芋纪事到外面丰富的世界,创作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发表了一百多万字,成为一位作家。不到大山包,谁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不知道他人生中的奇崛,堪比牛栏江峡谷的风景。
青烟起处,悬崖边的一个老妪正在烤洋芋。她头上扎着蓝色和白色两层头巾,脸色黧黑,眯眼微笑。我想,沈洋的母亲跟她也许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沈洋跟她打招呼,从铁锅里拿起一个洋芋,熟练地剥开皮,送到我的手中。我试图品出高原的味道和他童年的风味。一股清香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一边吹一边吃,尽管中心部位并没有熟透,我也全都吃下去了。这就是大山包人的吃法。
下山,沈洋宁可我冒着误机的风险也要带我去看跳墩河水库,那个在九岁孩子记忆中停留的地方。一湖碧水之清澈,湖光山色之空灵,非人间气象,让人怀疑这水是天上飞下来的。此刻它放空自己宛若无物,某个瞬间就会像丝绸一样甩袖而去。
但是,甩袖而去的是我,沿途不容停车,哪怕在湖边上站一站的时间也没有,我总是成为绝美之地的过客。现代人不知为何要生存在一种令人晕眩的速度之上,千山万水走遍,却不留半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