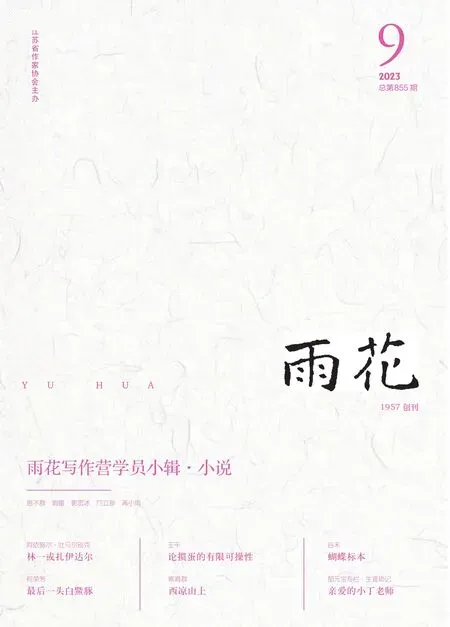林一或扎伊达尔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1
一直到新年前一天,北京都没有下雪。温度低到令人不适的程度,天空似乎下一秒就要裂开,然后落下纷纷扬扬的雪来——但一直没有。
翟娜尔习惯了早上清扫房间,然后在厨房冲一大杯咖啡,端到工作台前,开始一天的工作。清扫完房间,她把扫帚随手塞进厨房门背后,门和墙之间的狭小缝隙让扫帚正好立起来。
她一边冲咖啡一边想,母亲一生中从未这样做过——哈萨克人认为扫帚要平放在地上,才不会招来厄运。三十年来,母亲一直是这么做的——即使翟娜尔十二岁时她们家搬进了楼房,长期的城市生活也没有改变母亲的习惯。
更别提那些琐琐碎碎却贯穿一生的禁忌:不可以用左脚踏出门去;不可以夜晚修剪指甲;不可以裸露着头发做饭而要包上头巾;不可以说不吉利的话;不可以踩踏男子的胸口……这些禁忌贯穿了母亲的一生。尽管母亲是小城里颇受尊敬的一名医生,一个兢兢业业的职业女性,但回到家庭,她依然是一位恪守传统的母亲和妻子。
母亲也用同样的标准教育和要求翟娜尔,她一定相信女儿在北京也是这样遵守禁忌的,想到这儿,翟娜尔又回到厨房。其实厨房里没有扫帚放平的空间,但她还是把扫帚放倒在靠墙的地板上。
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林一。
她和林一是大学同学,在他们那所以培养精英为己任的大学里,她和林一可能是两个少有的会讨论文学的傻瓜。他们常常会买上几罐啤酒,在操场上边喝边闲谈。又或者,沿着学院南路,一路来到学校附近那个不大的公园散步。在翟娜尔看来,他们之间的欣赏和情感,远远超出了爱情这样狭隘的范畴。以往她觉得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出现在真实生活里,但它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他们总是肆无忌惮地交谈,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精神的疼痛,却从来没有开口确定成为恋人。
哈萨克族同学散落在各个学院,只有午餐和晚餐时才会在餐厅相遇,但关于她和林一的绯闻早就传遍了校园。他们对翟娜尔选择了林一作为男友颇为惊讶。有一天在餐厅时,一位哈萨克族女同学和她聊起了林一。那位女同学丝毫不觉得自己越界过问了翟娜尔的私事是什么问题,翟娜尔也无法责怪她的好奇心。翟娜尔有些害羞,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罪感,她言不由衷地解释说她和林一只是普通朋友。
林一似乎也知道她的犹豫不决,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相互陪伴,然后在一次又一次默契的交谈中更加确信彼此的心意。
她很难想象如果父母知道自己和林一在一起,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几年前,她家附近的牧场上来了一位华裔女孩儿,她爱上了旅行中为自己拴马的哈萨克族汉子。两个人最终冲破重重障碍,结婚了。那个夏天,窸窸窣窣的流言一直在牧场上流传,甚至传到了翟娜尔家所在的小城。不同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还有长久以来流传的婚姻习俗让两个简简单单相爱的年轻人仿佛犯下了错。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人们似乎确信他们即将或者最终会分离。没过几年,两位年轻人真的黯然离婚,据说那个女孩儿回到了澳洲生活。
大学时代,她还太年轻,不知道如果自己选择不结婚会怎样,也不知道如果真的和林一结了婚,又会如何?他的家乡在南方,和林一认识以后,那个南方小镇的名字也刻在了翟娜尔心里。那里和翟娜尔的出生地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和人文,翟娜尔曾经偷偷设想自己去往从未踏足的南方小镇,和林一的家人相处的场景。
她固然很爱林一,她很确信。但从小到大,她的设想里,丈夫的人选和他的出生地都不是林一这样的。
2
林一发来晚上约会的地址,其实是他们过去常去的那家酒馆,但林一一向会把每件事都提前确认一次。翟娜尔回复“收到”,然后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毕业后,林一和她都留在了北京。她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工作不忙,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稿和写作。周末的时候,除了和林一约会,她还会去和哈萨克族的女友们聚聚餐。她们不知道翟娜尔还有林一这样一位地下男友,在她们眼里,翟娜尔一直是个对爱情毫无兴趣的单身女孩儿。
而林一是那种无论内在如何波涛汹涌,外表都波澜不惊的人。他工作上很有起色,也没放弃写作——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白领,周末和晚上则是勤勤恳恳的写作者。比起总是能够感知痛苦并把这种感受描述出来的翟娜尔,林一其实是一个过分平静的人,他生活简单规律,很少有情绪的波动,甚至不需要太多朋友,看书和写作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林一只是恰好能够感知和看到翟娜尔的那份疼痛,而这份默契又让翟娜尔不知不觉地沉沦其中。
他们没有选择住在一起,而是各自生活,只有周末才相见。两个相爱的人,住在一起原本可以更加亲密,还可以应对住在北京的许多困难,但他们似乎总是无法跨出这一步。
一直写到下午五点,翟娜尔才站起身来,吃了简单的晚饭。她拿着浴巾和换洗的衣物来到浴室,认认真真地洗了个澡。音箱里传来的音乐让她从写稿的紧张状态中抽离出来。她最近有些心事重重,对于一个住在北京的女孩儿来说,30 岁是一个临界点: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到家乡;是选择一个看起来合适的男生结婚,还是继续单身下去……而对翟娜尔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从都市生活的幻象里抽身,看看家乡的父母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和人生选择有多为难。
翟娜尔决定暂时不想这些,她从浴室出来,把头发吹干,从香水架上选了一支“三宅一生”香水喷在头发和手腕上,然后从衣柜里拿出一条丝绒旗袍换上。她喜欢在着装的选择上弄点“文化碰撞”,有时候她喜欢穿绣着羊角纹的手工定制连衣裙,搭配高跟鞋和珍珠项链,变成一个都市里的哈萨克族女子;有时候她选择穿一条旗袍或者日式连衣裙,然后戴一条哈萨克风格的项链,变成一个有点异域感的都市女孩儿。她喜欢在着装上营造一点风情,这让她觉得有趣。今晚,她决定用丝绒旗袍搭配皮草,和林一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他们约好的地方在宝钞胡同。那里不吵闹,但有歌手驻场,酒也好喝。他们总是在周末的夜晚约在酒馆里聊聊天,听听歌,然后一起在午夜的街道散步。
本质上,她和林一的感情与大学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没有过多的物质追求。他们只是喜欢在周五下班后的夜晚一起吃饭和散步,彼此分享一周以来发生的事情。
但这样的情感也有弊端——她和林一从来没有走向一种实质性的情感关系。如果男女之间的情感是一棵树,那么他们的情感似乎一直停留在抽芽的那一刻,而从未长出枝叶。他们默契地把彼此的情感都留在了未曾被现实染指的角落,守护着这份感情的纯净。
怎么可能不变呢?两个大学里的年轻人,留在北京参加工作,从零开始,一直到今天,整整七年过去了,翟娜尔和林一都不是当年的彼此。
林一在另一个城市买了房子,已经准备着开启另一段人生,或者说,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妥帖的退路。可以想到,不远的将来,林一会和一个同样来自南方的女生成为夫妻。而翟娜尔,单位为她解决了户口和住房,让她暂时可以安心留在北京。他们都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推进着自己的人生。但每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他们仿佛还是刚刚认识时那样。
不知道北京有多少这样的情人,他们在情感上高度契合,在生活的层面却无法真正依赖彼此。而那些真正共度一生的人,可能并不需要精神的契合,而只需要一套房子和两份稳定的工作。
大学时代的林一长着一张清爽英俊的脸,笑起来眼角有小小的纹路,翟娜尔总是着迷于他眼角的笑意。她一直是《乱世佳人》的拥趸,渴望成为斯嘉丽那样的女孩儿,也为瑞德·巴特勒着迷。她一直觉得她一定会爱上瑞德这样的男人。林一的出现改变了她的想法,她从此明白真正的感情是爱上了那个具体的人。翟娜尔和林一都是情感上有些内敛的那种人,所以翟娜尔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多爱林一,但她觉得不必说,林一会知道。
工作以后的林一开始慢慢从一个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有时候几天不见,亲吻时林一的胡茬会扎痛翟娜尔。而有时候,他和翟娜尔聊起工作,翟娜尔会觉得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林一有点别样,也有点陌生。
3
从大学时代开始,翟娜尔的生活里只有林一一个男生。她很少出门,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看书和写作。翟娜尔是那种可以永远独处的人,见林一是她觉得唯一必须出门的事情。
直到今年,她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扎伊达尔。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她和朋友们参加在京哈萨克族的那吾热孜节庆典。从餐厅出来,她和姑娘们临时决定续个摊,去附近的酒吧坐会儿。
她们正站在门口打车,就看到一群男生呼啦啦地也从餐厅出来。在北京的哈萨克族年轻人就算不认识,也彼此脸熟。大家乱七八糟地互相打了招呼,就决定一起去酒吧。
男生们开始用打车软件叫车,然后叫相熟的女孩儿搭车,一起去酒吧汇合。轮到她搭车时,一个陌生的男生打开车门,看着她和两位女友坐上去,才坐进副驾驶。
那是难得尽兴的一夜,他们在酒吧玩到天亮,翟娜尔也没提前溜走,而是决定和大家待在一起。在北京,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一个月能见一次已经算是高频率。更何况是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有些人她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大家围坐在酒吧的长条桌上,努力伸长脖子听对面的人说话,每个人都热烈地交流着近况,身边的人换来换去。翟娜尔感到难得的放松和欢乐,不知不觉猛灌了好几杯。
就在这些热闹非凡里,她总能感觉到一束目光,而她转过头去看时,那束目光没有躲避,而是更加炯炯地迎上来。她意外地发现那是一种温柔和善意的注视。目光的主人端起酒杯遥遥致意,翟娜尔也拿起自己的酒杯远远地碰了一下。
快天亮时,大家都醉醺醺地穿上外套,准备各自打车回家。翟娜尔感觉到那簇目光离自己越来越近,直到靠近自己:“翟娜尔,你好。”她抬起头,看到了扎伊达尔。扎伊达尔有一头略微金黄的头发,搭配他近乎白皙的面庞,和鹰隼一样的高挺鼻梁,有一种错位的和谐。
相熟的朋友立刻介绍两人认识,扎伊达尔是石油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了石油研究院工作,刚刚完成五年的驻外工作回国。轮到介绍翟娜尔时,扎伊达尔笑着说:“不必介绍,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也一直关注她的社交账号。”于是,他们加了微信。
“关注你很多年了,你一直没变,这样的你真的很难得。”那天回到家时,她收到了他的微信。翟娜尔又敏感地觉得这位扎伊达尔有点有备而来的意味,索性没有回复。
过了一两周,在一个她常去的餐厅里,她又一次碰到扎伊达尔。那是一家伊朗餐厅,户外已经暖和起来,他正坐在户外悠闲地抽着水烟,和几位朋友交谈。他看到翟娜尔,从座位上站起来,和她打了个招呼,然后帮她打开餐厅的门,轻扶了一下她的后背,送她安全进门,才回到座位坐下。
翟娜尔坐下的时候,透过玻璃看到扎伊达尔。为了躲避阳光,他戴了一副墨镜。墨镜架在鹰隼一样的鼻梁上,不突兀,还有点英俊。想到自己没有回复他的微信,翟娜尔有点不好意思。
他和朋友们起身离开时,翟娜尔看到他和朋友说了几句,然后径直走到她身边。他向翟娜尔身边的朋友点头打了个招呼,就对她说:“翟娜尔,你好。下周我可以约你吃个饭吗?”
翟娜尔有些错愕,只好说:“好的。”
下一周他真的发来邀约的微信。她一向觉得哈萨克族的男生有点天然的掌控欲,没有分寸感,但扎伊达尔彬彬有礼,也没有跨过什么界限,翟娜尔觉得再拒绝就不礼貌了。于是,他们约好在那家伊朗餐厅见面。
那是一个难忘的周末。翟娜尔一直在汉语学校读书,几乎没有哈萨克族的男生朋友。偶尔认识一个,也觉得难以成为交心的朋友。而扎伊达尔就是那种可以成为朋友的男生,他从小读哈萨克语学校,能说很好的哈萨克语,大学时来了北京,在石油大学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身上有一种混血的美感,既有传统生活留下的痕迹,又经过了都市生活的打磨。翟娜尔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相似的气息,他们算得上是同类。
那家伊朗餐厅有一种酸奶饮料,味道和翟娜尔小时候在牧场上喝到的一模一样,翟娜尔经常只为了喝这一杯饮料来这家餐厅吃饭。那天,扎伊达尔点了两杯,说:“你得尝尝这个,完全是奶奶们的手艺。”翟娜尔说自己也很喜欢喝,于是他们聊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牧场生活的场景。
扎伊达尔说他经常端着一个小碗,等待着牛群归圈。奶奶挤好第一桶牛奶后,会当场舀出一碗,看着扎伊达尔豪情万丈地一饮而尽。
“哇,幸好你没有得布病。”说完,她和扎伊达尔同时大笑起来。其实翟娜尔小时候也常常等着奶奶挤好牛奶,喝下第一碗。那是独属于草原儿童的特权。
在北京,有一个可以一起讨论牧场和爷爷奶奶的人,是多么难得。他懂每一个笑点,知道要在哪里发出笑声,也知道怎么把她逗笑。他完全知道她是怎样长大,怎样走到今天。他们的人生经历,几乎是彼此的翻版。
翟娜尔说,很长时间里她一直不知道倒水以后茶壶嘴不可以对着人,哈萨克族好像没有这样的禁忌。她一直在工作场合帮同事倒茶,然后把茶壶嘴对着客人放下茶壶,直到一位同事提醒她。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她常常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小小碰撞。
扎伊达尔说,他曾经在饭桌上对着一位南方的朋友说,我们把鱼翻个面儿吧?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南方人很忌讳翻鱼。
同样的经历让他们有点惺惺相惜。
看得出来,在非洲度过的五年,让他变得更加珍惜友情。他在非洲待的那个城市只有一家中国餐厅,是一家兰州拉面馆,所以每当想家的时候,他会去吃一碗兰州拉面,和拉面馆的老板聊几句家乡话。他说,他经常在下班后,驱车一两个小时去海边等待日落。等太阳消失在海的尽头,他再开一两个小时车回住处。
“为什么要开那么久的车去看日落啊?”翟娜尔不明就里地问。
“因为我总觉得洋流会带着我的思念,从非洲去往亚洲啊。我怕还没回到家乡,爷爷和奶奶已经不在了。”扎伊达尔苦笑着说。
翟娜尔的爷爷奶奶都是她在外求学时去世的,父母隐瞒了爷爷奶奶去世的消息,一直等到她暑假回家才告诉她。很长时间里翟娜尔都无法原谅父母,她完全懂得扎伊达尔的苦笑。
在晚餐即将结束的时候,扎伊达尔终于把话题切入了主题,他说他渴望拥有一个完美家庭和美丽的妻子,要让美丽的妻子成为他手心的玫瑰。而在他的心中,翟娜尔就是这朵玫瑰。
听到“手心的玫瑰”这一句时,翟娜尔在心里默默想,这是哈萨克族的男人才会说出的话,让人措手不及,又有些触动。但那一刻翟娜尔很想念林一,林一不会说出“手心的玫瑰”这样的情话,但他懂她的一切。
翟娜尔说他们只见过两次,好像还没到讨论婚姻的程度。扎伊达尔却说,那我们至少可以先成为朋友。
那个周末和姑娘们聚会时,翟娜尔提到了扎伊达尔。翟娜尔很少提到一位男生,姑娘们都有点惊讶。当她说到“手心的玫瑰”那一句时,姑娘们也笑作一团。在北京工作的哈萨克族男生其实已经逐渐融入周围的一切,很难想象他们的嘴里会说出这样直白的情话。
翟娜尔经常会收到扎伊达尔的快递。有时候是一束花,一件好看的大衣,有时候则是真空包装的羊肉,或是一截马肠。他会说“美丽的女孩儿应该常常收到鲜花”,或者在微信里详细地介绍怎么烹煮马肠。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敞开心门,接纳一位朋友。”扎伊达尔在某一天发来微信。尽管翟娜尔心门紧闭,但扎伊达尔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一丝一缕地融入到她的生活里。
第一次快递员上门的时候,她有些惊讶——那是一个巨大的纸箱,寄件人是扎伊达尔。她打开来,在冰袋的下面看到了真空包装的羊肉——经验告诉她,这差不多是一整只羊。多么彪悍的礼物。她正在忙着写稿子,于是把整袋羊肉放进冰柜里就没再管。有一天,她想起这袋羊肉,决定拿出来分解好备用。她一边做饭,一边看着羊肉解冻。做好饭,冰也差不多化好了,她拿起砍骨刀,却发现羊肉是一块一块的。扎伊达尔早就分解好,一一包装,每次做饭时只需要取用一袋。她看着一块一块的羊肉,不由一笑。
她想到了父亲。父亲就是这样的,他会料理好这个家庭里男人所需做的一切,也会常常对母亲说出令人不由一笑的甜言蜜语。但与此同时,他经常呼朋引伴,家里一年到头聚会办个没完。爷爷奶奶生育的十个儿女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更何况还有父亲的堂兄弟。家里一年到头都是客人。招待完客人,母亲经常收拾残局到半夜。翟娜尔和父母穿着哈萨克族服饰的合影被放大,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在那张照片上,父亲是绝对的中心,而她和母亲则是父亲身畔的两朵玫瑰。经营和展示一个完美家庭,承载着父亲作为男人的虚荣和骄傲。
与此同时,母亲度过了劳累的一生。父亲家族里的每一个亲人生病,母亲都会动用自己在医院的人脉协调他们住院、治疗,还在工作的间隙去看望和照料他们。午休时,她会匆忙地在家里做好饭,自己顾不上吃,就送到医院。甚至身无分文的亲人出院时无法支付医疗费用,母亲还要替他们签担保协议。爷爷和伯伯患癌症时,也是母亲临终陪护。母亲甚至帮助已经无法排尿的爷爷和伯伯插导尿管,还在他们临终前帮他们擦洗身体,剃去头发和胡须。
即使这样,母亲也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哈萨克族媳妇儿的标准。冬宰季节和古尔邦节,亲戚们轮流宴请,母亲也尽她所能地招待每一位亲戚,但亲戚们还是会说母亲是个沉迷工作、不够贤惠的女主人。亲戚们来城里时,看到母亲做好饭菜匆忙地赶去上班的身影,总会跟父亲抱怨没能喝上一口热奶茶。
翟娜尔在北京工作的时间越久,父母对她的婚事和感情归属就越是感到忧心。他们数次说,只要你嫁给一个哈萨克族男生,男方暂时买不起房子或者收入不够高也没有关系。如果翟娜尔选择了扎伊达尔作为丈夫,父亲和母亲可能会喜出望外吧?这不仅是一个哈萨克族男生,还称得上是一位青年才俊,但翟娜尔已经能够想象自己将要开始怎样的下半生。
4
她没有隐瞒认识了扎伊达尔这件事,还和林一聊起她的困惑。她和林一都清楚,他们的情感很难有结果。相比恋人而言,他们更是推心置腹的朋友。
多年来的都市生活和职场磨练,打造了两个过度理性的人。他们不用真的生活在一起,就知道未来一定是充满艰辛和鸡飞狗跳的。“怎么可以浪费珍贵的人生,在这些无价值的事情上,尤其是早已知道了结局。”翟娜尔曾这样对林一说。她曾和林一聊起那个华裔女孩儿的故事,他们在脑海里设想了生活在一起将要面对的一切。
当然了,他们都有过情难自禁的时刻,不止一次。
最后,他们都保持了理智。她和林一都是从无名之地披荆斩棘地考到北京,走到今天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都是那种渴望有所建树的人,他们的人生就像一座建筑,刚刚搭建好地基,即将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刀阔斧地建设。
更何况,他们还要面对许多禁区。爱是什么呢?跟那些庞杂的现实比起来,爱更适合被呵护在内心最深的地方,在无人的角落里拿出来安静地回味。而即使是最为纯净的爱情,和现实碰撞在一起,也一定会立刻破碎。
翟娜尔的矛盾在于,她理性聪慧,但与此同时,她屈从于身为哈萨克族女子的命运。翟娜尔其实是个传统女子,或者说,有成为传统女子的潜质。而扎伊达尔看到了她的这一面,并试图把她的另一面消解,只保留传统的一面。
翟娜尔经常在和他吃饭时看到他接电话。通常都是家乡亲人朋友的来电,他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任何问题扎伊达尔都能找到办法解决。令翟娜尔触动的,其实是他那种无限的耐心,即使是素不相识的同乡辗转打来电话,他也会耐心地接听,并帮忙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这与其说是一种能力,不如说是扎伊达尔身上有一种善意的底色。只是扎伊达尔的善意是那种久经磨练、暗藏锋芒的善意,他并不是毫无原则,只是因为经历丰富又足够聪慧,处理起来游刃有余罢了。
翟娜尔在他身上看到了未被现代文明驯服的野性和率真。她觉得,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扎伊达尔也可以马上找到门路带她登上诺亚方舟。她被他的善良和锋芒打动。更何况,他对翟娜尔付出的,是那种成年人里难得一见的呵护和疼爱。
他常常会在陪翟娜尔吃饭时,安静地听她说话。翟娜尔总是说出很多对传统生活不满的话,当然也提及母亲忙碌辛苦的一生。扎伊达尔不会反驳她,而是用一种温柔的眼神看着她。
他也提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和翟娜尔的母亲一样,一生都在职业女性和贤惠妻子的角色里奔波忙碌。因为父亲工作忙碌,所以扎伊达尔陪伴母亲的时间很长。霸道的父亲偶尔回家时,几乎不会听母亲说话,所以扎伊达尔决定要成为一个善于倾听的人。
翟娜尔困惑地说:“那些总要兼顾美丽和贤惠的母亲身上有一种神性,而让我们忘记了她们只是普通的女人。”扎伊达尔巧妙地回应她说,我恰好也只是普通男性。
扎伊达尔妥帖地预估和照料翟娜尔生活的一切,并保持着一种礼貌和界限,这样一来,一向敏感的翟娜尔也无法拒绝扎伊达尔走进自己的生活。她和扎伊达尔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
盛夏到来的时候,翟娜尔终于决定和扎伊达尔开始一段正式的关系。那是一段甜蜜时光。每次送她离开的时候,他总会吻一吻她的额头。这让翟娜尔想起父亲,父亲总是吻小翟娜尔的额头,一直到翟娜尔成年才改为亲吻手背。所以扎伊达尔亲吻她的额头时,翟娜尔总是感到非常安稳。
但与此同时,扎伊达尔总是喜欢改造翟娜尔。一次聚会时,翟娜尔发出爽朗的大笑声,扎伊达尔看向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亲昵的不满,翟娜尔明白他觉得自己这样不够得体。有一段时间,翟娜尔喜欢穿露出肚脐的短T,搭配牛仔裤。扎伊达尔说,翟娜尔,你应该学会优雅的穿着,这样才不辜负你的美丽。下一周,她真的收到一件剪裁得体、包裹严实的连衣裙。
扎伊达尔在按照他的设想,塑造一位理想妻子。每当翟娜尔做出一桌美食邀请朋友们来聚会,或者在朋友们相聚时说出令人会心一笑的玩笑话时,又或者穿着那种大方得体的裙装戴着珍珠耳环出现时,扎伊达尔都会不失时机地赞美她,或者投来充满爱意的一瞥。
翟娜尔依恋扎伊达尔带来的传统生活,那种气息让她觉得安心。但她很确定,自己并不是扎伊达尔设想中的那种女孩儿,她只是暂时屈从于这份温暖。
秋天来临的时候,她选了一件暗红色的棒球外套送给扎伊达尔。扎伊达尔高兴地收下,但一直没有穿。翟娜尔知道,在扎伊达尔看来,穿红色的棒球外套会显得过于幼稚。
而有一天,他看到翟娜尔在读伍尔夫,拿起来随手翻了几页,就说:“哇,这个女作家最后自杀了。你最好不要看她的作品。你知道的,有时候作家和作品无形的影响力太大了,我只希望你健康快乐,不要变成一个忧郁的女孩儿。”
翟娜尔没有说话,因为她知道什么都不必说。扎伊达尔是那种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男人,他不需要别人的教导,而总是在教导别人。
关于伍尔夫的对话发生后,翟娜尔还和扎伊达尔见了好几次,一切都和过去一样甜蜜。直到有一天夜里,她想到那次聚会,突然怒从中来。她厌恶扎伊达尔的这一面,也厌恶这段时间来他改造自己的一切作为。
翟娜尔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表达对他的不满:“你不喜欢我大笑。你不明白什么是穿衣自由。最重要的是,你在干涉我的想法。我真的痛恨你这一点。”
发完微信,她坐在工作台前发呆。她是那种对别人都很疏离和包容的人。与其说包容,不如说她的世界只欢迎有限的人。对不算熟悉的人,她一向不会作任何要求,很少有人可以看到她情绪激烈的那一面。即使是林一,认识多年,她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发过脾气。
真是发了疯,扎伊达尔一定觉得她疯了。想到这里,翟娜尔更加觉得无法面对扎伊达尔,索性把他的微信删除了。删除之后,她觉得自己更愚蠢了。
扎伊达尔没有加回来,于是翟娜尔认为他们已经分手了。
5
和扎伊达尔亲近起来以后,她和林一开始默契地不再见面。他们曾经设想过两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分道扬镳的那一刻,所以当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翟娜尔没有伤感,只是觉得应该如此。
其实她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林一或扎伊达尔”的选择题,而是属于翟娜尔个人的命题。
“伍尔夫事件”发生后几天,翟娜尔照例在家写稿。手机响了,是林一。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通过电话,也没有见过面。电话一接通,他们还是愉快地聊了一两个小时,交流了一下近况,谈了谈最近的写作,还有为什么今年北京没有下雪。
电话快要挂断的时候,林一略有些生硬地把话题转向了扎伊达尔:“你和他怎么样了?”翟娜尔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丝难得的情绪。
和林一认识的这些年,翟娜尔偶尔会疑心林一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自己,毕竟他从来没有以一种正式的形式表达过爱意。翟娜尔只是能够感受到,在他心里,她和所有其他人都不同。
翟娜尔有点惊讶,但还是认真地回答:“分手了。上周。”
“哦。”过了一会儿,林一的声音从话筒那一端传来。
于是翟娜尔索性多解释了两句:无非是性格不合,她喜欢自由自在,而扎伊达尔喜欢每件事都有标准和规则;她喜欢伍尔夫,而扎伊达尔不喜欢。
林一的语调里有一些难得的调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伍尔夫不是一个男性喜欢的作家。你应该跟他聊聊萨特。”
翟娜尔有些粗鲁地说:“屁。作家分什么男女。”
林一突然笑了。大学时代,她和林一总是不厌其烦地讨论那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工作以后,讨论文学成为了奢侈的事情,她在工作的场合一向都只聊安全的公共话题,比如天气和交通。而和林一在一起,随口聊起伍尔夫和萨特,就仿佛讨论天气和交通一样自然。
她也知道为了伍尔夫和男朋友分手听起来很荒诞,但她就是非常生气。也可能她早就厌倦了这一切,而伍尔夫只是一个借口。
翟娜尔也笑了,随即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翟娜尔知道,林一一直计划离开北京,回到他购置房产的那座城市生活。这些年,他们已经陆陆续续送走了几乎所有北漂的朋友,只有林一一直在离开和再坚持一段时间之间犹豫不决。
“应该是新年后。昨天刚递了辞职信。”林一说。
翟娜尔的心漏跳了一拍。真奇怪,他们早就理智地讨论过所有的一切,但知道林一真的将要离开的时候,翟娜尔的心还是有点疼。她立刻想到,在所有那些翟娜尔表现出理智和疏离的时刻,比如她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个华裔女子婚事的时候,比如扎伊达尔出现的时刻,林一的心一定也这样疼过。
想到这儿,翟娜尔决定问出口:“你爱过我吗?”
“爱。”林一这一次回答得很快。多年来,这是翟娜尔第一次问他是否爱自己,也是林一第一次说出答案。翟娜尔的心再一次微微地疼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林一说约她一起去胡同里那家酒馆跨年。这原本是他们多年来的保留节目,翟娜尔同意了。
6
翟娜尔化完妆,站在窗前朝外看了看,发现外面早就下起了大雪,积雪完全覆盖了路面,也盖住了她窗前的那棵翠柏。这是十年来北京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雪。
她回到工作台,拿起手机。北京市气象局发布了局部暴雪的消息。许多网友已经在延庆的山上赏雪,各种各样的雪景早就刷满了手机屏幕。翟娜尔想到大部分出租车还没有来得及更换雪地胎,决定搭地铁去见林一。
在地铁上,她想起刚刚上大学那一年,北京也下过这样的大雪。不同的是,那是一场深秋时节突如其来的暴雪。她和林一约好在宿舍楼前集合,一起去处理一项班里的工作。她没有带伞的习惯,而生在南方的林一很自然地从包里掏出一把伞,撑在两人头顶上。
银杏叶被暴雪猝不及防地击落,空气冷冽,翟娜尔的脸生疼,又有些别样的诗意,于是她伸出手去感受雪的温度。林一看了看她伸出的手,把伞换到另一只手,然后握住了她的手……翟娜尔没有觉得突兀,仿佛早有默契,于是牵在一起的手再也没有放开。
翟娜尔一边想着往事,一边站在地铁口把伞撑开,朝着林一走过去。林一可能刚刚下班,背着双肩包,长款大衣的领口露出黑色衬衫。他没有撑伞,任由雪落在肩头,连睫毛上都落了雪。
翟娜尔发现他正在用一种忧伤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好像在跟什么人告别。翟娜尔知道自己一定也在用同样的眼神注视着他。
她把伞分了一半给林一,伸出手想要帮他掸去肩头的雪。手机却响了,翟娜尔只好用空出的那只手掏出手机,是扎伊达尔的短信。
他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套贴了很多便签、上面写了笔记的伍尔夫全集,一张是他穿着红色棒球外套的照片。照片里他留着短短的络腮胡子,看起来憔悴又可怜,完全像是一个饱受情伤之苦的男生。翟娜尔不自觉地笑了。
这时,第三条短信来了:“翟娜尔,你好。明天一起吃饭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