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缠绕的一生
李静

潘绥铭。摄影/白杨
对于社科学者而言,73岁也算不上高龄,可潘绥铭还是彻底从学术界消失了多年,近两年更是哪怕是科普性质的讲座也很難请动他。研究了几十年“性”,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如今他安心做一个去野外拍摄野鸟的有趣老头。拍摄的那些照片,他没觉得有多少艺术性,完全是自娱自乐,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出去走走路。
他出版的那些著作《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搭建起了中国性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然而直到今天,性社会学仍然算是一个小众学科。
今年9月,潘绥铭出版了在拍鸟以外的空余时间写作的学术自传《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叙述和总结了他从1981年开始的主要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新思考。大概还是无法真的置身事外,他把自己以前说过很多次的话,再次掰开揉碎在几十年的学术经历里又说一遍。
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性”,希望获得什么、赋予什么意义、表达什么理想、导向什么方向。几千年来人类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于其上,精神和肉体,自私与无私,个人与社会……正是在这里,蕴育着人类认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潘绥铭彻底开始新生活的理由有好几重,最重要的在于他发现且承认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创造力枯竭,所以不愿成为后继者的绊脚石,“总是喋喋不休,真的招人讨厌”。再有就是,他认为他这个人和他的性社会学都属于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而现在时过境迁。
在他的学术生涯里,最为知名的壮举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程,这是中国高等学府课程中第一次破天荒地出现“性”,几乎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那还是1985年,人大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已经看过不少性风俗与性文化英文著作的潘绥铭顺理成章地报上了这门课,被当时的首届学生骂“脸皮厚”,在学校内乃至整个学术界,自然也是褒贬不一。课讲了一个月,学校里劝他还是不要讲了。潘绥铭随即准备放弃,但是不知怎么,几天后,外系老师甚至他东北师大母校的同学,好几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说,一些老师为他打抱不平,甚至有领导来过问。而这一切他一无所知。没多久,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李文海在全系大会上表扬潘绥铭开出新课,性社会学就此生存了下来。
第二个壮举更为惊世骇俗,自1998年第一次去中国南方考察、写出《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潘绥铭又带领他的团队、学生,定性调查了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
潘绥铭强调的“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一向主张不是调查,不要直接提问,而是自然接触、聊天,只有转化身份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对他们的理解才是完整的。可是如何融入那些人的生活呢?首先不能假装客人,那样一点意义都没有,看到的只会是职业表演,而他想了解人。这个难题在潘绥铭1998年第一次田野考察的第三天,就意外地解决了。潘绥铭对她们说:“我只是来看看。”
其实,在那些女孩简单到枯燥的生活中,狭小的世界里,她们只在乎一个人会不会害她,其余诸如为什么要做研究等问题她们并不会关心,多数也不懂。一旦她们放下戒备,就开始和潘绥铭聊生活、聊感情、聊孩子、聊心里话,由于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有些甚至把他当长辈看,“恨不得叫爸爸的、叫爷爷的都有”。潘绥铭慢慢感受到,她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有故事、有牵挂、有感情。

10ab7f61fb6e8c79936ef883110dfc10潘绥铭出版的著作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
在持续了近10年的调查里,潘绥铭得到了很多完全颠覆人们想象的结论。例如,他讲课时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到她们那去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都是被敲诈,被行骗,被她们引诱下水……只有一次,一个男学生答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因为她们几乎没有被男性平等对待过,更不要说尊重,只要跟她平等坐下来聊聊天,她就会掉眼泪。在她们的世界里,“恐怕连爸爸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由于这个领域的猎奇性,潘绥铭在大众眼中被贴上了标签。这让潘绥铭感觉有点别扭,他总结过自己在学术上做的三件事: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四次做过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红灯区”调查以及反思了社会调查的方法。“红灯区”调查只是其中一件,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正是他投入的那些日日夜夜,积累着对方法论的感悟,最终形成2007年他提出的“主体建构论”,以及落实于“相处调查法”“求异法”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
“如果不是一起生活那么久和接触那么多次,我就无法发现,更无法总结出主体建构论的要义。”潘绥铭说。那就是无论社会对那个群体如何严苛与不公,她们并不是完全逆来顺受,而是自己不断地构建出自己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也创造出应对社会与自我发展的各种行为逻辑和策略选择,并且获得了自己相对满意的生活状况。潘绥铭觉得,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应该首先了解和理解这种“主体对于自己和外界所进行的建构”。
潘绥铭出生在1950年,有着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几乎可以彼此复制的人生经历,令人无法不好奇究竟是什么驱使他进入了当年实属空白的性学领域。在他自己看来,其中的偶然性远远大于必然性,因为自己的平淡人生跟日后的研究实在没有太大关系。
但当他进入性学领域后,倒对自己这一代产生了好奇。2000年,他进行第一次全国“性调查”的时候,特意把被调查者的年龄上限规定为64岁,因为64岁的人出生于1936年,到1950年时,他们刚好14岁,开始进入青春期,因此他们可以反映出整个1950到1960年代的情况。
潘绥铭的青少年时期在下乡和进厂当工人中度过,“文革”前学历为初中。1981年,他在女儿八个月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保存了一大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英文著作,所以他一扎进书库,就迎头碰上了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看到的第一本是什么他已经记不清楚,但第一年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类学家佛林格尔于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我觉得,所谓历史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人,在那样的时空中,做过怎样的一些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时的震惊,如今已经难以描述,那些堪称人类奇观的记载对于当时的潘绥铭可谓“狂轰滥炸”,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写作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5100多张,全部是读研究生时一笔一笔抄下来的。
1985年,潘绥铭到人大工作的第二年就开设“外国性观念发展史”,可以算水到渠成,但这门课能够生存下来,才真正使性学这个潘绥铭原本当作兴趣的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
如果说到底是哪些因素偶然或者必然地促使潘绥铭走上后来的道路,他觉得有三件事缺一不可。东北师大历史系的那些英文“性书”能够一直被保留下来,且允许研究生阅读。“这就是天大的偶然。”潘绥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次,大概只有我这样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学生,才更加可能背着导师走火入魔去研究‘性’。人家正经科班出身的学生,从古到今都不会如此自毁前程。第三,全靠1985年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支持我讲‘性研究’的课,我才能一直走下去,否则我就仅仅是无知小儿的偶发无聊而已。”
如果把目光从个体身上移开,望向历史的纵深处,潘绥铭承认,自己赶上了时代的机遇。1980年9月,修订后的《婚姻法》将“夫妻感情破裂”明确地列为离婚的法定理由,爱情开始成为婚姻的主导,那年上映的《庐山恋》第一次在文艺作品里张扬爱情且出现了中国影史上的“第一吻”。
可是他研究的话题毕竟那么敏感,所以不断有人问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阻力?也许有过一些,但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戏剧化。人是时代的产物,能够摩擦出火花似乎不仅在于勇气,而更在于运气。潘绥铭也明白自己遇到的是“不可复制的历史机遇”。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人都分明感到性、爱情、婚姻观念的剧烈变化。可是,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多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人们只能根据自己对周边的观察和经验去揣度。
从2000年开始到2015年,潘綏铭和团队完成了四次“中国人的性”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四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地点和调查方法都一致,问卷的内容也基本一致,具有历史可比性。能够跨越15年的四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中国人在性方面的纷扰也终于借助这四次调查得以被看得更清楚一些。
使用统计学方法对收集到的问卷信息进行分析后,潘绥铭和团队得到很多重要且有趣的结论。例如,中国人的性技巧急剧发展,根据统计结果,2000年被调查者的性技巧平均得分为1.35,2006年猛增到2.19,2010年再增加到2.68,然后2015年是2.55。另一方面,27~35岁人群中“无性者”在2000年时,男性只有2.4%,女性则是0.7%。可是短短15年内,男性人数增加近5倍,女性人数增加几乎14倍,潘绥铭预计,如果2020年也做调查,应该会再翻一番。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但选择单身,而且是无性单身,且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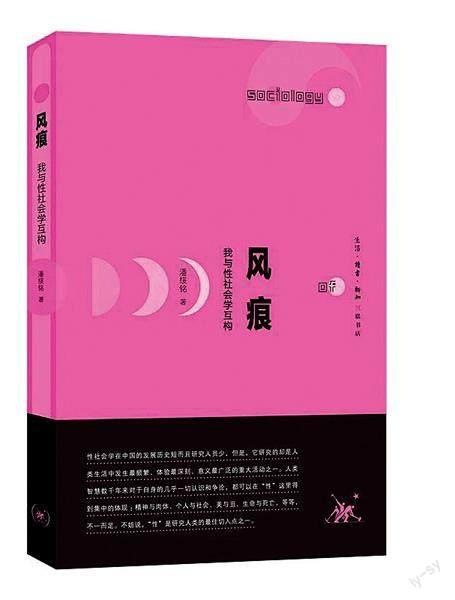
潘绥铭的学术自传《风痕》。
每一项调查数据背后,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潘绥铭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常常只是给出结果,却不能为“为什么”提供清晰的答案。他从来不否认自身的短板和局限性,“我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甚至都没有上过大学,是从中专毕业生——其实就是重读初中——直接考上硕士研究生,就再也没有继续求学。”所以难免“闯禁区多于深追究”。有人批评他“缺乏终极思考”,他没有否认,且自嘲是个哲学盲,一向信奉“常人社会学”,读研之后才读到弗洛伊德的书,把希腊神话也重新补课之后,却仍然无法体会弗洛伊德说的那些“情结”究竟是个啥,只是觉得实在是太矫情了。
当然,两千年来的汉文化也从来没有一种文字化的“性的哲学”,这让潘绥铭一直耿耿于怀,“在性方面,汉文化一直实在是太世俗,太私人化了,“而阴阳哲学又过于大而化之,很难直接管理人们的‘性’,哪怕作为性革命的敌人,也还是需要有一个性哲学啊。可是我实在不是那块料,只能寄希望于后辈了。”
大概也因为如此,性社会学仍然是一个十分小众的学科且仍然伴随着带有偏见的审视。潘绥铭一辈子没得过任何奖,没有任何社会兼职、学会职务和社会荣誉,他又自嘲愚笨,却也知足常乐。他的学生大多数在高校任教,少数到了机关。任教的那些只有5位曾经得以在他们本校开设“性社会学”或者相关课程,并不完全是社会压力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性研究有趣但不重要”。当然,继续写出相关论文的学生也不多,还是同理,学术刊物没工夫理睬他们这一小撮。
潘绥铭常说,研究性社会学,自娱自乐就是唯一的动力,也是唯一的挡箭牌。但再冷门的研究也必然有社会价值,例如他新出版的《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他希望读者能够从中“享受思考”,不研究这个专业的人们把它当作科普读物,能知道“性”还可以研究出这么多内容来。那么也许,“性”这个议题可以变得敞亮一些,因为其本来就不仅仅关乎性本身,而是带着强烈的现实观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退休多年,潘绥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当下的社会思潮,担忧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只能感慨:“我这一辈子耗在性社会学里,老也老了,却瞪着眼看到性文化在走向岔路。”
所以他不准备说很多话了,《风痕》这本书,说是学术自传,却主要是学术,并没有多少自传性质的故事。他的学生说,“应该叫《性社会学思想史》”。这正是他的目的:“我觉得,所谓历史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人,在那样的时空中,做过怎样的一些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风痕》,顾名思义,就是一阵刮过去的风,一小段行将逝去的历史,仅仅是为了留下痕迹,留下史料记载。至于当前和以后的一切,我,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