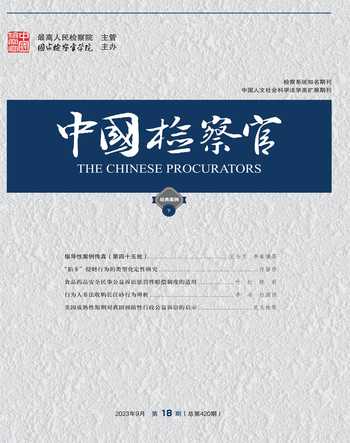最高检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评析
熊秋红
摘 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作了规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事抗诉职责提供了基本指引。最高检发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指导性案例中的“精准抗诉”突出地体现在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准确适用、对此罪与彼罪的准确界定、对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条件的准确理解以及对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妥当处理等方面。指导性案例还展示了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补充侦查、全面论证抗诉意见、深挖关联案件、确立新的法律适用规则等成功经验以及通过能动履职延伸审判监督职能与效果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刑事抗诉 指导性案例 抗诉条件与标准 能动履职
2021年6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 。2023年6月25日,最高检发布了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共计5个案例,这是最高检发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这些案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既有危险驾驶等轻罪案例,也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重罪案例;既有二审抗诉案例,也有再审抗诉案例;既有轻罪抗重罪案例,也有无罪抗有罪案例;既有单人犯罪案例,也有共同犯罪案例;既有证据采信、事实认定争议案例,也有法律适用争议案例。透过这5个指导性案例,可以看到刑事抗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价值以及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刑事抗诉条件和标准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二审抗诉与再审抗诉的条件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二审抗诉与再审抗诉的条件作了规定,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刑事二审抗诉与再审抗诉的标准,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事抗诉职责提供了基本指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8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这里的“确有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也包括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以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如违反公开审判原则、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等。《刑事诉讼规则》第78条补充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导致第一审判决、裁定错误的,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事诉讼规则》第584条细化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一)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罪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四)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五)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禁止令、限制减刑等错误的;(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4条的规定,最高检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事诉讼规则》第591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三)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四)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五)原判决、裁定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六)认定罪名错误且明显影响量刑的;(七)违反法律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的;(八)量刑明显不当的;(九)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十)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抗诉与再审抗诉在适用条件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检察机关“认为”一审裁判确有错误,后者是检察机关“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一个是“认为”,一个是“发现”,从用词上可以看出,再审抗诉在对“确有错误”这一条件的把握上应当比二审抗诉更为严格,这主要是因为再审抗诉涉及到如何处理纠正错判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在最高检发布的5个指导性案例中,有3个属于二审抗诉案,1个属于再审抗诉案,还有1个同时涉及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包括法院判决未能正确把握证明标准、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罪名错误、量刑不当、遗漏犯罪事实与同案犯等多种情形,彰显出检察机关全面、充分地行使抗诉权的必要性。5个指导性案例为检察机关如何运用好刑事抗诉职责、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提供了具体指导。
二、指导性案例对刑事抗诉条件和标准的正确把握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作了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仍然有相当的难度,这也是造成刑事抗诉案件数量少、质量低的重要原因。最高检发布的5个指导性案例在抗诉的准确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一)关于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根金线。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行实体处理的活动均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在传统上,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明标准,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从而形成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可以发挥与“疑罪从无”类似的功能。“疑罪从无”被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机关处理疑罪案件的基本准则。 在某种意义上,“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意味着裁判者在综合审查全案证据之后,如果仍然存在合理怀疑,那么,他就只能遵循“疑罪从无”的理念,按照“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原则,作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疑罪从无,应当是公安司法机关穷其努力,仍然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时的一种处理。
在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是第一审判决未能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错误地将有罪判为无罪。刘某某辩称其车内毒品为其朋友周某(举报人)所留,一审法院基于刘某某车内毒品可能为周某所留的“合理怀疑”,作出了刘某某无罪的判决。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刘某某与周某之间的关系及其经济往来情况,梳理刘某某的社会关系和5起毒品犯罪关联案件,排除了刘某某车内毒品为周某所留的合理怀疑,并进一步夯实了刘某某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证据基础。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有罪,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刘某某无期徒刑。司法机关正确把握刑事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有罪与无罪的准确认定。在该案中,被告人从一审被判无罪到二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两次判决可谓天壤之别,检察机关通过补充证据,排除了犯罪为其他人所为的合理怀疑,保障了刑事裁判的正确性,防止了有罪的被告人逃脱法网。
在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中,同样涉及司法机关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正确把握问题。在该案中,被告人宋某某停车走到人行道上睡觉时被发现,进而检测出其血样酒精含量超标;宋某某的小轿车涉及一起交通肇事案,造成被害人张某轻微伤。一审法院以宋某某危险驾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其间有其他人驾驶车辆的可能性为由,判处宋某某无罪。在该案中,宋某某辩称其小轿车由“魏某”驾驶,而“魏某”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属于典型的“幽灵抗辩”。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类似这样的“幽灵抗辩”并不罕见,给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提出了难题。在该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仔细审查鉴定意见、自行侦查补强证据,力图澄清其间有其他人驾驶车辆的合理怀疑。不同的司法鉴定机构对于视频监控图像与被告人宋某某的同一性鉴定,作出了不同的鉴定意见,基于此,法院一审、二審判决均作出了被告人无罪的裁判。在再审抗诉中,检察官发现了新证据——案发路面监控抓拍的影像资料,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影像中出现的小轿车驾驶员与被告人宋某某的同一性鉴定,得出了肯定性的鉴定意见,从而使全案证据更加确实、充分,排除了其间有其他人驾驶车辆的可能性。再审法院据此裁定撤销原判,改判原审被告人宋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该案例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证明标准的把握,法检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新证据的发现往往是破解僵局的关键之所在。检察机关积极充分履职,可以有效避免不经仔细查证而作出“疑罪从无”判决,错放真正的罪犯。
(二)关于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正确认定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在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是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错误地将抢劫罪认定为盗窃罪,从而导致量刑畸轻。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而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性方法,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这是抢劫罪区别于盗窃罪的重要标志,又使抢劫罪成为财产罪中最严重的犯罪。在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中,李某约见被害人荣某,并将其带至酒店,趁荣某昏睡之际,指纹解锁其手机,盗取支付宝账户内4000元。对于李某的行为,公安机关认为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认为构成抢劫罪,一审法院认定构成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11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检察机关通过破解被告人李某的电脑硬盘加密分区,发现了李某其他抢劫、强奸、强制猥亵线索,并查找了李某获取精神类药物的途径和方式,此外,还调取了饭店监控录像等,从而得出了现有间接证据能够证明荣某被投放药物后处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状态的结论,据此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以强制方法强取公私财物,构成抢劫罪。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20万元。该案例表明,正确认定此罪与彼罪,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的量刑。区分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关键在于是否使用了强制方法,在该案中,尽管缺乏被告人使用了强制方法的直接证据,但检察机关通过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对“被告人使用了强制方法”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证明,从而使该案的性质从盗窃罪改判为抢劫罪,并且带来量刑上的巨大差异。
(三)关于判决适用刑罚明显不当
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均属于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时,必须综合评价所有情节,判断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规定,但对哪些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刑事审判经验,应当判处死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定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后自首、立功、坦白或者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的;在共同犯罪中罪行不是最严重的,或者其他在同一或同类案件中罪行不是最严重的;被害人的过错导致被告人激愤犯罪或者有其他表明容易改造的情节的;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有令人怜悯的情节的;虽然极其严重罪行的证据确实、充分但具有其他应当留有余地情况的。
在严重犯罪适用死刑还是死缓的判断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赔偿谅解情节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中,一审法院基于赔偿谅解情节对王某作出了适用死缓的判决。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是第一审判决“量刑不当”,其中的重要争议点是“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以及“王某是否可以判处死缓”。检察机关经过深入调查,一方面补充了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的证据,包括犯罪的性质属于恶势力犯罪、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等,另一方面补充了赔偿附加条件、被告人并非真诚悔罪的证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当适用死刑的抗诉意见。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王某死刑。该案例表明,赔偿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于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的影响不是绝对的,需要结合案件的性质、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作出综合评判,司法机关不能因存在赔偿谅解情节径直对被告人作出死缓判决。
(四)关于对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处理
认定罪名不正确,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均会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在孟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等犯罪再审抗诉案中,一审法院对孟某某等12人以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判处10个月至4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检察机关以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且存在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同案犯的重大线索为由提出再审抗诉。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证人、调取证据,发现该案是涉及自然资源领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了补充、追加起訴,再审法院对被告人孟某某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非法采矿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2年6个月至2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李某等5人,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判处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1名公职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人实施的共同犯罪案件,是否涉黑涉恶,对于定罪量刑至关重要;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涉及一人犯数罪、多人犯一罪、多人犯数罪等复杂情形,只有进行彻查,才能为准确定罪量刑奠定基础。在该案一审程序中,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提出指控;后以原判决部分情节、部分事实、个别罪名认定不当提出再审抗诉;后又通过自行侦查,补充、追加起诉,还原了案件的全貌,从而实现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全面精准打击。
三、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所带来的经验和启示
最高检发布的5个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最终均达到了通过抗诉使错误的刑事裁判得以纠正的效果,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第一,检察机关对于一审裁判和生效裁判中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进行实质性审查,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如在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对赔偿谅解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发现了赔偿附条件、被告人并非真诚悔罪等情况,进而认为赔偿谅解协议不应当成为对被告人适用死缓的充分理由。第二,检察机关围绕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自行侦查,补充完善相关证据。如在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补充收集了关于被告人与举报人关系的证据以及刘某某社会关系的证据;在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补充收集了李某大量的类似行为证据以及从未患过精神类疾病却多次以失眠抑郁、癫痫疾病为由开具精神类药物的证据。检察机关通过补充收集证据,澄清了案件中的疑点,促使法院对原判决进行改判。第三,检察机关注重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抗诉意见。如在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一方面排除了刘某某车内毒品为周某所留的合理怀疑,另一方面通过举证证明了刘某某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主客观相结合、正反两方面相结合准确把握有罪认定的证明标准。第四,检察机关深挖关联案件,防止遗漏犯罪事实与同案犯,保障案件办理的全面性。如在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贩卖毒品案的上家为陈某,经报告最高检协调公安部,成功抓获了陈某,陈某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孟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等犯罪再审抗诉案中,检察机关不仅挖出了首犯孟某某的多项漏罪,而且追加了16名被告人,还开展了“破网打伞”行动。第五,检察机关对于查清事实后足以定罪量刑的抗诉案件,如未超出起诉指控范围的,建议法院依法直接改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36条的规定,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第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可以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检察机关对于案件事实已查清的案件,建议法院直接改判,减少了程序回流,有利于兼顾诉讼经济与人权保障。
在5个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检察机关行使刑事抗诉权,除了严格依法履职之外,也涉及能动履职问题,如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涉及恶势力犯罪,孟某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等犯罪再审抗诉案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国家曾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对于此类犯罪应当依法从重打击。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有时将魔爪伸向了未成年人,未成年人被迫成为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出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考虑,对于犯罪分子应当从严惩处;对于涉案的未成年人,还需要做好司法救助、安置帮教等工作,以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对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社会治安管理漏洞,检察机关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犯罪的源头预防与治理。如在案例中,检察机关针对城市房屋租赁监管、重点人员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问题和骗购精神类药物等管理漏洞,向有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延伸了审判监督职能和效果。
最高检发布的5个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刑事抗诉职责、提升审判监督质效,作出了鲜活的阐释,对于破解检察人员不愿抗、不敢抗、抗不准现象,改变抗诉案件数量少、抗准率低的局面以及重个案轻类案、重二审轻再审等倾向,能够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