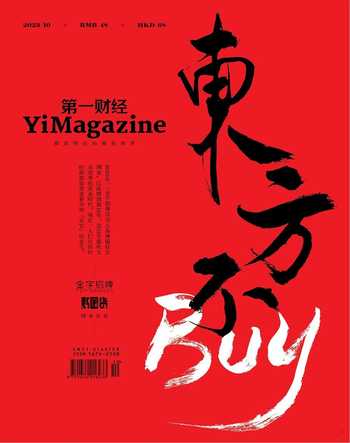解锁创造力的惊喜
王俊煜
最近有两个瞬间,觉得自己忙起来了。
第一个是前两天的一个中午,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晚霞预警”,说是今天傍晚会有超级好看的晚霞。想起春天的时候暂停工作,有好几次在颐和园看落日,坐在昆明湖边的长椅上,等着太阳走掉、星星出场,漫天的晚霞就是它们之间的过场。如果那时候的我看到这条“晚霞预警”,应该马上就抓上相机去颐和园了吧。
那天的晚霞的确刷遍了朋友圈。
第二个是前两天和朋友约在雍和宫见面,从办公室往外走的时候才意识到整个夏天我都很少到这条大街上来。其实办公室就在雍和宫旁边,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雍和宫大街或簋街。以前中午或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出去吃饭顺便散会儿步。现在,中午都不太舍得花时间出去了,因为觉得白天的工作时间过于宝贵,都是外卖解决。一个夏天过去,街上的店已经换掉了不少,甚至还新开了一家星巴克,我都没有发现。
7月初我们团队开始恢复工作,决定先动手探索“认真阅读”和AI的结合,再来看阅览室如何继续迭代。过去半年积累了许多和AI相关的产品主意,我们讨论了判断标准,并据此投票挑选出了其中4个主意,计划制作成产品原型,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让自己“眼前一亮”。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中两个产品原型的制作,正在做第三个。
第一个产品原型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内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的内测中,我们确认了这个产品的目标用户群体,也确认了它是能在这些用户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会被日常使用的。所以,我们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原型开发成可以正式上线的产品并推向市场。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
其他的产品原型,我们也在逐个推进。如上期专栏所介绍的,原型制作在这里是产品设计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一边写代码、一边试用体验、一边修改设计,将这些主意逐渐打磨成型。这里面的大部分主意如果能活下来,今后也可以整合进阅览室,这也是换了个思路在考虑阅览室的迭代。
我们聚焦在AI的应用,而不是底层技术上。这几个月仍然不断看到海外有基于AI的新产品或新功能发布,有一个AI产品的导航站目前已经收录了近万个产品。像ChatGPT、Bard、Claude这样的通用AI也在不断迭代,增强能力。即使这样,使用AI来开发新产品的机会仍然很多。如前几期专栏中所讲的,AI在今天已经能在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了,只是使用门槛还有点高。有时候和朋友交流,也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令我惊讶的想法,但前提都是他们自己对技术有一些了解,也愿意动手设计自己的工作流,而且日常使用中可能还需要手动去完成一些今天的产品还无法自动化的部分。这些对普通人来说都是门槛,那也就隐含了机会。整体而言,在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些可能被新的AI能力解决的问题,利用今天的AI技术扬长避短,设计出普通用户不需要学习理解AI的技术原理就马上可以开始使用、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际价值甚至惊喜的产品—这是我们这几个主意的共同特点。
这种创新是我们比较擅长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冒出各种新的和AI有关的主意,即使是限定在AI和“认真阅读”的结合点也是足够多的。怎么更快地把这些主意通过原型来验证,然后工程化并推向市场,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主要挑战。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内容品牌或创作者对内容和AI的结合感兴趣,我们也在和他们一起探索,这是另外一个切入点。
做事情的兴奋度和2010年做移动互联网时的兴奋度是类似的。而且,由于AI在能力边界上更模糊,在日常工作中能经常感受到“噢原来还能做出这个效果”的惊喜,看到自己的创造力被不断解锁、搭建出未曾感受过的使用体验,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很令人兴奋的。
当然,真的要和2010年比,个人的状态肯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多长了13岁呢。
那时候我刚毕业没有两年,单身,工作是唯一的优先级。显而易见是一个“工作狂”人设,可以通宵,可以睡在办公室。那时候行业还不流行“996”,但我坚持团队应该一周工作6天—如果可以把我们想做的产品提早20%让用户用上,为什么不呢?即使到了2016年,我还在明目张胆地说,每个人每周都应该工作70小时。
我现在理解了这其实是我的焦虑,也知道了这种焦虑来源何处,并接受了它。只是到后来变得越来越极端,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比如,到去年之前我每天都会记录自己不同工作的耗时,精确到分钟,再根据每个月的统计数据,来检查自己在工作上的时间是不是足够多、分配是不是足够合理。今年上半年暂停工作以后,在考虑如何恢复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想回到这种很焦虑的状态。
7月刚开始恢复工作时,我们对工作时间的预期都不高,而且那个阶段本来能专心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就有限,这和2010年相比显然是很大的区别,基本下午四五点钟就需要回家照顾各自的家庭。还是会因为整体的进度感受偏慢而感到焦虑。焦虑之下,一开始我会很直觉地认为还是工作时间不够长的问题。不免就会想念那个能沉浸在工作中很久很久的自 己。
但后來我意识到,其实本质不是工作时长的变化,而是优先级的竞争。仅仅谈论工作时长的话,如果不顾其他任何代价,像之前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并不是不行。我有一些已婚已育的男性朋友依然是凌晨两点下班回家;大家如果读了马斯克的传记,大概也会对他身上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有所体会,这是成为“工作狂”的代价(这个代价并不仅仅由自己承 担)。
比如说,今年春节后我的确有一阵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家里陪小孩和做家务,但后来重新请了钟点工,而且我爸爸有空的时候会来帮忙。现在,如果我想工作到深夜才回家,是有这个自由度的。但我一般还是会六点前到家,因为我认为能陪小孩玩耍学习两个小时是重要的。这对工作当然会有影响—按我长年累月形成的生物钟,下午四五点可能正是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
现在每天要起身回家的时候也还是会觉得纠结,这也说明我自己目前在优先级的分配上不够自洽,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工作的优先级,在实际中还是太低了,会轻而易举被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打断。我虽然也不觉得应该回到原来那种很紧张、焦虑的状态,而是应该更从容。但如果工作的优先级无法保证,经常会被打断,还是会觉得工作节奏过于松弛,甚至有些松垮垮的感觉。
但这些都是自己作的决定。既然知道了问题在这里,就应该知道其本质是自己对两个优先级的判断和选择,而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安排。那么,就应该更认真地看待在自己这里这两个优先级的竞争,做到更好地平衡。
从容、不焦虑对创造力有好处,但如果时间无法保证,就很难进入到创造力爆棚时那种能量满满的状态,而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说到这里,其实另一个每天要提醒自己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 上。
工作资历和我们类似的同龄人,现在多数从事的都是管理工作。即使是创业,同龄人多数也会选择资源型的创业方向,毕竟这是工作资历带来的更显性的积累。而我们今天的工作方式,是选择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动手做事情 上。
显然,如果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刚毕业时就能做好的简单工作上,是非常浪费的。当然,我今天对此也没有那么焦虑,因为简单工作带来的一些乐趣就像照着说明书拼乐高一样,可以带来确定的产出、快乐和成就感。作为恢复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我暂时对此有一些宽容。
但整体而言,还是需要更有智慧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其实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要去解决那些足够难又足够有影响力的具体问题。工作资历带来的无非是对方法论的积累和坚持,对我们来说,主要就是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的方法论,以及对自己持续多年关注的这个用户群体的洞察和直觉。放在我们现在的工作中,这就意味着以我们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应该能更准确地找到用户的关键问题,探索出和之前的解决方案相比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创新本身了。
我对此还是蛮乐观的。像是在这几个月对AI的探索上,我们自己当然很难去做一些年轻人社交、美颜之类的产品,但如何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用户问题,或者设计出别人没有做出来过的方案来解决用户的问题,我对此都是蛮有信心的。这也包括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的信心,对新方法、新知识的整合和融会贯通,这些都是个人能力会对业务很有帮助的地方。
一旦摸索出方向,就像现在的第一个原型一样,还是应该尽可能找其他人来帮忙,这样才能确保整体的进展。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