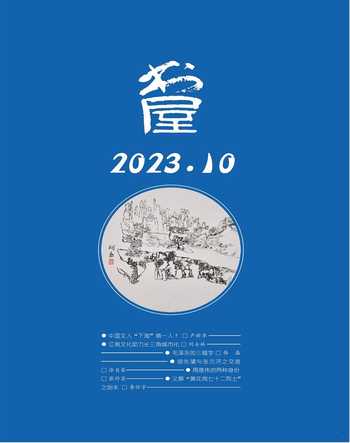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
一
“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非卢新华莫属。”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曾经常从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这种说法。我当时是从洛杉矶的中文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心想:这哪里跟哪里啊?发这样的消息为什么不找当事人查证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文人“下海”经商比我早的肯定多的是,怎么就能断定我是第一人?至少,黄宗英就比我早到深圳蛇口办公司,她的公司名称叫作“都乐文化娱乐公司”。我到深圳后,曾多次去蛇口看她,并向她请益。她也告诉我,“都乐文化娱乐公司”的“都乐”一词,是取自赵丹先生的“天下都乐”一语。
后来,我又看到国内的许多报刊在报道我在赌场当发牌员一事时,都想当然而且言之凿凿地说我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发牌”,有些采访我的视频背景通常也是拉斯维加斯的地标建筑。为此,我在面对一些平面媒体和电视台的采访时,曾着意加以更正,并明确地告诉采访者:我从未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发过牌,我的工作单位是“洛杉矶一家扑克牌赌场”。然而,我的更正从未受到任何一家媒体的重视。许多涉及我的报道,只要议论起我曾作为赌场发牌员的这段经历,都无一例外地仍旧将我定格于拉斯维加斯。这种像是串通好了一样的以讹传讹,渐渐地也让我时常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怀疑,甚至有时做梦也会感觉自己真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上班了。
但有时心里忍不住又要想:也许不仅是此事,过往的许多事情,恐怕也会有相同的遭遇吧。人们想要的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剧情、数字和细节罢了,至于是否完全失真或有所失真,似乎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从来都是这样的,我心里想,也就一点点释然了。
二
我大约是在“下海”去深圳创办公司的七年前就认识黄宗英了。虽然就年纪而言,她是属于我父母亲辈的,但后来却成为我比较亲近和熟识的朋友。当然,我认识她还是通过她的丈夫——我的南通同乡、著名电影演员赵丹。
大概是1978年的9月或10月吧,那时,我的小说《伤痕》已经于当年8月11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于上海《文汇报》,不仅搅动了文坛,也搅动了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以至于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当天的《文汇报》破天荒地加印到一百八十万份,各地转载和改编《伤痕》为广播剧以及各种地方戏剧的也很多。同时,读者来信也像雪片一样不住地从全国四面八方飞向《文汇报》编辑部,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7711信箱——只因小说在《文汇报》发表时,编辑曾在我的名字后面注有“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字样。
而我能够与赵丹先生结识,则又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女演员,如今已九十一岁高龄的陈奇先生牵的线。
那是《伤痕》发表不久后的一天下午,陈奇在复旦小礼堂有个讲座。其间,她声泪俱下地为师生们朗诵了《伤痕》,结果引得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讲座过后,陈奇通过认识我的学生找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对我说:“赵丹有意拍《伤痕》,还决定任导演,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如果有,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伤痕》如果能拍成电影,当然可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而且,导演又是这么赫赫有名的电影界前辈,求都求不来的,我当然同意,便满口答应了。
陈奇于是对我说:“那好。这样,我今天回去后就跟赵丹说一下,安排你们尽快见个面。”
记得是接下来的周日的下午,两点半左右的光景,我先是来到淮海中路上的一个弄堂口与陈奇见面,然后便由她引领着走进弄堂,来到新康花园内一處小别墅的二楼。赵丹先生大约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拜访,早在客厅里等候。客厅的门敞开着,我们上楼还没踏进门,就见赵丹已从沙发上站起来,但一见我,却显然愣住了,有些惊讶地道:“啊,你是男的啊?”我只能对他笑笑:“不错,是的,赵老师。”嗣后也告诉他,因为《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是女性,很多读者都误以为我就是王晓华,写的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遭遇。我所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很多人都直接称我为“新华大姐”或“新华小妹”。所以,他以为我是女性,一点也不奇怪。
赵丹于是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只有涉世未深的顽童才有的而且似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的大笑,很有感染力,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一个才刚刚入学一个多学期的大学生,与一个电影艺术大师间的距离。继而,等他知道我是他的南通小老乡后,就更不把我当外人了。自此,我经常会到新康花园赵丹家中去,除了商谈有关《伤痕》的剧本改编和成立摄制组事宜之外,也会一起谈天说地。有一天,赵丹很高兴地告诉我,上海电影制片厂相关领导已经同意并批准成立拍摄电影《伤痕》的摄制组,由他亲任导演,杨延晋任助理导演,我和黄宗英任编剧。这样一来,我更成了赵丹家的常客,遇上吃饭的当口,黄宗英更让我不要客气,自己从碗篮里取碗盛饭便是。她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和蔼可亲,和我也很谈得来。这样,我不仅和赵丹夫妇越来越熟稔,渐渐地,也认识了他们的女儿赵桔,儿子赵佐和赵劲。赵桔那时在外地读书,很少回家。赵佐和赵劲比我年龄略小些,还在上学或上班,见得也不算多。多数时候,我都是和赵丹以及黄宗英两位老师接触和交谈。一次,我忍不住问赵丹:“除了《伤痕》,你还计划拍些什么影片啊?”
他听后,略想了想,两眼放光地看着我,兴致勃勃地说起来:“我这一生中还想演的人有四个。”说着,他扳起手指,对我细说道:“其一是闻一多,其二是鲁迅,其三是李白,其四是周恩来。”说得兴起时,他还放了一段他演周恩来的试妆影片给我看,还真有些像。但忽然,他的情绪变得有些消沉和郁闷起来。我猜想,那大概是他也听到了有人反对他出演周恩来的传言吧。忽然,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取过身旁挂在墙上的一把剑鞘,抽出鞘中的长剑,学着李太白的样子,摸了摸下巴下方想象中长长的胡须,又摸了摸剑锋,然后举起长剑上下左右挥舞起来,嘴里则念念有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忽然,又敛住万丈豪情,将剑锋由上而下用力一按,仰天长叹道:“唉,可惜啊,真是可惜,抽刀斩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我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和经常童言无忌、率性而为的言行举止中,感觉到在他乐观、豁达的外表下,其实掩藏着一颗郁郁不得志的内心。他也常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他也不再谈《伤痕》的话题,似乎都已经将拍电影的事遗忘了。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到学校找我,要我尽快去他家一趟。见面时,我发现他一改以往的达观和直率,先是欲言又止,继而又有些愤愤不平地道:“小卢,很遗憾,不瞒你说,拍《伤痕》本来是厂里已经决定了的事,可厂长不知从哪里听到市委里面有不同意见。这几天他才刚刚打听清楚,原来是市委主要领导人对《伤痕》有不同看法。所以,今天已经正式通知我,要我们下马了……”
我听后,一时无语。我一个学生,第一次触“电”未果,也很正常。但回过头想,我虽有所失,却也有所得,至少交了赵丹和黄宗英这样两个忘年交,于我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尤其因为黄宗英也写作,她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故我们常常也会就写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探讨。后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我与他们夫妇俩再次见面,发觉赵丹穿了一件比较短的紧身夹克衫,戴一顶鸭舌帽。我于是说:“赵老师,你这身装束看上去也只有四十出头。”他听了,看上去很开心。谁人不喜欢年轻呢?但很可惜,后来会议期间我再未遇到他们。原来,那时赵丹已在北京检查出得了癌症,后病逝于北京。
赵丹逝世后,黄宗英曾从北京给我拍过电报,让已经回到复旦的我去北京参加赵丹的追悼会。可惜,大约学校考虑到我那时的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准假。
我那时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尽管我一直不知道是谁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的。我也是第四次文代会作家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代表,还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因此,在学校里,我经常会被安排接待外宾。开始时,来访者主要采访我个人,有外国记者,也有精通中文的外国专家和学者,男的女的都有。我后来曾见到过相关的采访被刊载在日本的《读卖新闻》上,也有被摘录在《参考消息》上的。其中一位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林教授,还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留学。他没有食言,此后几乎每年都会给我寄入学申请表。可我一次也没有填写过,主要是我从个别渠道了解到,像我这样得过国家级“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人,有关部门基本上是不会放的。但想要通过留学去好好地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却也由此萌生。尤其,有一次在复旦大礼堂看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载着宇航员登陆月球的影片,让我对美国科技水平的高度发达印象极深,又想到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更在心中将留学美国作为我人生的目标之一了。
接待外宾多了,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我基本上已有所了解,通常回答得都比较得体。但这一来,也引得管外事的校领导经常安排我接待一些并非专为访问我,而是来学校参加交流和学习的外宾,基本上一周不少于两次,接待地点均为物理系二楼。这样一来,我大量的学习时间被占用。于是,我通过系领导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减少或取消我的外宾接待任务。此事后来得到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夏征农的同意。
北京电影制片厂因听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伤痕》的计划流产了,遂派出他们的文学编辑张翠兰到上海找到我,说他们厂里已将《伤痕》列入拍摄计划,并决定要我亲自改编剧本。为此,他们通过正规途径,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向复旦大学发了一封公函,替我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伤痕》搬上银幕又指日可待了,我心里当然也很开心,也就不再计较会耽误学业了。
张翠兰老师于是协助我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选出那些比较典型的,逐一登门进行家访。为节约时间和精力,十几个读者中我们有一半以上都选择了属于上海地区的读者,但最远也去过福建三明市和安徽某地。然而,很遗憾的是,虽然得益于这些采访和我们之间一次次地交换意见,我拿出了电影剧本改编的第一稿,却又听闻《伤痕》和“伤痕文学”被视为“缺德文学”,北京电影制片厂于是马上偃旗息鼓,刀枪入库,不再提拍摄《伤痕》一事。
后来,形势又开始好一些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也来找过我,提出拍《伤痕》。但他们的计划还没出来,就再一次胎死腹中。
中国最大的也是实力最雄厚的三家电影制片厂,三次计划拍摄《伤痕》,三次流产,让我在失望之余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伤痕》和“伤痕文学”有社会大众和文学界的大力支持,但现实生活中,我也不能不承认,围绕“伤痕”所引发的各种争论,其实也依旧是《伤痕》的“伤痕”,即便整个社会都在为《伤痕》叫好,但细细观察便可得知,大多数人的身上依然戴着“伤痕”的镣铐,只不过轻重不一而已。
三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我算得上是早的了。
有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如“一鸣惊人”“洛阳纸贵”等,几乎都可以用到我身上。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除了《伤痕》总拍不成电影外,我后续所写的一些作品,也常常会被退稿或腰斩,或砍头去脚。因此,虽然我浪得大名,心里其实充满挫折感。
我就有些灰心。于是,当我看到报纸上有不少政界、学界的人士“下海”经商的报道后,忽然受到启发,也萌发了“下海”经商的念头。
大约是1984年底或1985年初吧,有一次在上海文艺会堂开会,中场休息时,我们几个年轻作家、记者和编辑走出会议室,坐到绿茵茵的草地上闲聊,我于是提出由上海文艺界同人共同发起,成立一个“上海文化服务公司”(暂定名称),跳出体制,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构想,马上得到不少人的响应。
见大家积极性挺高,于是,我便对写话剧的Z道:“你年龄大一些,做事也比较沉稳,你来牵头好不好?”
马上就有人鼓掌,表示这个提议很好,但Z却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连连说:“不行,我不行。我身體没你们好,做生意很累人的,吃不消。”
于是便有人说:“新华,这事儿是你先提出来的,还是你来牵头做吧。”
就这样,在文艺会堂外绿茵茵的草坪上,一共有十三个人参与组建“上海文化服务公司”,其中包括作家P、X以及C等。
后来,为能尽快注册公司,我以记者身份来到静安区工商局了解具体的申办条件和流程。工作人员告诉我:首先,办公司必须有公司法人,且明确说明,在国家企事业单位担任公职的人员不能担任法人,其次还需要有注册资金等。
这第一条一下子就将我们难倒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公职和单位的。
“除非我们当中有人辞职来当这个法人,否则这事就黄了。”有人气馁地说,并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我。
我明白,考验我的时候到了,事情因我而起,如果我这时不迎难而上,也打退堂鼓,不仅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也会凉了大家的心。于是,我心里暗下决心,要辞去《文汇报》记者的公职,不再抱着“铁饭碗”不放,而要去好好地闯荡一番江湖。同时,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虽然当过兵,在工厂做过工,也下乡插队落户当过农民,并且曾是一个大学生,但在“工农兵学商”这五行或五种经历中,唯独缺“商”。因此,为丰富我的人生阅历,积累创作素材,“下海”经商对于我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知行合一,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遂向报社领导递上辞呈。
大约那个时候,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报纸上也不断地在宣传“发家致富”光荣,而我的辞职要求也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故很快就批下来了。与此同时,报社还给我发了一张红皮的“《文汇报》特约记者证”,欢迎我在经商之余随时给报社写稿,一经刊用,会按相关规定发给稿费。
本来这之前,我已经单位同意,请了一年创作假,由上海作协发工资,潜心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不用上班的日子是很惬意的,但时间长了,人也变得有些懒散,早上常常会睡懒觉。
但筹办公司又让我的生活找到一个新的着力点。我每天除了修改自己的《森林之梦》,所思所想都是和筹办公司相关。我也读了不少商业方面的书籍,研究市场,研究管理,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地由外行转变成内行。在一次筹备会议上,我被十二名作家、记者和编辑公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我当即表态:囿于自己在经商方面还没有经验,是个外行,我只当董事长,总经理可以先兼着,将来若有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会马上让出来。
很快,公司注册地点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还好,不知是通过谁的关系,我们了解到靠近南京西路石门一路附近的南汇路上,有一户人家刚刚落实政策,退赔了一间约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便找上门去,提出和他们合作办公司。这家人好像只有母女两人,吃过不少苦,听说我是《伤痕》的作者,马上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房子需要装修,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利用工作之余主动跑过来帮忙。尤其C,干活最卖力,他穿一身雨衣刷油漆的场景多少年后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有一次我们开会讨论公司的人事安排,X为副董事长,C为广告部经理,P好像是人事部经理。会上,C激情澎湃地谈了他有关在公共汽车上甚至是直升机上做广告的大胆构想,其想象力之丰富,出乎许多人意料,一时弄得大家都很兴奋和激动,摩拳擦掌,大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在商海鏖战中“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和冲天干劲。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完全亮,我的房门上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我被敲醒后,心里很奇怪:“谁呀,这么早乱敲门。”揉着眼睛走到外间去开了门,才发现是C。他那时家住浦东,很远,要坐渡船摆渡才能到浦西来。我将他让进里间,在沙发坐下,忍不住问:“有什么急事啊?这么早!”
他两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后,才一脸严肃且郑重地说:“我昨晚一夜没睡。我想好了,我要当副总经理。”
“昨天会上不是讨论过,你当广告部经理吗?”
“广告部经理我可以兼着,但我还要当副总经理。”他大约属牛的,上了牛脾气,坚决地说。
我一时无语,也不知他内心究竟怎么想的,就委婉地说:“你当副总经理也不是我个人就能决定的,需要再开会讨论。不过,我倒是要提醒你,根据你的特长和志趣,做广告部经理其实很适合。当然,你的要求我会在董事会上提出来,可你想过没有,别人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大家会怎么看你?”
他就不吱声了,稍稍坐了一会儿,便悻悻地走了。
而我这时心里最着急的事,还是迫切希望能早一些找到一个合适的总经理,同时抓紧完成公司的注册手续,否则,一切都还是纸上谈兵。
有一天,X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叫CP,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又说,他还是某智囊团最年轻的成员呢。我听了很高兴,就让X约CP一起见个面。
见面地点就约在CP家中。
见面后,CP又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位来自深圳云兴公司的朋友L,是退伍军官,转业前在部队当连长,现任深圳云兴公司总经理。CP又介绍说他对《孙子兵法》特别有研究,并出版过《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当然,他也向L介绍我是“伤痕文学”的“鼻祖”。于是,大家一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遂达成口头协议,CP辞职,加入尚未注册的“上海文化服务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同时,CP作为总经理的头等大事便是促成“上海文化服务公司”与深圳云兴公司在各方面的紧密合作。L则承诺,我们拟成立的公司的开办费用和注册资本将由他们公司垫付,待公司开张营业盈利后再行偿还,并表示当晚回宾馆后,他就会打电话给财务部门,让他们先期汇款十万元到CP名下。他后来听说我预备辞职,但尚未办手续,遂建议我将工资和人事关系暂时挂靠到他们公司。他们公司是国企,是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设立的一个窗口,这样可以无后顾之忧。我同意了。同时大家也商定,L第二天回深圳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办公室主任发函,由云兴公司出面邀请我和CP以及X到深圳考察访问,进一步洽谈合作事宜。
那时的深圳已很亮丽,晚上灯红酒绿,一切看上去都很光鲜,几乎已是一个不夜城,和从飞机上俯瞰黑乎乎的夜上海大异其趣。大家于是都很兴奋,感觉着时代正在向我們招手,而我们也将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和弄潮儿。但对于CP和X来说,令他们更感到兴奋和激动的是在深圳晚上还可以通过卫星天线收看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两人劲头十足,常常要看到凌晨两三点才肯入睡。我虽不反对,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看看,但多少也有些担心他们会沉湎于此,影响工作。
在深圳云兴公司的支持和资助下,最终我们决定在深圳蛇口注册了一家“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但公司甫开业,内部就发生矛盾和分歧。主要是有一些董事看不惯CP的做派,觉得他手上有钱后,几步路的距离也喜欢喊出租车。更有人觉得他的做派像个花花公子,这样的人当总经理,将来很可能会“豁边”。于是,就有人要求我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召开董事会,将CP和相关人等清除出去,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尽管我对CP的一些做派也有看法,但又觉得他能说会道,谈吐不凡,有高屋建瓴之势,心里很矛盾。思考再三,公司好不容易注册成功,内部马上就闹分裂,这肯定不好,不但会损害我和几个作家以及记者、编辑之间的友谊,而且我虽初涉商海,也已发现,要在这个道上混,即便我不骗人,也保证不了哪一天不会被别人骗。这样,在一次董事会上,我郑重提出离开刚成立不久的“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同時一并辞去我的公司法人身份以及公司董事长职务,并表示,自己是“净身出户”,自此不再拿公司一分钱的薪水。
因此,算起来,1985年年底,是我不到两年多时间里第二次从单位辞职。第一次是《文汇报》,这一次则是“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我曾经想过重新回到《文汇报》工作,并且也和原文艺部负责人史中兴谈过,后来也得到报社总编辑马达的同意。但我后来还是没有回去。
四
尽管离开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后,我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但通过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汪逸芳的帮助,我预领了一笔一千元的稿费,又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报名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那时还不是大学)的“出国培训班”,开始一门心思攻读英语,以期能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托福考试,实现好些年前心中就已经萌生出的出国留学梦。此后,常常有人看到我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着扶手,一手捧着一个小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小本本,专心致志地背英语单词。《文汇报》文艺部有一位当年一同分配进单位的毕业于北大的同事X,其时正负责“文艺百家”的评论版,他见我经济上颇为拮据,便约我每周为他的版面写一篇一千多字的书评,至于写哪本书则由他选择,我可以不署真名。我当然愿意,但都写了些什么,一篇能拿多少稿费,已记不清了。
现在想想,那时留学之于我,其实已不再是一个梦,而是一种逃避。
混迹商海一年左右后,我最大的收获便是身心获得一种少有的释放,可以自由地思考,可以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去生活,不再有一个上司随心所欲地差遣我,我也再不需要跟着许多人一起去时时刻刻揣摩其他人的意图。同时,我也讨厌自己虽然从控制下解放出来,却又不得不为赚钱养家而苦恼。
所以,回顾往事,尽管“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非卢新华莫属”的说法不准确,但在“下海”后呛了几口水,急急忙忙爬上岸,马上就转身投入“留学”大潮的文人第一人,恐怕还是非我莫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