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大地之爱
殷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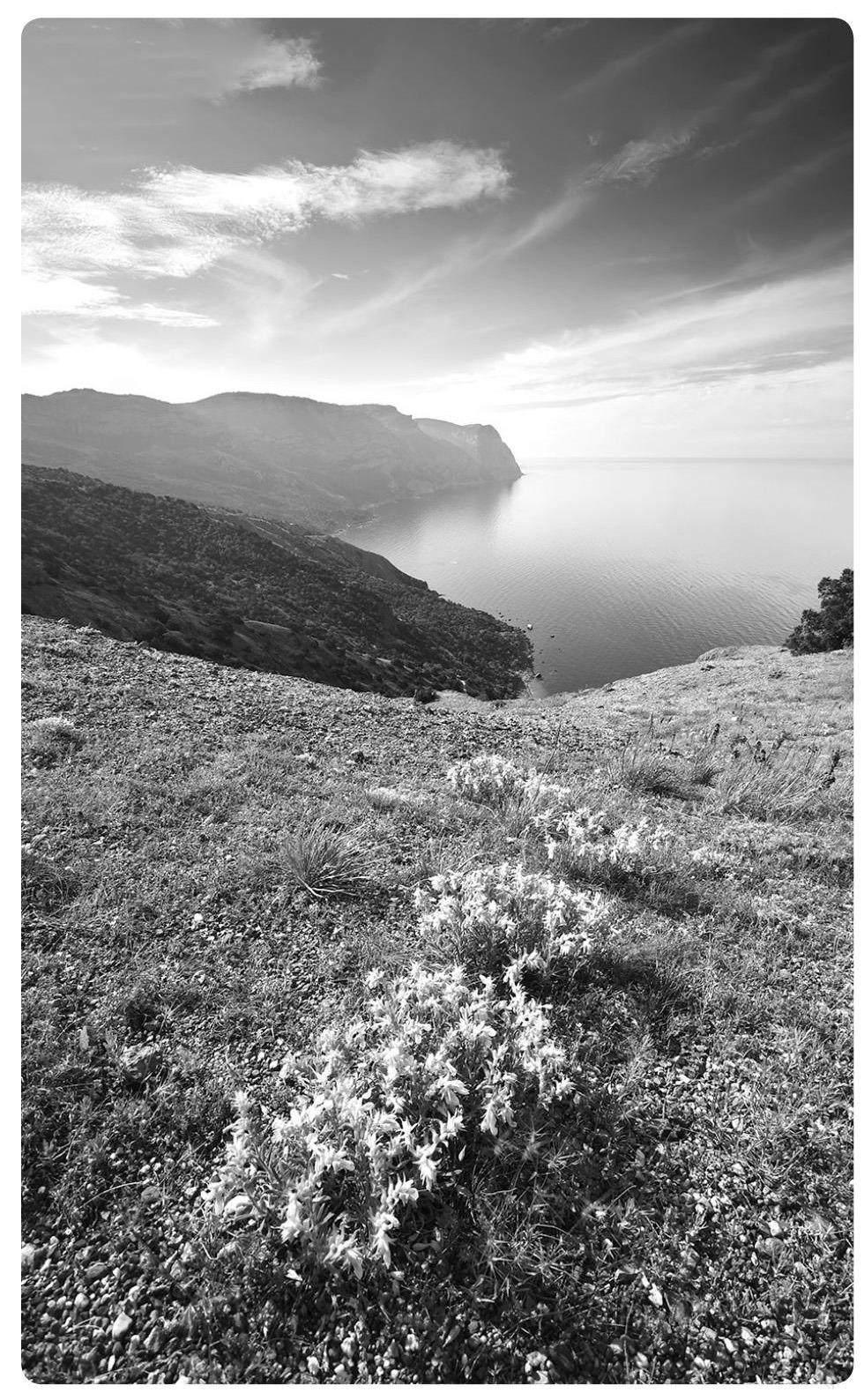

迟子建,中国东北地区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迟子建的作品都展现出她对东北大地的热爱。她的小说和散文,诗化语言风格明显,节奏和词语排列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她始终追求内心真诚细腻的体验,扎根广袤的东北大地。她对中国传统语言的诗化风格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用语言书写自己忧伤而又带有希望的内心世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存在。
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今漠河市)北极村。她于十八岁开始文学创作,扎根东北大地,至今已经发表了超过五百万字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有的评论家从美学意义上对迟子建的小说进行了审美概括—宁静、纯净、悲悯情怀。东北大地的坚硬和萧瑟造就了迟子建宁静而悠远的内心,而人生路上的种种遭遇给予了她细腻而忧伤的情怀。
迟子建生活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作为最富特色的东北作家,她的所有作品都体现着她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最深沉的爱。
迟子建出生在中国最北部,冬天的皑皑白雪和广袤的孤寂给予她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养分,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精神土壤。当她遇到任何难题时,那片皑皑白雪和童年时就感受到的孤寂就成为她日益成熟的心灵慰藉。汪曾祺说过,语言是接近一个作家最可靠的途径,母语是一个人最惯常的思考和表达方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母语,包括了很多中国地域内的地区语言、惯常语言形式。文学作品是文字语言的表达,可以想见语言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性。迟子建说过,中国的小说语言并非今天这样,它特别讲究平白、有韵味和对语言的推敲,遣词造句特别精细,而现在的小说语言特别乱。她在《秧歌》中这样写道:“日子飞快地流逝着,逝去的日子全然不知道都去了哪里。那逝去的风雨云霞亦不知去了哪里。反正又到了天高云淡的日子,灯盏路的两旁的杨树又显出单调来,但灯盏路的路面上确实热闹的。那些金色的落叶覆盖着路面,秋风掠过时,它们就飞旋起来互相撞击着,好像一群无忧无虑做游戏的孩子,有时那落叶调皮地落在人的头发上,人去了哪里,它就跟着去了哪里。”“逝去的日子”“那逝去的风雨云霞”“又到了天高云淡的日子”“又显出单调来”……看得人眼前闪过了人影、树影、光影,好像在书里和秋风做伴,和落叶相依,多美!
在迟子建的创作中,故事性好像不是第一位的。她试图在创作中传承中国叙事文学抒情的传统,弱故事、弱人、弱矛盾。她关注生活,在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和归纳中,体现自己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平凡生活最真切的热爱。
迟子建说,她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生活。如果我们单看迟子建的小说,情绪大都来自具体的生活场景。在《旧时代的磨房》中,这个时代风起云涌,而四太太的复杂经历被作家津津乐道,作家一直在描绘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她的希望,她的失望,她的绝望。
在《重温草莓》中,迟子建这样写道:“有雪的日子,炉膛里的火苗总是活跃的。母亲站在锅台那儿烙饼,父亲就像少年一样举个酒盅在旁边说笑着什么。他常常打趣母亲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并且老是调侃母亲年轻时快乐得过于丰满而现在却变得疲倦了的胸脯。我和姊妹们在里屋窗前看雪,常常被他们的笑声搅扰了那平静。”眼前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东北普通人家最平凡的冬日,一生相伴的父母笑着,说着,孩子们看着,这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最简单的热爱。
在《亲亲土豆》中,丈夫得知自己已经到癌症晚期时,给妻子买了一件宝石蓝色的旗袍;而妻子在丈夫去世后,给了他一座土豆墳。死亡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作家却说这座坟“洋溢着一股温暖的丰收气息”。丈夫在世时,土豆是夫妻二人的热爱,而“土豆坟”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写到了极致,大概就是那种“我爱什么,你一目了然”的最高境界。土豆是迟子建记忆中最平常的食物,她在多年后依然清晰地知道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时候该收,怎么才能在一垄地里摸到最好的土豆,还有关于土豆的亲情。所以,她在《亲亲土豆》中赋予了土豆那么深的含义,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有了自己深切的情感。
在《日落碗窑》中,吴云华在翻新棉裤,“又回到炕上翻新棉裤,一缕棉絮精灵般地飞起来……吴云华抖了抖未絮好的棉裤,惹得棉絮飞得更欢了,她就像坐在棉花飘飘的场院里,让关小明望去有些朦胧”。在迟子建的笔下,普通如棉絮,也可以飞起来像精灵,只有心中无限美好的人看到最普通的事物才能感受到最纯粹的美。虽然吴云华在责备儿子的不务正业,但是在儿子的眼中,飘扬的棉絮在面前飞舞,让这个心中有着无限希望的人好像看到了跳舞的精灵,母亲在他眼前都是朦胧的形象,母亲的责备进不了耳,而棉絮进了眼,在充满希望的人眼里一切都是美的。简单而纯粹的美好在最简单的生活场景中,这是迟子建建构的自己的文学世界。在其中,我们一眼看去就知道作家是深爱着东北这片土地的,因为炕上和场院这样的场景,都是东北大地最广袤的农村最普通的场景。作家赋予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和场景最深沉的爱。
迟子建的语言是温情的,可以让读者明确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浪漫。在《五丈寺庙会》中,她写道:“放河灯的人听见乌鸦的叫,都抬头张望着。只见那乌鸦向着栖龙河的下游飞去,它的头顶是一满圆月,而脚下的迤逦的河灯,这天地间焕发的光明将它温柔地笼罩着,使飘飞的剪影在暗夜中有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我们仿佛看见了圆月下那最深刻的活人对逝去的人的悼念,因为远去的乌鸦带走的是希望和逝去的祝愿。在这个场景中,意象组合形成意境,即由多个意象构成一幅生活图景,形成一个整体意境。而在其中选择乌鸦这个意象,既是迟子建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是自己语言艺术的再次体现—因为诗化的中国语言,从不避讳好坏。
乌鸦是一个传统的意象,从“枯藤老树昏鸦”开始,乌鸦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就是不祥的征兆。在迟子建的作品意境中,乌鸦既是逝去的人的,又是带着希望的远去。所以,她在《遥渡相思》中将死亡进行消融,将死亡写成了“沾染了白色的花朵”,而失去母亲的痛苦是“苍凉的音乐”,是“穿黑衣的人在春风中流泪”。因为迟子建心中满怀温情,所以在文字中她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哭和悲痛。
迟子建作品的语言风格来自她对故土最深切的爱。在《原始风景》中,迟子建谈到她的一个奇想,“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装在桦皮篓中,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月光燃烧得无声无息,火焰温存,它散发的春意持之永恒”。为什么对月光如此执念?迟子建这样解释:“我生于一个月光稠密的地方,它是我的生命之火,我的脚掌上永远洗刷不掉月光的本色,我是踏着月光走来的人。”迟子建的作品就像东北黑土地的史诗,她用最纯正的北方方言,告诉你这片大地上的风土人情,说给你听普通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到了情绪最热烈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爱。所以,加格达奇、西林吉、漠河……是她的故事发生的地方,鄂伦春人是她的主角,漫天飞舞的大雪是稀松平常的景色。
迟子建是从《北极村的童话》开始构建的东北黑土地,她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都让她在一众作家中别具一格。她曾这样概括作品中的人物—“小人物的巍峨”,她从平凡人身上体会不一般的情感,对小人物的描写和体会即是对平凡人最深的感触。
迟子建作品的语言风格在2002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2年之前,迟子建的作品是温情的,对生活是饱含希望的;2002年之后的作品却充满了哀痛和悲伤。迟子建的爱人因车祸离世,突发的变故颠覆了迟子建的人生,她觉得“整个世界的天平倾斜了……整个的街和平时的色彩都不一样了……”所以后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文中,作家以第一人称叙述,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芸芸众生中个人的和大众的那种彻骨哀痛,饱含着作家对底层平民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女主人公在魔术师丈夫车祸去世后,独自远行,语言之悲伤,可以看见丈夫突然离世后崩溃的迟子建自己,心中那种无法抒发和无法言语的痛楚。火车因山体滑坡中断,中途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在那里,她目睹苦难、不公和死亡的集中出现。在乌塘所有的寡妇里,蒋百嫂的痛苦最显而易见,最外放,“蒋百失踪后,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三天两头就去酒馆买醉,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也变得很浪荡了,隔三岔五就领男人回家去住”。她喝醉了就去一个会唱民歌的民间老画家那儿,听又悲又没歌词的小调儿,并且还会哼上几曲。蒋百嫂还有一出近乎神魂颠倒、神经错乱的异常举动,就是一到停电就开始大闹,扬言“要用炸药包把供电局给崩了”,并且“跟疯了似的四处奔走呼号,绝不肯在家里待一刻。而一旦室内电灯复明,她就奇迹般地安静下来了”,暗合了煤矿里暗不见天日的环境,她走不出来。蒋百嫂的痛苦在这个绝望的小镇如影随形,“笑容像晚秋原野上的最后的菊花”,孤寂地唱着人世间至纯至美的悲凉之音……一个满怀绝望的女人,遇到了一群绝望的寡妇,迟子建笔下描绘出来的这群绝望的女人身上,一如既往地承载了她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她对普通人身上痛苦的深切同情,又何尝不是在抒发自己的感情?在看遍人间苦难之后,女主人公放下自己心中愈加感觉微不足道的苦难,开始了新的人生。迟子建的温情,就体现在她总是给人以活下去的希望。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方式有很多,她用自己的文字语言给人一种最直接的呈现方式。
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迟子建开始更多地关注苦难,用语言表现人类的苦难,用文字救赎她笔下的人物和她自己。读完《额尔古纳河右岸》,笔者感受最多的就是爱、宽容和救赎,都是爱和被爱的人间。伊芙琳的那一段话最可以概括这种感情,“我看透了,你爱什么,最后就得丢什么;你不爱的,却能长远地跟着你”,这种想得而不到,不想得却相伴的,不就是最简单的人生!人生中有希望就会有失望,有得就会有失,有想得就会有得不到,只有尝遍人生苦痛的人,才会有如此清晰的体会。
最近的《群山之巅》中,温暖和诗意减少了很多。迟子建将更多的笔触放到了现实,让笔下的人物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涉及生存、爱情、犯罪和人的救赎。迟子建的作品之所以有诗意的退却,是因为作家人生感悟的深切,让作品更加贴近现实,语言风格更加简单。
我们依旧可以在迟子建的作品中看到东北大地的群貌:海拉爾、根河、呼伦贝尔大草原……她依然扎根于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她的语言诉说着她对这片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的热爱。迟子建的作品字里行间充盈着诗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字节奏的把握,对祖国大地和生活在祖国大地上人民的热爱,都构成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深的根基。
在文学史上能够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作家,都极具地域特色和个人情怀。迟子建深爱着她脚下的这片土地,深爱着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她愿意用她擅长的方式来表达她内心深沉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