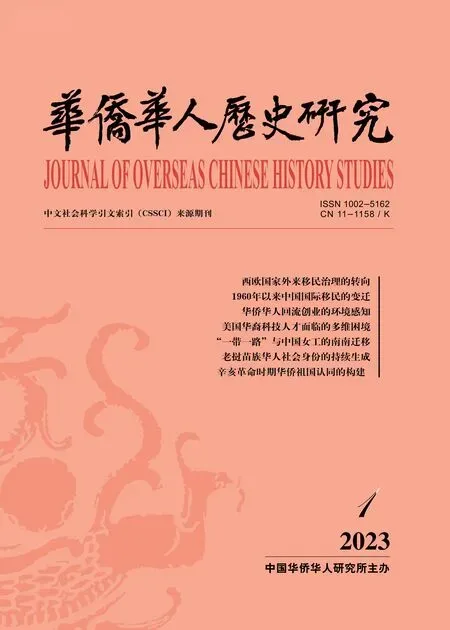19世纪古巴华人苦力问题新探*
——基于西班牙外交官玛斯的研究
张宇晨
(北京外国语大学 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北京 100089)
19世纪中叶,尚被清政府称作“日斯巴尼亚国”的西班牙,继英、法等国之后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而首先出现在两国外交交涉议程之上的却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颇为重要的华工问题。彼时仍是西属殖民地的古巴,因为这一问题与中国建立了最为紧密的联系。大批被冠以“苦力”之名的华工背井离乡,被送往美洲,正是他们在打开中外外交往来新局面的同时,书写了全球互联互通历史的崭新篇章。
开创中—西(班牙)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西尼巴尔多·德·玛斯(Sinibaldo de Mas, 1809—1868)同样也是最先开始处理中国同古巴之间苦力贩卖问题的西班牙外交官。作为西班牙首位驻华特命全权使臣①在西班牙文版《中西和好贸易条约》当中,特别提到玛斯是作为西班牙驻华特命全权使臣签署的条约。参见: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2, Miscelaneous series, No.30, Shanghai: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908, p.1085。,玛斯参与并主导了早期中拉苦力贸易问题的处理与谈判。[2]有关中拉之间苦力贸易问题的研究,重点往往在华人所蒙受的欺骗与虐待之上,而从事苦力贩卖的另一方——如古巴及其宗主国西班牙,则是邪恶与贪婪的施害者。从苦力问题的历史影响来看,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往往会忽略近代以来各国之间不断调适、磨合的过程。
玛斯在1868年4月结束驻华使节工作自北京返回马德里的途中,曾写信②这封机密信件(copia confidencial)便是本文所使用的珍贵一手史料,来自于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有关中国移民前往古巴的集合档案。这份文件共计334页,其中也包括英、法两国同清政府草拟的《续订招工章程条约》西班牙文手抄副本。整份档案之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驻华外交官玛斯的手稿信件,总长58页,后文引用页码将从该信件首页开始计算,西-中翻译由笔者完成。给西班牙国务大臣,希望不必通过复杂的行政程序直接同政府决策人沟通“华人移民”③玛斯在信中往往用“移民”(inmigrante)或者“垦殖者”(colono)来指称苦力。问题。在信中,玛斯通过不同国家面对华人苦力问题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深刻分析了英、法、美、西等国在自身社会、经济、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也通过这封亲笔信向世人证明,对华条约的谈判,特别是涉及苦力贸易的各项条约,不仅仅是协约签订双方相互博弈的过程,更成为西方各国相互逐力的舞台。这封信件长达50余页,言辞恳切并且多处“引用”与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谈话和书信沟通。[3]此时的玛斯已经离开驻华使臣的岗位,仅作为对前序事件的解读,他的这封亲笔信内容是可信的。遗憾的是,这份重要的外交官手稿档案一直没有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关注。④中外学者在对苦力贸易问题进行研究时没有引用过玛斯的这份手稿,也没有学者分析西班牙是如何得以短暂冲破当时的英、法“霸权”,参与到《续订招工章程条约》的修订当中。据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西尼巴尔多·德·玛斯”的词条当中记载,玛斯是自行辞去驻华使节职务离开中国的,但是在手稿中,玛斯对谈判中途不得不离华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也断定其后继者一定无法完成捍卫西班牙利益的使命,想必玛斯的离华并非“辞职”这样简单。由此可见,这份手稿对于研究早期中西关系史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这份文件中,除了辨明事情原委、分析各国态度外,已经离任的玛斯仍旧在向国务大臣描述自己对修订华人劳工出国章程方面的设想,这样的举动并不能单单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在剥削华工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结合这位西班牙外交官在1841—1843年针对当时的西属殖民地菲律宾所呈交的另外一份“秘密报告”(Informe Secreto),⑤玛斯有关菲律宾群岛的情况报告出版了共计三卷,最后一部分因为涉及“内参”信息,西班牙政府原本要求对这一内容不予出版,故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但随后这部分内容终究还是以第三卷的形式获得出版。可以看出,玛斯对于“华人移民”问题,除却“压榨”劳动力之外,另有更深层次的考虑。[4]或许对他而言,华人移居古巴甚至可以改善西属殖民地的境况与结构,从而改变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份外交官的手稿进行挖掘与研究,这同时也会有助于人们系统理解玛斯本人的思想与政治愿景。当代研究者们不仅可以重新将苦力贸易的发生与斗争置入世界互联互通的历史格局中来思考与审视,同时也会看到,在极具国际视野的西班牙首位驻华使节心中,中国移民如何担负着改变西属殖民地、西班牙乃至世界格局的重任。
一、拉丁美洲华人苦力问题的出现
自19世纪起,受《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影响,从非洲运送至美洲的黑人奴隶数量逐渐下降,①《废除奴隶贸易法案》通过之后,为了保证所谓“公平”,英国要求、监督甚至威胁拉丁美洲各国同样废除奴隶贸易,以使这些国家在劳动力的问题上不会因为蓄有奴隶而有太多“优势”,如英国迫使巴西签订的《英巴协定》,就禁止在1831年7月以后进口奴隶到巴西,参见本杰明·吉恩和凯斯·海恩斯著,孙洪波等译:《拉丁美洲史:1900年以前》,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其中“第十章 种族、国家和自有的含义”有对废除奴隶问题的具体论述。众多依靠奴隶劳动维系农业生产、资源开采的美洲国家爆发了人力危机,西属古巴也在此行列。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数家英国公司开始充当中间商,大规模贩卖中国苦力至美洲从事劳作与生产。这些中国人大多是在被招工代理欺骗、逼迫甚至绑架②西班牙驻华使臣玛斯对此的解释为:“‘南美洲的移民代理人’来到中国,找寻移居者,他们会去找那些底层民众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但是,由于‘移民’之事对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来说太陌生了——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移民,所以很难找到自愿前往者,逐渐就演变成了用欺骗形式甚至诉诸暴力迫使就范。”参见:Sinibaldo de Mas, Expediente General sobre la Colonización Asiática en Cuba, Ref:ES.28079.AHN/16// ULTRAMAR,86,Exp.3.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1868, p.2。的情况下,签下一纸合同,被关押进船舱并运往海外,在漫长的航路上忍受恶劣的条件,[5]并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从事高强度的工作、遭受雇主的虐待。[6]在厦门、广州等口岸都曾出现过非常严重的人口贩卖案件,在被英国占领的香港、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③华工出国形成高潮的另一原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前后,闽、粤劳动人民在清统治者疯狂镇压下,大批逃往香港、澳门,出洋避祸。”之情形更是猖獗。[7]从表面看,华工必须要与招工所或雇主签订为期数年的合同,声称他们自愿前往海外务工,并以此获取相应报酬,与奴隶贩卖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经调查,华工所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往往多涉欺骗,招工过程也依然充斥着暴力。[8]然而,贩卖苦力所能带来的高额利润在“合法”名义的加持下,还是促使一众西方国家的中间商纷纷效仿英国公司,大肆开展苦力贩运——西班牙代理人在其中尤为活跃。
在拉丁美洲,从古巴的甘蔗、烟草种植到秘鲁的鸟粪采集,苦力都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185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在英国公司逐渐受到本国政府限制之后,苦力运输业务便日渐被少数西班牙集团所垄断。在1864年西班牙开始与清政府洽谈“和好贸易”条约之后,以西班牙殖民地古巴为首要目的地的苦力贩运变得更加猖狂。全球苦力贸易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其间,从中国运往古巴[9]和秘鲁[10]的华工数量最多。[11]在拉丁美洲,被像奴隶一般对待的华工苦不堪言,却往往求助无门;在中国,经历了亲人出海音信全无的民众怨声载道,甚至发起过数次针对“洋人”的大规模反抗活动。[12]这条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为起点、拉丁美洲国家秘鲁和西班牙殖民地古巴为首要目的地的苦力航线,承载了无数个中国家庭无穷尽的悲愤与泪水,不仅促使清政府,而且迫使一众西方国家不得不共同正视、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苦力贸易问题开始走出国界,进入全球视野。
1865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推动下,总理衙门开始同英、法两国驻华公使共同商定更为细致的招工章程——对招工程序、出海准备工作、劳工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合同期满后的安排等都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次年3月5日,即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三方在北京共同签订《续订招工章程条约》①海关总署“因思中国既有奸民略买人口出洋,即难保外国不有奸商揽买出洋转贩”,故特提出“速定章程申明禁约”。尽管《招工章程二十二款》对出洋务工各步骤均作出了规定,但从其内容可见,主要针对在华招工这一步提出了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在签订《招工章程二十二款》之后,总署又照会美、俄、布国提出澳门处“多有内地奸民拐骗抑勒承工,沿海附近民人,深受其害。该处现在尚未设有中国官员驻扎,实属无人照料”,所以禁止在澳门装载华工出洋。由此可见,此时清政府更为关切的是中国劳工是否自愿出海务工,是否了解所签订合同的内容,是否存在拐带人口之各项情形。(又名《招工章程二十二款》)。[13]鉴于清政府在与西方各国交往的过程当中一向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其他意欲招工的各国也应遵守新章程中的各项规定,当时,首当其冲受新条款影响的必然是苦力贸易最盛的西班牙。而西驻华使臣玛斯对这一条款的内容及其签订过程颇有一番极具国际视野的认识。
二、西班牙外交官玛斯手稿中的苦力贸易问题
玛斯在1844年作为西班牙任命的驻中国商务代办和总领事来到澳门;1847年,又被任命为首位特命全权使臣,负责与清政府进行贸易条约的谈判。②1846年,玛斯完成了第一次出使中国的任务并回到西班牙,菲律宾总司令致信西班牙政府高度评价玛斯作为驻中国总领事和驻华贸易代办为马尼拉商业委员会做出的贡献,参见Servicios prestados por el cónsul en China a la Junta de Comercio, Ref: ULTRAMAR, 431, Exp. 6,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1845-1846。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西班牙特任命玛斯为首位特命全权使臣。几经波折,他终于在1864年代表西班牙与清政府签署了《中西和好贸易条约》。尽管该条约三年后才正式被批准生效,但是,“各国所有已定条约内载取益、防损各事,日斯巴尼亚国官民亦准无不同获其美;嗣后中国或与无论何国加有别项润及之处,亦可同归一致,期免轻重之分。”[14]只此一条,便满足了西班牙的迫切需要——为中拉之间的苦力贸易提供更多法律和外交层面上的支持。事实证明,在1868年被西班牙政府召回马德里之前,玛斯一直都在为华工问题与清政府以及各国外事机构与外交人员联络、斡旋,这是中西、中拉早期外交史上的首要之事。
在《招工章程二十二款》广发各国驻华使馆后,[15]出于种种原因,法国驻华领事宣称新章程未获法国政府批准,需重新讨论条款内容,对其进行修订。③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法国使臣兰盟照会总理衙门,称前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于同治五年签署的《招工章程二十二款》因“内有本国不允准照办数条”,故而“续增条款所列已废”,还需要再与清政府商讨制定新的章程。而总理衙门则回复称,并不知法国驻华大臣同中国所签订之条款仍需法国政府允准方能遵行,且新修章程已经刊刻通行,不可出尔反尔。此后,法方坚持《招工章程二十二款》已废,坚持按照之前的旧招工条例行事,双方僵持不下许久。同治七年三月初九日,英、法、日(斯巴尼亚)使臣才为“原二十二条有碍招工,另新拟工章致总署照会”。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8~181页。此后,1868年4月,英、法、日(斯巴尼亚)三国驻华公使便共同呈交给总理衙门一份有关“中国移民问题”的草拟章程,希望用以代替此前由英、法两国在京使臣与总理衙门共同商定的《续订招工章程条约》。[16]这份新修条例递交至清政府之时玛斯还在北京履职,但是同月底便已准备卸任回国。由于时间仓促,玛斯直至同年6月20日才在回国途中从巴黎撰写长信给西班牙国务部长,向其详细叙述《续订章程》从英、法协商变成英、法、西三国制定修改方案的过程。可以说,是玛斯成功游说英、法驻华大使,是他打破在对华苦力问题谈判中的英、法垄断,让彼时苦力贸易正盛的西班牙在这一事件上同样拥有话语权——他本人也在信件中强调自己为此所做出的不断努力以及所体现的强大个人魅力。[17]玛斯在这封信函的事件背景分析当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与见解,详细描述了各列强国家在面对中国苦力问题、设计招工条款之时所抱有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一)英国对苦力贸易的限制举措
首先,玛斯承认,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引入华工的规模要比英国大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在劳工引进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
英属殖民地契约劳工的引进是由殖民地政府出资,并由一个或者多个驻扎在中国的代理人来实施。移民同殖民地政府的执政者签订协议,后者保留支付移民75银元的权利——当然,给他愿意支付之人。引入一位移民所需要支付的所有费用(一般来说,不会低于200银元)都是从殖民地政府经费或者皇家公共经费中支出。
因此,对于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当地政府来说,引入移民花费巨大,但同样之举对于古巴(当地政府)而言,几乎毫无花费可言,这就使得在英属殖民地根本没有办法像在西属殖民地那样引入如此大批的移民。[18]
按照玛斯的解释,英国是通过让劳工与英属殖民地政府直接签约的形式来对苦力贸易实施管理和限制。但是古巴——西属殖民地的长官却没有办法对当地的权势者实施真正有效的管制措施。作为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遗留的最后两块殖民地之一,古巴当地的大庄园主、大地产主无论财富还是权力都远远超过中央政权的管控范畴。这所体现的恰恰是西班牙和英国在管理其各自殖民地上的差异。实际上,英国和西班牙在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上的发展早已逐渐拉开距离,而如何管理海外属地、如何“利用”海外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成为双方逐力的重要因素,中国苦力问题自然也卷入了这种相互竞争乃至相互敌视的国际关系当中。而彼时的清政府,受时代所限,尚不能在纷争的国际局势中保全自身,对海外劳工的实际状况则既无从了解,更谈不上保全其合法利益。
而彼时的英国,面对西班牙苦力贸易集团的失控,与其说表示担忧,不如说表现出相当反感的态度,英国驻华外交官更是以苦力贩卖行径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引发动荡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停止中西之间的贸易。1866年同清政府签订《续订招工章程条约》的英国使臣阿尔科克(Rutherford Alcock,即清档中的阿大臣,1865—1869年任英国驻华外交使节)便最为反对西班牙苦力贸易。对于英国的敌对态度,玛斯十分了解,他知道英法在同总理衙门商议《招工章程二十二款》之时,所谓的规范招工流程、限制苦力贸易其实就是针对西班牙的,因为同样从事贩卖华工行当的英国并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玛斯特别谈到《招工章程二十二款》中第二十款的一项内容:“惟于领事官既经批准,或另有委员以该船尚有不妥情节,禀明地方官以为不宜出口,海关暂准不给红牌……”为了查验招工所是否合规、运输船只是否符合远航条件、华工出海是否自愿,按照新订章程,清政府应委派官员随时探访各招工机构,在之后1868年英、法、西三国共同呈交的另一份章程修订方案中,上述内容予以保留,可见玛斯对此并无异议。但是他对于“委员以为不宜出口,海关暂准不给红牌”却抱怨良多,因为在他看来,以英国彼时在华之影响力,断不会有官员敢阻拦英国招工船只出洋,但是西班牙则不同。玛斯深知,西班牙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位都是十分有限的。[19]另外,从玛斯的记述中也可侧面得知,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仍无力同西方殖民列强直接抗争,但对于西方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同地位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除了条约中的“红牌”问题外,与华工签订的用工合同,在玛斯看来,同样更加符合英国人的利益。
华工合同期限为5年,这也是英国合同一贯的时限。协约上还规定华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9个小时,若超时,就应按照双方商定的标准额外支付费用。这项条款对于西班牙代理人来说简直糟糕透了。在古巴的移民,如果每日工作9个小时,那么除了他们日常生活开销,每月会有4银元①原文中玛斯所用为dólar一词,清末在华流通货币中,这一词既可指西班牙银元以及俗称为“鹰洋”的墨西哥银元,少数情况下也可指美元。鉴于在收集到的苦力用工合同当中,西班牙语合同部分往往会以“比索(peso)”为工人薪酬计算单位,而在中文版本中则是以“大员”计,故指代前两者的可能性更高。的固定工资;但是工人们——按情理——肯定会在9小时工作当中尽可能地偷懒,好留着力气再去赚加班费。如此一来,大庄园的工头要么不得不逼迫工人们干活,要么就在9小时之外不断地付钱给这些中国人。这该死的政策不会对英国人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因为在他们的合同当中并不涵盖移民的日常吃穿用度,也没有固定工资,他们只是承诺工人,在殖民地将会依照自由工作的标准按工计酬。[20]
从今日之角度,签署工作合同、按时计工、按劳分配均属最基本的工作条件。尽管从玛斯的这段论述当中完全能够读到这位西班牙外交官员无理的辩驳,但是如果置入19世纪60年代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恰恰能够从中体会到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大大拉开了同其他欧洲国家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距离。以奴隶贸易为代表的早期近代极端父权制度便是以大英帝国为中心,先行消解,并逐渐蔓延至其他地区。虽然在苦力贸易的问题上仍深刻体现了一众西方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民众的剥削,但是沿袭了数千年的等级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英美是工人阶层、社会新兴力量最先崛起的地方,那么西班牙对于这一趋势的追赶却起步甚晚。正如奥斯特哈默在论述“鞍型期”问题时所言,阶级形成的大趋势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悄然蔓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21]曾长期依靠殖民地贵金属开采及农业经济红利的西班牙,在19世纪的工业发展方面也一直同英法等国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换言之,玛斯其实对于造成英西之间巨大发展差异的原因确有感知,那就是英国已经进入历史新时期,而西班牙还停留在传统的过去。
但是无论如何,为了切实满足古巴增加劳动力的需求,玛斯还是建议:首先,殖民地雇佣方应适当提高华工的薪资;第二,劳工在合同期满之后如若愿意,应当有一年时间考虑是否续约;另外,也应允许勤俭节省、存有余钱的华人可以在合同期结束之前返乡。[22]玛斯相信,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吸引更多华人前往古巴务工。玛斯所提出的这些修约建议或许是打动英、法两国代表,令其决定可以与西班牙共同商议章程修订的原因之一。合同期满续签——在英、法看来——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工被虐待致死的可能,而对苦力薪酬的增加,则或可降低古巴当地引入华人的兴趣。可以说,华工问题在正式得到本国政府的重视之前,确实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像《晚间邮报》(Evening Mail)这类报刊也对苦力贩运问题进行了多番报道。[23]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革命、信息传播革命得以让“中国情况”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人道主义关怀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各国、每一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样也是重要因素。
(二)美国人的虔诚与现实
如果说清政府勒令对苦力出国严加管控是源于民众不断发起的抗议活动,那么,许多当时并不牵涉进苦力贸易事件当中的官民,乃至一众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批评,在玛斯看来,与英文报刊“有偏差性”的报道以及美国驻华使节表现出来的坚决抵制苦力贸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玛斯在信件中告知西班牙国务部长,“美国在1862年2月19日颁布法令,彻底禁止契约劳工的运输活动。此后,俄国和普鲁士政府也颁布了类似的禁令。”[24]除此之外,玛斯也注意到,美国上议院在1867年1月16日还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所有从中国出发从事所谓‘苦力贸易’的船运都将受到美国人民的厌恶,这种反人性并且毫无道德性可言的行径,违背了现代国际法精神”,因此,所有美国人都应以阻止苦力被引入西半球为己任。[25]
实际上,早在1856年,美国驻华公使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就曾针对苦力贸易问题发布公开通告(Public Notification),提醒全体美国驻华官员,过去通过美国及其他国家船只进行的中国苦力运输“充斥着非法、不道德和令人反感的暴行”,很多签下契约之人“被强行绑架,被暴力地带到他们不知道的国家,并且永远不会回来”。[26]最早以公理会传教士和医生身份来华的帕克非常关心苦力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充满了对贩运行为的深恶痛绝。即便如此,也不能单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待帕克及美国政府对苦力贸易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谴责和反对。面对海外华工的悲惨处境,彼时如美国一般并没有如此依靠苦力劳动从事生产的西方国家,除却悲悯之情,也在为“外国”之名被污名化而担忧,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中外刚刚发展起来的友好贸易关系。帕克在他的公开通告中便阐明了这样的担忧。[27]
玛斯在信中提到,如帕克一般同样身兼传教与外交职责的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多次写信给他探讨苦力贸易问题。1866年4月25日卫三畏曾写道:“看到这样的贸易还在进行让我感觉很难受,这些可怜的中国人,被迫工作、惨遭奴役,我认为,如果西班牙了解这些事实,就应该采取行动来杜绝这种恶行。”[28]作为著名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创办人之一,卫三畏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在西方世界非常有影响力;对中国语言和传统的认识让他在清廷也非常有威望,如果他对于华工的认知与言论都是如此这般,那么西班牙必然百口莫辩。因此,玛斯认为,对其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便是在驻华外交人员及所有其他在华外国人中间降低苦力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角度来说,玛斯清楚前往古巴务工之人并没有被当做真正的“自由民”来对待,但是,他很有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在古巴的华工彼时所遭受的虐待。①从19世纪40年代直至50年代末期,西班牙驻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外交人员常常由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人——担任,例如,英国商人泰特(James Tait)在1846—1859年间就担任西班牙驻厦门的副领事,在此期间他也曾兼任德国和葡萄牙驻厦门外交官。泰特自己也在经营苦力贸易业务,从中获利无数,德国便是由于这一原因辞退了他。但实际上,在泰特之后,西班牙派驻厦门的西班牙籍外交官同样延续了这一做法。他们不仅为苦力登船开绿灯,更向政府汇报“移民”登船时的兴奋与满足。这样的信息或许干扰了玛斯的判断。参见:Mònica Ginés-Blasi, Exploiting Chinese Labour Emigration in Treaty Ports: The Role of Spanish Consulates in the “Coolie Trad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6(1)。他在信中对西班牙国务部长抱怨,认为中国官员之所以对华人在古巴的境遇抱有错误观念,完全是受到了卫三畏以及英、法驻华外交官的唆摆。
(中国官员)应该去查明真相,我跟他们说,在福建和广东有几位中国人都在古巴待过,每年还有更多人回来,很容易就能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我还知道,在上海便有一个中国人曾以劳工的身份去过那个岛(指古巴),我可以自己出钱接他来北京,亲笔致信,送他去总理衙门,他们(中国官员)可以亲自考察一下,看看在古巴有没有强迫中国人成为基督教徒等行为。这就可以说明,那些外国人所描述的在古巴奴役中国人的行为根本就是夸大其词。[29]
在玛斯眼中,他国人士之所以如此“诋毁”古巴的苦力贸易,完全是出于“竞争”这一原因。英国之所以希望切断西班牙运送苦力前往古巴之路,因为同在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多巴哥和英属圭亚那同样需要大量的亚洲劳动力。[30]美国人也一样“务实”,1853—1854年,驻华专员汉弗莱·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曾建议美国政府务必要阻止中国苦力的输出,因为美国的农业生产会受到雇佣“廉价中国劳动力”的拉丁美洲竞争对手的威胁。[31]如果任凭苦力贸易继续下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将会受到挑战。
着眼19世纪后半叶的美洲,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力量角逐甚为明显。从独立战争时期开始,美国便不断从英、法、西等国控制的区域获取领土,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因此,无论从经济收益角度还是话语权的角度,美国都在全力排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可以说,华工所引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和苦力贸易国两方之间的纠纷,更是体现了彼时各个列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矛盾与制衡。
三、玛斯的殖民地改革计划——不可或缺的“中国移民”
在被派往中国之前,玛斯曾受西班牙政府资助游历东方各国,在学习各国语言与文化的同时,留心各国动态并向西班牙政府呈交具有一定政治价值的研究报告。他曾于1840年9月至1842年初留居菲律宾,在菲各处行走、观察、探访,并最终写成了三卷本的《菲律宾诸岛情况报告》(Informe sobre el estado de las islas Filipinas),其中不仅对菲律宾的历史、人口、地貌、物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记述与讨论,还特别呈交了一份“内参报告”,供西班牙政府内部研究、制定相应政策。[32]
玛斯对西属菲律宾进行调查与研究之时,西班牙摄政王埃斯帕特罗(Baldomero Espartero)所领导的改革主义政府正计划为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建立新的管理体系,这让支持国家革新的玛斯倍受鼓舞,写下他对于殖民地现状的研判以及对改革的设想。[33]对比旅行期间亲眼见到的英属印度,玛斯认为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非常低效,他甚至认为,如果西班牙不改变殖民策略,那么就该还殖民地以自由。[34]而他所提出的策略之一,便是在殖民地强化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以保持各方力量势均力敌,靠“制衡”之术保证殖民地的稳定。[35]
在包括玛斯在内的众多西班牙人眼中,西属美洲殖民地在19世纪初的独立是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反叛的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混血人)的助力。长久以来,殖民地社会阶级固化问题严重,被统治、受压迫的印第安人及混血人群本就对西班牙中央政府全无好感。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决定殖民地管理者人选之时,往往倾向于从宗主国派驻人员前往美洲,而非选择当地上层人士,这样的“偏私”不免让一众土生白人精英心生怨怼,再无对母国的血缘归属之情。西属美洲各国的反抗运动大多就是由这些克里奥尔人领导并最终实现独立。类似的情形在菲律宾也已出现。19世纪初,经历了数次本土战争的西班牙,既无力通过强权保证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无法指望殖民地对宗主国自发的忠诚与维护,唯有效仿古巴、波多黎各——西班牙仅剩的美洲殖民地——的模式,或可保全对菲律宾的掌控与拥有。[36]
古巴和波多黎各在历史上都曾大量引入非洲奴隶,这一举动似乎反而保证了当地种族构成上的平衡,白人、印第安人、黑人及混血人群的形成使得各方势力得以相互制衡。在菲律宾的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颇多矛盾与竞争。玛斯观察到,菲律宾本地人认为,自己比具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地位更为优越,因此地方管理者的职位往往被菲律宾人占据,但是,中国移民逐年到来,混血儿数量不断增长,玛斯将其视为可加以利用确保“西班牙旗帜”在菲飘扬的方法,即确保在各行各业、各个种族之间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让殖民地社会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才是宗主国稳固统治的有力手段。[37]
在此之后,玛斯被任命为驻华使节前往中国。但是,无论身在何方,玛斯从未放弃过对西班牙殖民地进行改革的愿望。1850年,玛斯曾递交西班牙政府一份提案,提议让中国幼童移居菲律宾以补充该地日益减少的人口,[38]这或许是玛斯对改变殖民地人口结构、谋求“种族平衡”所作出的一次努力,但是这一计划最终也完全没有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①玛斯非常关注欧洲列强国家在中国开展的外交和经贸活动,面对“天朝”(el Imperio Celestial)门户的被迫开启,这位西班牙外交官洞察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西班牙对中国的认知非常有限,并且缺乏应有的兴趣。在最后一次来华担任西班牙全权使臣之前(1864—1868),玛斯利用他停留在欧洲的岁月(1851—1863),记录下了他对中国政治和国际现实的分析。他一共出版了三部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作品:《英国与天朝帝国》(L’Angleterre et le Céleste Empire,1857)、《英国、中国与印度》(L’Angleterre, la Chine et l’Inde,1858)、《中国与基督教列强》(La Chine et les Puissances Chrétiennes,1961),但遗憾的是,这三部作品都是以法语书写并且在巴黎首先出版的。事实上,这三部作品很有可能是19世纪西班牙人所撰写、出版的有关中国最为成熟的作品。但是,它们在彼时的西班牙基本不会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英、法等国已经燃起过中国热潮甚至热潮都已逐渐被蔑视所替代之时,在西班牙仍旧几乎没有什么与中国相关主题的文本。这也更加说明,玛斯的学习及游历经历让他更加偏向作为一个时下的“欧洲人”去思考与行事,而非一个对中国仍漠不关心的“西班牙人”。而玛斯对于古巴也秉持同样的态度:要么改革,要么离开。
19世纪中叶,曾经得以在独立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西属美洲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也不断陷入动荡之中。《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影响逐渐显现,古巴不仅陷入劳动力短缺,失去“种族平衡”更是加剧了当地的危机。想必这位西班牙外交官也曾怀揣最后的希冀,期待通过外交交涉让“中国移民”大量移居古巴。华工的到来在实现补充岛上劳动力的同时,也能够产生改变古巴人口结构、平衡各方势力的效果。或许这便是玛斯不同于西班牙同期其他外交使节、愿意通过改变华工待遇以尽可能获取更多移民的原因。①在玛斯担任西班牙驻华全权使臣期间,西班牙驻上海、厦门等地领事馆同样也有外交官将苦力问题呈报西班牙中央政府。例如,1861年年底,时任西班牙驻厦门领事的法拉尔多(Tiburcio Faraldo)便就苦力贸易问题向西班牙国务秘书进行陈述,声称运送中国移民前往古巴务工的行动已经暂停超过一年,且没有任何恢复运行的迹象。在报告中,法拉尔多也根据自己对苦力问题的分析向西政府进行解释,其中导致苦力贸易难以继续下去的种种恶行皆为中国代理人乃至中国工人所为。甚至这位外交人员还不断发问,为何在中国本土之时,甚至在马尼拉务工之时,中国人都是积极、本分而又吃苦耐劳之人,但是到达古巴的中国劳动力却集体丧失这些优秀的品质……参见:“Despacho de Tiburcio Faraldo al Primer Secretario de Estado,” Archivo China España, 1800-1950, consulta 26 de junio de 2022, http://ace.uoc.edu/items/show/531。
玛斯一方面积极分析英、法、美等国反对“中国移民”出洋务工的原因,揭露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古巴之间的苦力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国劳工同古巴庄园主之间的纠纷,也不仅仅是清政府同古巴乃至西班牙政府交涉上的矛盾,更多是沉浮于各西方国家逐力过程之中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玛斯也在尽力应对国际舆论对苦力贸易问题不断施加的层层压力,希望可以冲破难关,推动并实现华工“移民”古巴的合法化、制度化,以此拯救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甚至改变西班牙沦入世界末流国家的命运。在其1868年手稿的最后几页,这位已经卸任的驻华外交官仍在对移民章程进行详尽的设计。例如,针对不断被诟病的运送苦力船只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等问题,玛斯在“附录”中罗列出工人人均在甲板和船舱中分别应该有多少活动空间、每日多少饮食供应、船上通风情况等内容。玛斯试图用行动诠释送往古巴的“中国移民”不可或缺。
玛斯曾经在手稿中数次强调,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斡旋,英法两国才会同意将西班牙纳入谈判阵营当中,与清政府共同商讨中国劳工出洋务工条约的修订;[39]如若换做他人,结果将会大不一样。但是,玛斯未能再回到中国。总理衙门的确收到了英法西三国共同商讨出的修约章程,[40]但随后便因西班牙使臣不在京中而失去了西班牙在修订章程问题上的发声。由于清政府坚持按照原先既定的《招工章程二十二款》行事,而英法两国政府对此并不认可,1868年之后的华工苦力贩运曾长时间处于“无约相遵”的局面。现实正如玛斯在信中所言——后继外交官无法解决规范华工出国各项规章制度的问题。从太平洋航道以及古巴、秘鲁等地依旧接连不断地传出有关华工遭受凌虐的消息,而蓬勃发展的新闻业也愈发关注中国苦力在美洲的悲惨遭遇。②如在美国俄亥俄州发行的《辛辛那提探询者报》(Cincinnati Daily Enquirer), 1867年1月29日即报道了“苦力体系”;《哈泼斯杂志》(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1864年6月第29期对“苦力贸易”进行了描述与评论。不仅是在如美国、西班牙一般进行苦力贩卖的国家引起舆论关注,其他各国对于苦力问题的议论也激起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应。苦力贸易问题在国际引发的强烈反响最终开启了中国近代外交的新篇章。[41]
四、结语
尽管早在16世纪之时,商品的贸易、白银的流通、文化的交流便已贯通亚洲、美洲与欧洲,但是,彼时中西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仍然只是由单一航路所引导的一条东西联络线,是当时世界众多独立运转的联通体系中的一支。然而,在进入19世纪之后,“人类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广阔。古老的中心逐渐解体,许多地区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而是与新发现的更大的空间范畴——全球国家体系、国际贸易和金融网络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2]在此背景之下,以苦力贸易问题为代表,许多看似发生在局部范围的事件也都无法再以当事双方、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而是要放诸更加广阔的全球背景中进行分析。无论是废除奴隶贸易、英国工业化和劳动生产方式的改革,还是新教取代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美国与西班牙即将在太平洋展开权力的争夺……如何看待前往西属美洲从事苦力劳动的华工,需要参考上述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从苦力贸易的实际角度出发,以西班牙人为首的西方代理人贩运华工前往西属美洲,的确是为了解决《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实施之后当地劳动力缺失的问题。面对西方列强,清政府尽管软弱,但是也仍然在尽全力维护华工的各项权益。陈兰彬使团的调查以及总理事务衙门同西方国家的交涉的确加速了苦力贩运的快速衰落,“但却并非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移民输入国的经济体系中,对华人劳动力的需求已不复存在。”[43]不论是具有奴役性质的生产活动本身,还是西班牙外交官玛斯所秉持的依靠种族“制衡”寻求殖民体制存续的构想,都仍然停留在前现代思维之中,与新时代的需求格格不入。实际上,单纯依靠帝国决策者或者依靠某些群体对苦力贸易问题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同拉丁美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早便已扎根于纷乱的全球形势之中,也一直在映衬并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只有全球社会的整体向前发展方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西关系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5页。
[2]P. San Ginés Aguilar ed.,Cruce de miradas, relaciones e intercambios,Granad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pp.323-340.
[3]Sinibaldo de Mas,Expediente General sobre la Colonización Asiática en Cuba, Ref:ES.28079.AHN/16//ULTRAMAR,86,Exp.3.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1868.
[4]Sinibaldo de Mas,Informe sobre el estado de las islas Filipinas en 1842, Madrid: I. Sancha, 1843.
[5][6][14]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6~589,632,527页。
[7][11][12][13][15][16][40]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7、16~19、154~162、161~163、183~188、183~188页。
[8]《总署奏与英国会定招工章程二十二款经过情形折》,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二册),第154~155页。
[9]Juan Perez de la Riva, “Demografía de los culíes chinos en Cuba (1853-1874)”, inEl barracón y otros ensayos,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1975, pp.469-471.
[10]Arnold Meagher,The Coolie Trade: The Traffic in Chinese Laborers to Latin Aтerica, 1847-1874, Bloomington:Xlibris, 2008, p.222.
[17][18][19][20][22][23][24][25][28][29][30][39]Sinibaldo de Mas,Expediente General sobre la Colonización Asiática en Cuba, pp.27-28,6,8,7-8,34,5,4,4,18,21-22,6,27-29.
[21][42][43]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6、190、126页。
[26][27]George B. Stevens,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Boston and Chicago:Congregational Sunday-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p.306, 307.
[31]Rudolph Ng, “The Chinese Commission to Cuba (1874): Reexam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om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4 (2), pp.39-62.
[32]N. Martín Alonso, “Un diplomático olvidado. D. Sinibaldo de Mas y su, ‘Informe secreto sobre el estado de las Islas Filipinas en 1842’”,Revista de Occidente, 1975 (148), pp.3-19.
[33]Josep M. Fradera,Colonias para después de un imperio, Barcelona: Edicions Bellaterra, 2005, pp.585-588.
[34][36][37]Sinibaldo de Mas,Informe secreto de Sinibaldo de Mas/Secret Report of Sinibaldo de Ma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uan Palazón, Manila: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1963, pp.84, 17-22, 26-28.
[35]Josep M. Fradera,Colonias para después de un imperio, Barcelona: Bellaterra, 2005, pp.299-322.
[38]Sinibaldo de Mas,Proyecto de repoblación de Filipinas con niños chinos, ES.28079.AHN/16//ULTRAMAR, 5162,Exp.24,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1850.
[41]陈晓燕、杨艳琼:《古巴华工案与晚清外交近代化》,《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