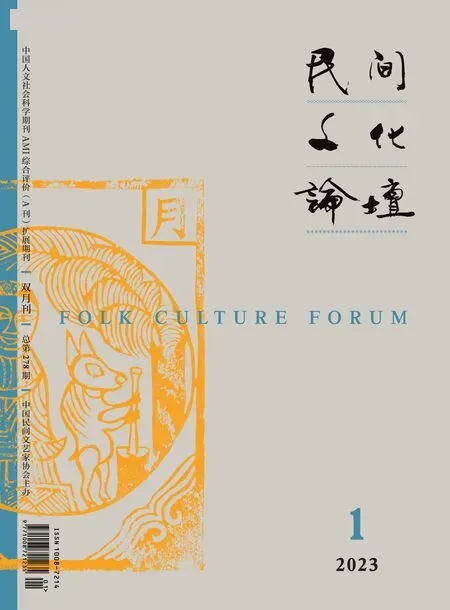灶神形象的认知与传说母题的生成
—— 以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为例
斯竹林
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流传于皖、豫、鲁、川等地,学者们将之定义为一种常见的故事类型,因侧重点不同,学者们的命名各不相同。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将湖南凤凰地区苗族中流传的这一传说称为“灶神故事乙”。①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将之称为“银器搬家”。②[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3页。丁乃通称其为“乞丐不知有黄金”型,③[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9页。高木立子称其为“分手的夫妻再逢”型。④[日]高木立子:《中国〈分手的夫妻再逢〉类型故事研究(1)》,《池州师专学报》, 1999年第1期。刘锡诚将东部从苏北、山东半岛到华北、东北各地,西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传的这一传说称为“张郎型”。⑤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438页。虽然名称各异,但传说中的母题有许多类同之处。由于传说异文中共有母题为“张郎休妻”,传说结尾都解释了灶神由来,笔者将之命名为“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
笔者认为,此类传说中的母题并非从故事类型中借用而来,而是围绕民间对于灶神的姓氏、身份、职责等认知生成的,有其独特的生成方式。
一、灶神“张姓”“妻眷”的认知与传说母题的“解释性”生成
(一)灶神“张姓”“妻眷”的由来
1.灶神“张姓”的由来
灶神张姓之说较早出现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⑥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页。据清代学者恽敬在《大云山房文稿》中的考证,灶神张姓来自古代张六星宿之说:“灶神姓张名单,有六女皆名察,以张为厨故,灶神张姓,张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从”。⑦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第76页。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恽敬认为,民间所传的灶神张姓由张六星之说附会而来。张文星,属于朱雀区域,为朱鸟之嗉,共六星。《晋书•天文志》载:“张六星,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饮食、赏赉之事。”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页。张六星宿主管的事务中,包含天厨饮食赏赉之事,与灶神主饮食这一神职相契合。
祭灶的缘起与饮食相关。《白虎通•五祀》谓:“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溜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②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7页。正因为灶与人之饮食相关,因而祭祀灶神。从祭祀的地点来看,明清之前官方祭灶地点一般在庙门外、郊外、御厨和宫中。而明清之际,祭祀地点基本上在御厨。《明史》载:“孟夏祀灶,设坛御厨,光禄寺官主之。”③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3页。言在孟夏时祭灶,祭灶由掌管酒醴膳羞之政的光禄寺主持,祭祀地点在御厨。《清史稿》记载:“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④赵尔巽等撰,许凯等标点:《清史稿(卷八四~卷一三0)》,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4页。言在大庖(御厨)前祭祀灶神,由清代掌管宫廷事务及帝后衣、食、住的内务府主持。而民间祭祀也往往在厨房灶间进行,送灶神的方式一般包括在灶台上备糖果、酒水,将灶马(灶神画像)贴在灶上,用酒糟涂在灶门上等,这与“灶主饮食”的观念是一致的。“灶主饮食”这一官方与民间的通行观念,与“张六星宿”之说契合,因而灶神被冠以张姓。
而据恽敬在《大云山房文稿》中的考证,张姓被冠以灶神的另一缘由与张角密谋代汉的政治目的有关。“《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窃骑刘天翁白龙至元宫,易百官。刘天翁,失治为太山守,是张角谋代汉之妖言也。”⑤恽敬:《大云山房文稿》,第76页。张角自托为张天翁,在民间制造了因刘天翁失守,张天翁将取而代之的说法,而灶神张姓也是其“妖言”之一。
灶神“张姓”之说被《酉阳杂俎》等书收录后,被各类书籍“纷纷传说”,并继续在民间流传。辽宁一带的跳神调《灶王爷本姓张》的唱词中,仍有张天翁与张姓灶神为兄弟的说法:“灶王爷,本姓张,住在上方张家庄。张家庄有哥三个,老大就叫张天师,老二就叫张玉皇,剩老三,上方他不坐,下方当上灶王。”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上),北京:中国ISBN中心, 1995年,第575页。这一唱词中明确指出张天师、张天翁(张玉皇又被称为张天翁)与张姓灶神的亲缘关系。张天师为东汉时期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陵,后人尊张陵为天师。这进一步证实灶神张姓可能来自张角的编造:张角自托为张天翁(玉皇),为张天师之弟,张姓灶神之兄长,他利用张天师与灶神在民间的影响力,达到密谋代汉的目的。
不仅如此,灶神张姓还出现在民间祭灶习俗中。旧俗重灶,大多数人家都在灶头立灶神神位,用红纸书写:“九天东厨司命张公定福府君之神位”。⑦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民俗志》,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同时,灶神“张姓”也进入“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成为灶神前身“张郎”的姓氏,影响着母题的生成。
2.灶神“妻眷”的由来
对灶神形象的描述初见于汉代。《后汉书》记载阴子方在腊月“晨炊”时见到灶神,对灶神“再拜”行礼。此时灶神是以单独形象示人,并未有妻眷儿女。
唐代《酉阳杂俎》中较早出现灶神“妻眷”之说:“灶神……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①段成式:《酉阳杂俎》,第77页。此说中,灶神有妻子,并且生有六个女儿。如上文所述,此说很有可能源于张六星宿之说。因张六星宿由六颗星组成,因而附会为灶神有六个女儿。
当灶神有妻成为共识之后,便出现了灶公之说。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描述了当时的“媚灶”习俗,并提及了“灶公”之说:“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②《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05页。明代时就已出现灶公之说,并且在日常口语中频繁使用,以此来指代直言无隐之人。
在民间,灶神与其妻被称作灶公灶母。这一共识不仅体现在民众口头上,还体现在灶神像上。民间的灶神神像一般有四种:除“独坐”(灶王捧圭而坐,常供奉于工商铺户),“端立”(灶王两旁各立一侍童,流行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通行的还有“双头灶”与“三头灶”。“双头灶”画中,灶王与妻并肩而坐,常供奉于百姓家中。安徽淮北一带,送灶前,在锅台上贴灶君像,“其中端坐长须的男像,谓之北灶像。有的是男女双人像,谓之蛮灶像。”③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民俗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可见淮北地区灶神像有男女双人像之说。“三头灶”画中,灶王与妻妾三人并坐,流行于冀鲁豫一带。山东潍县“三头灶”的灶王像中,一位灶公、两位灶婆坐于香案前,灶公居中,两位灶婆分坐两侧,香案上摆着面条、果品、酒水等。④王树村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绘画卷》,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一般家庭供奉的灶神像都是依传统延续下来的,不得随意更改。因此每年年画作坊制作的灶神像都体现了民间对灶神的传统观念。
由上,自唐代之后,对灶神形象的认知就包含了“张姓”与“妻眷”。这些说法可能源自民间,并在民间和文人群体之间流通。对灶神形象的“张姓”“妻眷”等认知,融入了灶神牌位中,也进入民间歌谣、民间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
(二)张郎“张姓”“有妻”的固有形象特征与传说母题的“解释性”生成
对灶神“张姓”的认知,投射到灶神前身张郎身上,成为张郎的固有姓氏。在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灶神前身在封神之前,绝大多数为张姓。一部分传说中直接点明灶神前身是一个姓张的人,或是出生在一户张姓的人家,于是邻里乡亲称他张郎。除张姓之外,有些传说中还有名字,如张幸福、张定福、张万良等。虽然名字各异,但均为“张姓”。
以灶神前身的“张姓”解释张郎封神的原因,由此生成了“张郎因与玉帝同姓而被封神”的母题。在民间观念中,张姓灶神与张天翁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因而在传说中,张郎被封神并非因其有功于人,而仅仅因为他与玉帝同姓:“玉皇大帝也姓张,一听是姓张的,便看在同姓同宗的份上封张郎做了一名‘灶王官’。”⑤刘锡诚编:《灶王爷传说》,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第9页。
有妻也是张郎的固有人物特征。有些传说中,张郎之妻在开头直接出现。另一些传说还解释了张郎娶妻的缘由:由于张郎命中犯败,要娶得一个“丑年丑月丑日丑时生的女娃”,“四丑”女是“八福命”,以“八福命”抵张郎“八败命”,才能守住家业不败,于是张郎父母为其娶妻。⑥同上,第36页。从而生成了“张郎娶妻”的母题。同时,以张郎有妻的属性解释夫妻封神的原因,从而生成了“夫妻投灶”的母题:张郎钻入灶中,其妻念及夫妻之情,也随之扎进灶膛自尽而死。于是张郎与其妻一起被人们供奉,张郎成为灶公、其妻成为灶母。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安徽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安徽卷》, 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8年,第728页。
在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灶神的“张姓”“有妻”成为张郎的人物特征,以对其进行解释或者以之作为缘由的方式,生成“张郎与玉帝同姓而封神”“张郎娶妻”“夫妻投灶”等母题。
二、灶神的“乞丐”身份与传说母题的“描述性”生成
(一)跳灶王仪式与灶神的“乞丐”身份
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张郎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乞丐。这一身份特征可能来自民间跳灶王仪式中的“灶王”形象。
一般认为,跳灶王中的“灶王”是由民间傩戏中“傩公”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傩公形象的发展来探讨灶王形象的演变。南宋时,傩舞分为皇城(禁中)和民间两类。禁中“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教坊使孟景初……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5页。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可见宋代皇城中,傩仪由亲事官、教坊使、镇殿将军、伶工等人装扮。且禁中傩仪所扮演的角色中,已经出现了灶神。
而在民间,傩仪又称“打夜胡”或“打野胡”,打夜胡的扮演者一般为贫者和丐者:“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③吴自牧∶《梦粱录》,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76页。“打夜胡”仪式由贫丐者装扮成妇人、鬼神等沿街乞讨,有驱祟之意,是驱傩仪式的民间形态。并且“打夜胡”所扮演的人物与宫廷中的人物大体相当,虽未提到灶神,但按照宫廷所扮演的角色,灶神应该也在“鬼神”之中。
清代,傩戏逐渐与跳灶王相结合,《土风录》也记载了跳灶王仪式:“自朔日至廿四日止,名曰跳灶王……称灶神曰灶王,见唐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辞灶王。’谓之跳灶王者,旧俗在二十四日,是日必祀灶,有若娱灶神者。犹满洲祀神谓之跳神也。后以一日不能遍改而先期,今遂以月朔始矣。装钟馗、灶神,即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以索室驱疾之遗意。又有扮作灶公、灶婆者。《秦中岁时记》云:‘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为傩公、傩母。’”④顾张思:《土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页。《退庵笔记》记载了作者家乡的跳灶王习俗:“此乃古傩礼之遗意。其装扮诡异,即方相氏所谓‘黄金四目’,《东京赋》所谓‘丹首玄制’是也。”⑤夏荃撰,徐进等校注:《退庵笔记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1年,第104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1.将灶神称为灶王,在唐时诗中已经出现。后在满洲俗语的影响下,将祀灶王变为跳灶王。这是跳灶王名称的由来。
2.清代之前的旧俗中,跳灶王仅在腊月二十四日与祭灶同时举行,目的是“娱灶神”。因一日之内跳灶王无法“跳遍”每家每户,因而改为从腊月初一跳到腊月二十四日方才结束。而傩仪从腊月初一开始,因而,在清代前后,随着跳灶王仪式时间的延长,它很有可能与腊月初一进行的驱傩仪式融合。
3.跳灶王中乞儿的扮相与傩仪中的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执戈扬盾”十分相似,因而跳灶王很可能是“古傩礼之遗意”。跳灶王仪式中的灶公灶母有可能从傩仪中的傩公傩母发展而来。根据《秦中岁时记》的记载,傩仪中有傩公傩母的扮演,与灶公灶婆的扮演大体相当。与傩仪结合之后的跳灶王仪式,不仅保留了灶公灶母的扮相,也延续了沿街乞讨的习俗。
《清嘉录》记录了当时的跳灶王仪式:“(十二月)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①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土风录》也记载了跳灶王仪式:“腊月丐户装钟道、灶神,到人家乞钱米……名曰跳灶王。”②顾张思:《土风录》,第9页。《退庵笔记》载:“又乡俗腊底,乞儿以蒲包戴首,用彩纸饰其上,状如高冠,手执春鞭,至人家跳跃不已。口唱吉语,连呼好好,谓之‘跳灶王’。”③夏荃撰,徐进等校注:《退庵笔记校注》,第104页。清代跳灶王时由乞儿扮演灶公灶婆,以蒲包戴首,饰以彩线,状如髙冠,手执春鞭,手持竹枝在门庭前喧闹,口唱吉语。手持竹枝在门庭前喧闹,乞钱米,时人多予以钱财,来“媚灶王”,祈求来年赐福。
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近代。浙江宁波在近代时仍有此俗,乡间跳灶王时,有乞丐头持剑念咒,另一乞丐手摇铜铃,喊:“抲,抲,灶王年年来,伤风咳嗽抲进麻袋里。”④周时奋:《宁波老俗》,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年,第 36 页。通过此种方式向各商铺讨钱,俗谓“跳灶王”。安徽地区的方志中也记载了这一习俗:“二十三日……街市乞丐跳灶(古之傩礼也)。”⑤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48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安徽北部地区仍然有跳灶王仪式。后来因改革开放之后,乞丐人数减少,这一习俗才逐渐消失。在跳灶王仪式的影响下,“灶神为乞丐”成为灶神的另一认知,并且进入张郎休妻型灶神传说中。
(二)张郎的乞丐身份与传说母题的描述性生成
灶神的乞丐身份投射到灶神前身张郎身上,成为张郎的固有人物特征。对于灶王前身“张郎”的乞丐身份,传说母题以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描述:
1.描述张郎乞丐命的种种先兆,由此生成了“张郎算命”“捡空谷”“捡板栗”“炸核桃”等母题
(1)“张郎算命”
有些传说中,张郎原本就是乞丐命。贫穷的原因是因为自身“很懒”“饮酒赌博”或是“爱抽鸦片”。而在更多的传说中,出现了“张郎算命”的母题:算命先生算出张郎命中“犯败”,载不住财,命中会败光家财,由富贵公子沦落为乞丐。⑥刘锡诚编选:《灶王爷传说》,第11页。
(2)“捡空谷”“捡板栗”“炸核桃”
不仅如此,传说中以“捡空谷”或“捡板栗”等母题来强调张郎乞丐命:张郎和妻子捡新谷或捡板栗,妻子捡的都是饱满的,而张郎捡的都是空的。于是妻子取笑他是叫花子命。“炸核桃”的母题也与之相似:张郎与妻子炸核桃,两人打赌,谁炸的核桃仁满,谁就有福气。结果总是妻子的仁最满。张郎不服气,说妻子享了他们家的福,于是妻子赌气说:“你既然认为我是享你的福,咱俩就离开,看看福到底是谁的。”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 2001年,第192页。妻子离开之后,张郎果然就沦为了乞丐。
2.描述张郎沦为乞丐之后的行为,由此产生了“排队乞讨”“夫妻相认”“失去妻子所给钱财”等母题
(1)排队乞讨
张郎沦为乞丐之后,四处乞讨,由此生发出“排队乞讨”的母题:有人救济乞丐,张郎前去乞讨。但讨饭的叫花子很多,需要排队。当张郎站在队尾时,就从队首发米;如果站在队首,就从队尾发米。结果“每次舀到他当门就没得了,饿得他头昏眼花打偏偏。”②刘锡诚编:《灶王爷传说》,第39页。这一母题其实是对“乞丐命”的再次强调:张郎在乞讨时仍无法摆脱“乞丐命”,连讨饭也讨不到吃的。
(2)与前妻相认
前妻再嫁之后,家境殷实,而张郎碰巧到前妻家乞讨,因此生成了夫妻相认的母题。在此母题中,前妻一眼就认出了张郎,而张郎往往一开始认不出前妻。有些传说中,前妻开始试图以首饰、面汤等旧物与张郎相认,但张郎却见面不相识,把妻子的首饰认作了豆叶和豆渣。③贾芝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44页。最后由前妻点破,询问张郎是否记得过往之事,张郎才知道眼前的女子是自己的前妻。
(3)失去妻子所给钱财
“失去妻子所给钱财”是对张郎乞丐命的又一次强调。张郎妻与变成乞丐后的张郎相遇后,同情张郎的遭遇,念及过往的旧情,于是将银钱包在包子、油饼、猪油里赠与张郎,并嘱咐不要给他人。但张郎拿到包子之后,很快将前妻的话抛到脑后。
张郎因为没有船钱,又嫌包子太重,就把包子倒在船上当作船钱;或是中途就将藏了银子的猪油换成了鸦片;或是看到这些雪白的馒头,拿到街上廉价卖了,将前妻所赠财物送给他人。有时这些银子还回到娘家,生成了“银器搬家”的母题:船夫就是张郎妻的后来的丈夫,“打渡的把包子掰开一看,里面尽是些银子”④刘锡诚编:《灶王爷传说》,第14页。,于是银子又回到张郎妻家。
3.描述张郎之妻的“财女命”,由此产生了“石头变银子”母题
以张郎的乞丐身份为中心生成了一系列的母题。在这一过程中,其妻是与之对立的“财女”形象,围绕她也生成了一系列的母题。张郎妻一般生于普通人家,或是庄户家的女儿。但她勤俭持家,有操持家务、当家理财的天分,被算命先生称作会掌财,有财命。她被张郎父母看重,娶进家门。她持家有方,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即使后来被张郎赶出家门,嫁到穷苦人家,也会发财致富。
最能体现张郎妻“财女”形象的是“石头变银子”母题。张郎妻骑着毛驴或老牛,到一户穷人家,并提出嫁给穷人。张郎妻拿出银钱给穷人筹办喜事,穷人把银钱当做石头,对张郎妻说周围都是这种“石头”。于是张郎妻发现这些石头就是银子。有时,张郎妻发现金砖遍地,甚至每块金砖上都有她的名字;或是在田头发现石头,撬开之后就露出几缸亮晃晃的银子。
三、灶神的两面性与传说母题的“隐喻性”生成
(一)灶神的职责与灶神的两面性
一般认为,灶神的主要神职包括:庇佑家庭与白人罪状。这两个神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此消彼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灶神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灶神是家庭的保护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让民间又敬又怕的告密者。
灶神庇佑家庭之职始见于汉代。《后汉书》记载阴子方因祭祀灶神而得子孙昌盛,家庭兴旺,因而庇佑家庭为当时灶神之主职。魏晋时期,因受道教影响,灶神增加了一项职能,即“白人罪状”。《抱朴子》中较早提及此项神职:“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①葛洪撰:《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45页。灶神的职责是在月晦之夜,上天向司命之神禀告人们的罪状,并以此来夺取人们的寿数。“白人罪状”的神职成为灶神的主要神职之一,延续至今。
宋时,灶神肩负着“庇佑家庭”与“白人罪状”两项神职。宋《青琐高议》记载,彭郎中在家中见一乌衣朱冠者,面部苍然焦黑不类人,于是上前询问。乌衣者即云:“某即灶神。”其神职在于“主内外事,酉刻则岀巡。遇魑魅魍魉皆逐之。”②刘斧撰:《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页。可见在人们当时的观念中,灶神肩负着庇佑家庭的职责,可谓一家之保护神。另一方面,灶神也会“白人罪状”。宋人范成大在写《祭灶词》时提到:“腊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说谓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前期祷之。”③杨万里、范成大著,侯剑、陈光荣选注:《杨万里范成大诗选》,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35页。因而产生媚灶的习俗,不仅要“祷之”,请僧道读经,备好酒水、果品送神,将钱纸帖、灶马贴在灶上,并用酒糟涂抹在灶门,称之为“醉司命”。
明清时期,“白人罪状”逐渐成为灶神的主要神职。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了在腊月二十四日吃斋的习俗: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灶神上天,奏报一家所行善恶之日,妇人女子都食素。二十五日,姑苏人认为前一天由灶神所奏的善恶,这天会有天曹复核,因而家家烧纸钱供奉。谢肇淛对这一习俗不以为然,认为平日不修行,当天“媚灶”的行为无法欺瞒灶公:“古人媚灶之意,不过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④《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第1505页。可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灶神肩负着白人罪状的职责,人们通过吃斋、烧纸等媚灶的行为使其不向上天禀报。
灶神神职的转变还可以从祭品的变化中看出。清代之前的旧俗中,祭灶多用荤品。《清嘉录》记录了历代古籍中的祭灶之物:班固的《白虎通》中,祭灶以鸡;干宝的《搜神记》中,汉代阴子方以黄羊祭灶;南朝梁宋懔《荆楚岁时记》中,以豚酒祭灶;北宋苏东坡以只鸡斗酒祭灶;南宋范石湖以猪头烂肉和双鱼祭灶,明嘉定王槐以黄毛鲜鸡祭灶。可见,从汉代到明代以来的旧俗中,祭灶多用黄羊、豚酒、双鱼、白鸡等荤品。而清代祭灶的祭品有了较大改变。《清嘉录》中记载了清代送灶时的祭品:“以胶牙饧祀之俗,称糖元宝。”⑤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第172页。腊月二十四日送灶,沿用的是清前的旧俗。但祭品为“胶牙饧”(又称糖元宝),与之前的荤品大不相同。
胶牙饧是传统的岁时食品,“饧”即古“糖”字,是用麦芽或谷芽同其他米类原料混合熬制的软糖,十分粘口。胶牙饧的作用原本是为了让牙齿胶固。而在祭灶时用胶牙饧,则是为了黏住灶神之口,使其不说坏话。除胶牙饧外,祭灶的供物还有“糯米粉”“团糖饼”“五色糖”等,目的同样是为了黏住灶神之口。祭灶不用荤品,而用粘口的食物,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灶神以“白人罪状”为主要神职。当时各地也多以糖品祭灶神:“二十四日,‘祭灶’用饴糖、小饼、炒米豆为供,不以牲”,“又做糖饼以祀灶神……相传灶神次日奏人间善恶于上帝。”①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942、957页。
由上我们可以得知,灶神有“庇佑家庭”与“白人罪状”两项神职,二者在历史上交替存在,从民间祭祀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后者成为明清时期灶神的主职。从中我们可以看灶神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具有善的一面,是家庭的保护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恶的一面,是向上天报“一岁事”的告密者。灶神的两面性投射到传说中灶神前身张郎的身上,成为张郎善恶兼备的性格,影响了母题的生成。
(二)张郎的两面性与传说母题的“隐喻性”生成
传说中,张郎具有善恶兼备的性格:既不知感恩,做出休妻的行为,但是又懂得悔恨,知道羞耻,最后投灶而死。这实际上是对灶神职责的一种隐喻,以张郎既善又恶来隐喻灶神既是家庭守护神,又是告密者的两面性。由此生成了“张郎休妻”“张郎投灶”的母题。
1.张郎休妻
张郎休妻的母题集中体现了张郎“恶”的一面,即忘恩负义的性格特征。传说中,张郎之妻挑起生活的重担,照顾公婆,操持家务,但是张郎却不领情,执意休妻。
休妻有时毫无理由,张郎外出做生意,回家后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就将一纸休书扔给了妻子,将她赶出家门。有时是因为比富贵命与叫花子命时起了争执,张郎不服气,要看看谁是叫花子命,于是将妻子赶出家门。有时张郎嫌弃妻子生的不好看,便把她休了。有时在赌场输了钱,张郎就把妻子卖了。有时妻子不见有身孕,张郎把她撵出家门。或是经不住媒婆的花言巧语,张郎另娶妻子,于是把妻子休了。虽然理由各异,但休妻是共同的母题。
2.张郎因羞愧投灶而死
张郎沦为乞丐之后,到妻子家乞讨。张郎没有想到,给他饭吃的是他休的前妻。前妻有时会提及旧事,“还记得十年前八月十五吃‘百谷’的事吗?”借此与张郎相认。而张郎往往是悔恨交加,他想起自己从前造的孽,觉得自己做事缺德,以至落到这步田地,再没脸见人。最后实在觉得难受,“竟一头钻进锅灶里,烧得乌七八弓”,妻子只好把他埋在灶脚下。②刘锡诚编:《灶王爷传说》,第26页。
有些传说中,张郎投灶之后,玉帝认为其有羞愧之心,敢于认错,于是封他为灶王爷。但更多的传说中,张郎并未被封神,妻子给他画了个像,在灶台上供奉他。而妻子家日子红火,人丁兴旺,日子一长,“远近人家都相仿她,也都在灶台上贴上灶君像,还供奉着香火”,于是供奉灶君成为一种习俗。③同上,第52页。在人们的观念中,张郎处于善恶之间,是不足以被封神的。
结 语
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的母题,围绕张郎的固有人物属性生成和聚集,我们可以借此反思汤普森提出的母题的类型化特性。汤普森认为,母题是在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成分,正是因为它在不同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导致了民间故事的类型化特征。母题的类型化主要体现在:(1)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即角色、背景和单一的事件,它们是重复出现且类型化的。(2)母题是“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①[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第499页。。母题在历史的沿革中持续存在,从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流动时,母题是相对完整、固定且不可分解的。然而,在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有些母题是相对固定的,比如“捡空谷”。这些母题一般用一个事件来展示人物的一种属性,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最终固定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且不可分割的,于是形成了类型化的母题;而有些母题有较大的随意性,比如“张郎休妻”,民众结合当时的讲述情境和生活经验,创造了多样化的母题呈现方式。因而,在该传说中,母题的类型化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特征的描述,在这一前提下,母题具有可变性,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
同时,在这一类型的传说中,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母题来展示同一人物的特定形象特征,母题的组合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借此反思汤普森提出的故事类型的概念。汤普森认为,母题的连接和组合形成故事类型。“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由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了的母题来构成。”②同上,第498页。母题在不同文本中流动时,排序比较稳定。而在张郎休妻型灶神由来传说中,不变的是母题与人物固有属性之间的关系,变化的是母题自身与其组合方式。传说的母题围绕人物属性生成。因为人物属性相同,且母题生成遵循着相同的方式,因而母题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母题具有可变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围绕同一人物属性,母题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其次,围绕不同的人物属性,母题的组合方式可以变化。最后,母题并非完整地呈现所有的人物属性,而可以选择性地呈现其中某些属性。因而,传说母题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与人物属性的关联,遵循着一定的生成规律,由它们组合而成的传说被辨认为是一种类型。
———二十三,糖瓜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