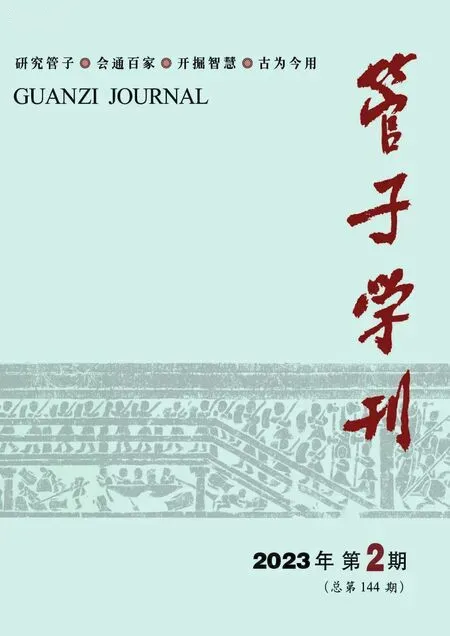章太炎与“日本阳明学”
邓 红
(北九州市立大学 文学部,日本 北九州 802-0841)
章太炎如何评判王学,是章太炎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已往的研究(如朱维铮的《章太炎与王阳明》(1)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5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3-345页。、孙万国(谢樱宁)的《章太炎与王阳明——兼论太炎思想的两个世界》(2)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230页。、朱浩的《章太炎之“王学”思想演变》(3)朱浩:《章太炎之“王学”思想演变》,《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4-22页。、张天杰的《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4)张天杰:《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72-79页。、张宗斌的《论章太炎对王学的理解与评骘——基于章太炎生命历程的考察》(5)张宗斌:《论章太炎对王学的理解与评骘──基于章太炎生命历程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第五十期,2020年7月,第255-292页。等),大都认为章太炎的王学评判分为前后两个(或三个)阶段,有着从基本否定到大致肯定的由低到高的变化。即使有人认为章太炎一生都在“非王”,但“非王”的调子不断降低(如彭传华的《“真”“俗”之间:章太炎批评王学的思想历程及真正动因》(6)彭传华:《“真”“俗”之间:章太炎批评王学的思想历程及真正动因》,《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113-122页。)。但这些先行研究对这一变化的外来影响特别是“日本因素”分析的不够,对王学本身如何能在反传统成风的近代异军突起这个问题很少谈及。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笔者独创的“日本阳明学论”为视角(7)关于笔者的“日本阳明学”视角,参见邓红:《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重新审视章太炎评判,梳理章太炎王学评判前后变化中的日本因素,澄清章太炎和“日本阳明学”的真实关系。
一、王学评判中“日本因素”的思想背景和方法
从明末一直到晚清章太炎的时代,王学因其空谈心性不贵实行,坠落于空疏的概念游戏和口号,耽虚溺寂放纵形体,被批判为“心学横流”之社会性弊病。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出于一时激愤而反思历史教训,甚至认为阳明末学空谈心性造成的理论混乱,是江山易主的原因之一;王学殿军代表人物李贽被认作伤风败俗反礼教的罪人,在明末被杀害,其著作在清朝一代被当作禁书(8)李贽的《李氏焚书》(国学保存会刊活字本)1908年才在中国首次出版。。总之,王学在章太炎出道之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界都一蹶不振,评价甚低。
就在这个时候,东邻日本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兴起了一场被称为“日本阳明学”的思想运动,王学的一些方法和心学原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利用,以作为振兴日本人的精神思想、建设国民伦理道德的口号和武器,与中国切割后的“日本阳明学”被誉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被视作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也正是许多中国人士以流亡(康有为、梁启超等)、留学(蒋介石、朱谦之等)、革命(孙中山、宋教仁等)等各种身份大举东渡日本学习的时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日本发现了喧嚣一时的“日本阳明学”,看到在中国被称之为“心学泛滥”、评价甚低的明代阳明心学,在日本居然大放异彩,成为一种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甚至被誉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感到了无比的新奇和莫名的骄傲,于是不加辨别地接受,还想将之塑造成革命的武器,运用于中国。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位。
章太炎曾三次亲履日本,现将其时间背景列举如下。
第一次,1899年6月至1899年8月。1900年《訄书》手校本目录中增加了《王学》第十。根据孙万国(谢樱宁)的见解,《王学》的写作时间不超过1902年(9)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71-172页。。
据汤志均考证,《訄书》“初刻本”1899年付梓时没有《王学》,章太炎于1900年重新校订(汤志钧称此为“手校本”),此中已见《王学》之篇名(10)汤志钧:《章太炎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3-150页。。我们推断章太炎很有可能在1899年夏天从日本回来后匆匆加上去的。根据馆森鸿的《似而非笔》,章太炎逗留日本期间和“日本阳明学”的理论创始人井上哲次郎过从甚密(11)林俊宏、[日]大山昌道:《十九世纪末中日学术交流的一幕:以馆森鸿〈似而非笔〉为中心》,《鹅湖月刊》2010年第6期,第27页。。他还和梁启超见面谈论救国大计,在梁启超的引见下拜会了孙中山先生,这也从侧面说明《王学》不是为攻击梁启超而写的。1900年的《訄书》还收入了一篇由《读日本国志二》改成的《东鉴》,其中大谈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
第二次,1902年2月至1902年7月。《訄书》1902年出版增订本,凡63篇,收入《王学》第十。1904年于日本东京翔鸾社重印,1906年再版。
这一期间的日本,“日本阳明学”的主要著作出版完毕。三宅雪岭在1893年出版《王阳明》(哲学书院1893年版),塑造了“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原型;1898年高濑武次郎出版《日本之阳明学》(铁华书院1898年版),1900年井上哲次郎出版《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00年版),两书标志着“日本阳明学”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第一本《阳明学》杂志已经发行了80期(12)1896年吉本襄开始出版半月刊杂志《阳明学》,到1899年出版第80期后废刊,参见邓红:《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第5-6页。。
第三次,1906年6月至1911年11月。留日期间发表的涉及王学的重要文章有《说林·遣王》(1906年末)、《答铁铮》(1907年6月《民报》第14号),《与梦庵书》(1907年)。
在1902到1911年间,章太炎借助日本书籍,大量翻译介绍了东西方社会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他受到斯宾诺莎的社会哲学、叔本华以及哈特曼的厌世哲学,岸本能武太、姉崎正治的宗教社会学,志贺重昂、三宅雪岭的日本国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其哲学社会学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不乏“日本阳明学”的痕迹。岸本能武太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姉崎正治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兼女婿。三宅雪岭是“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三宅雪岭1893年撰写的《王阳明》一书开创了“日本阳明学”的原型,书中将王阳明和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哈特曼哲学进行了直接的类比,认为王阳明的“心”类似于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精神”。王阳明所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和叔本华、哈特曼所说的“意志”类似,只不过范围较窄,且没有两者的“厌世”情绪(13)[日]柳田泉编:《三宅雪岭集》,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301页。。
1911年11月从日本回国。1914年修订《訄书》易名为《检论》重新出版,其中收有《议王》,其对王学的看法有了大幅度变化。1924年发表《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1925年至1928年口述《菿汉昌言》,显示出了较成熟的王学观。
从上面的时间表来看,随着章太炎留日次数的增多,精通日语的程度越来越高,和日本人士特别是“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井上哲次郎以及周边人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他的王学评判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如果说“晚清的思想家,大多通过日本书籍吸收西洋近代思想。……同样,章炳麟也从日本书籍吸收了西洋近代思想”(14)[日]小林武:《章炳麟〈訄书〉和明治思想──和西洋近代思想的关联》,《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5集),东京: 日本中国学会,2003年,第196页。的话,那么同样也可以说章太炎通过“日本阳明学”了解到在日本被“近代化”了的王学,也即“日本阳明学”(15)章太炎终其一生,始终使用“王学”而没有用过“阳明学”这个词汇,故本文凡涉及章太炎本人时都使用“王学”一词,涉及“日本阳明学”时才使用“阳明学”。。换言之,我们在讨论章太炎的王学评判时,绝对不能忽略它的日本影响,而应该把他的王学评判看作是他对王学本身和“日本阳明学”所谓“两个阳明学”的学习、吸收、鉴别、再造的过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学会了“日本阳明学”的比较类比方法。
刚才我们提到,三宅雪岭将王阳明的思想和西哲们进行比较,而我们曾经指出过,把王阳明作为东洋哲学的代表去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是“日本阳明学”的一大发明,是他们在评论阳明学的常套手段(16)邓红:《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第75页。。章太炎的王学评判,也时常将王学和西哲加以比较,譬如他在《王学》中这样写道:
希腊琐格拉底倡知德合一说,亦谓了解善为何物,自不得不行之。并有先后可序。王氏则竟以知行为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17)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使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论来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相比较,认为苏氏的知德合一论是知先行后,先要知道善,然后才能去行善。而就在1898年出版的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里,有专门比较苏格拉底和王阳明一节,其中一段说:
苏格拉底认为,善是知识之目的,行为之内容。没有知识就不能成为有能力的善良之人。(18)[日]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东京:铁华书院,1898年版,第17-18页。
可见高濑早就将苏格拉底和王阳明相比较,并认为苏氏的知德论是先知后行。此外,高濑在杂志《阳明学》第59到64期(1898年)上连载了一篇题为《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长文,将王阳明和西哲们进行了全面比较,其中第二章即为《苏格拉底和王阳明——智德福合一和知行合一》。
章太炎在《王学》中还说:
(王阳明)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1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47页。
用英国启蒙哲学家洛克的思想和王阳明进行对比,认为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和洛克的心灵是一块“白板”的假说有共同的类似点。而《答铁铮》这样写道:
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贵族之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20)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393页。
除开文中用佛教原理去解说王学特点的部分,章太炎赞美王学在“事功”方面大有作为,因为王学具有自尊、自信、无私、无畏、径行、独往、奋勇、高尚的性格,置生死于度外,旁若无人,不畏人言,近乎于尼采所说的“超人”。
总之,章太炎王学评判中将王学和西哲进行比较,是将他通过日本书籍吸收到的东西洋近代思想运用于王学评判的尝试。这种类比手法和“日本阳明学”如出一辙,而这种方法对于章太炎的王学评判非常重要,和其后来频繁使用佛学教理来解释、评判王学的手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论王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
吾人曾经指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或者“精神推动力”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日本阳明学”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影响力而创作出来的一种神话。比起日本来,这个说法在章太炎时代的中国更有影响。类似的说法有“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孙中山语),日本明治维新“有得于王学”(梁启超语),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朱谦之语),“日本尝以王学而造成开国维新之大业”(张君劢)等等(21)邓红:《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第3页。。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也有精彩论断。关于王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章太炎《答铁铮》一文曾有这样的论述:
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22)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卷),第386页。
一句“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的名言,在当时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样,章太炎在1907年《与梦庵书》中写道:
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馨香顶礼,有若圣神。(2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1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可以说章太炎是向中国宣传“阳明学促进了明治维新”论的始倡者之一。关于王学对明治维新的促进作用,章太炎在《议王》一文中有如下详尽论述:
今世谈者,颇以东国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其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从治朱、吕之言,犹自倞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学足以粉墨之。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仅得如明末枝柱一时,其道固不可久。(24)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66-467页。
这段话可以直译为下面的现代文:当今世间的评论家们,大都认为日本学习了王学,国家得以富强起来。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现在如何。当时日本刚开始抛弃分封制度时,人们崇尚武士道,地域狭小而人心团结,因而学习王学胜过学习朱子学,特别是能促进自强。加之日本人性格强忍,持之以恒,所以凭借王学取得了成功。反观我们中国,民众的性格很早就涣散懒惰了,虽然也有人奉行过王学,也只是在明末的一段短暂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王学之道不能长久。
这段话实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是说日本人学习了王学,国家得以富强,是因为日本地域狭小、习武成风、人心团结,学习王学后很快产生出自强作用。尤其是日本人的性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特别适应王学的性格,所以取得了成功。而中国人历来人心涣散、性情懒惰,所以王学在中国虽然在明末能够支撑一时,最终却失败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章太炎为何对日本情况如此了解呢,为什么会对王学促进了明治维新的论调如数家珍呢?作为一个中国人,章太炎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主张宣传王学不适合中国人的论调呢?我们认为,章太炎的如此论调,并非是他精确分析了当时国人的性格、气质、品行、特性后得出的结论,也不是他钻研王阳明著作的心得体会,而是可以在“日本阳明学”那里找到根源和现成的答案。
章太炎写《答铁铮》时的1907年,“日本阳明学”的主要论调已经基本定型。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道:
大凡阳明学含有二种元素,一曰事业性的,二曰枯禅性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25)[日]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第32页。
他认为日本继承了阳明学中的事业性元素,也就是好的、正面的、积极性部分,所以国家得以振兴,也即在阳明学的促进下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中国继承的是枯禅性元素,也就是坏的、负面的、消极性的部分,所以失败了。高濑还说,中日的差距在于日本的民族性比中国更适合阳明学:
和他们中国的坠落的阳明学相反,我国阳明学凛然带有一种生气,懦夫也有志气,顽夫也有廉风。只是两国国民的性质使之然也。日本国民的性质,和他们相比,毅然俊敏,更倾向于现实,富于实践性。(26)[日]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第33页。
这里所说日本国民性“毅然俊敏”,和上文章氏所说日本人“民志强忍,足以持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关于日本民族更适合阳明学,高濑武次郎的老师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这样写道:
再没有比阳明学更单纯的学问了。堪称为易简直截。所以日本人一接触到阳明学,便适合其性其物,以此迎彼,以彼容此,相互融会,合而为一。(27)[日]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东京:富山堂,1924年版,第574页。
从上可知章太炎的王学不适合中国人的论调直接来源于“日本阳明学”。
早在1899年10月,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章太炎写的《藩镇论》,就开始羡慕明治维新的成功,他说:
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28)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指明治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或可以说明章氏当时拥有和康、梁同样的改良主义观。“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则指地方藩镇特别是萨摩藩(今鹿儿岛县)、长州(今山口县)的藩将们勇于听命,而这些萨长“藩将”,诸如萨摩藩的西乡隆盛、长州藩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和伊藤博文,都曾被“日本阳明学”封为了“阳明学者”。他在《读日本国志》中还赞美幕末志士曰:“人人以为宪章前哲,佩刀赢粮,将其类丑,千里而赴之。及夫草宿路遇,相聚绵蕝,饮血神明前,高义者诚相踵。”(2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10卷),第47页。所谓前赴后继、大义凛然,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这些说法和高濑武次郎所说“日本阳明学”“义然俊敏,更倾向于现实,富于实践性”是一致的。
反之,王学既然有那么好的性格,为什么会不适应中国人呢?章太炎认为,因为中国人历来人心涣散、性懒惰,不太适合王学的性格,所以阳明学在中国没有取得成功。也可以说当时在中国即使像日本那样推行王学,不一定能取得成功,也即王学这个武器不适应中国。章太炎的这一思考是在对“知行合一”的理解过程中完成的。
三、对“知行合一”的理解
“日本阳明学”极端强调“知行合一”,其划分一个人物是不是阳明学者的标准,并不重视他的学问如何,而主要看重他有没有“事功”。井上哲次郎说:“阳明学派往往不免于浅薄,然学者们单刀直入,得其正鹄。……中江藤树、三轮执斋、中根东里、春日潜庵之类,其行为可观者不少。又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可观其事功。”(30)[日]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第4-5页。他还认为“朱子主张先知后行,阳明主张知行合一”(31)[日]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第3-4页。,以之作为区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特征之一。下面我们考察一下章太炎是如何看待王学“知行合一”论的。
首先考察《王学》。《王学》这样写道:
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
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程颐曰:“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如人尝噬于虎,闻虎即神色乍变。其未噬者,虽亦知虎之可畏,闻之则神色自若也。又人人皆知脍炙为美味,然贵人闻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则否。学者真知亦然。若强合于道,虽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为顺,故烛理明,则自乐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说所始),而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变为行,是即以心之容为心之行也。此只直觉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以上,则非可以征色发声,遽谓之行也。然程说知行,犹有先后。希腊琐格拉底倡知德合一说,亦谓了解善为何物,自不得不行之。并有先后可序。王氏则竟以知行为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虽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徒以事至密切,忘其距离,犹叩钟而声发,几若声与叩同起。然烛而暗除,不见暗为烛所消。其实声浪、光浪,亦非不行而至,其间固尚有忽微也。要之程说已滞于一隅,王氏衍之,其缪滋甚)。(32)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47页。
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解释。
第一,王阳明的学问中,唯有“致良知”是他自己独创的,包括“知行合一”在内的其他理论都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内容混乱,毫无章法系统可言。这一段话实际上证明了章太炎在此时并不完全了解王学的基本内容和哲学含义。在这一点上,章太炎还没有达到和“日本阳明学”同步的水平。譬如“日本阳明学”系谱的发明者三宅雪岭早在1893年写作的《王阳明》一书中,便将王阳明的学说概括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良知”(上、下)三章,开创了“日本阳明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来理解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三点式理解法的原型(33)邓红:《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第11-12页。。
第二,“知行合一”说来源于程颐。作为证据,他引用了程颐大段语录。这一段程颐语录出自《二程遗书》卷十八,原文如下:
勉强乐不得,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
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傍有数人,见佗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说了有畏惧之色,盖真知虎者也。学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脍炙,贵公子与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贵人闻着便有欲嗜脍炙之色,野人则不然。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34)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188页。
这一段话和章太炎的引文有很大出入,可知章太炎是凭借记忆作文章。但认真分析程颐的话,可知他分明是在讲“知先行后”。譬如第一段“故人力行,先须要知”,和章太炎引用的“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内容大致相仿,讲的是人只有先了解到了“知”,才开始行动;因为《书》经教导说“知”不是很难,“行”才是最困难的,因为不知便不能行动,犹如想要去东京汴梁,必须先要知道路径,才能出门。
后面一段话的比喻也是“知先行后”。闻虎色变的比喻是说先知道了老虎要吃人,才会闻虎色变,事先不知道就不会色变。听到有佳味,富人马上动了想吃的念头而穷人不为之动,因为以前富人吃过。
把程颐的话都理解错了,可见此时章太炎对王学的“知行合一”说更是一团迷雾。
第三,“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变为行,是即以心之容为心之行也。此只直觉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以上,则非可以征色发声,遽谓之行也。)这一段反对“以心之容为心之行”,认为这样的知行转换只是“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也即并非真正的知、真正的行,以此反对王阳明所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第四,章太炎还根据苏格拉底的逻辑和生活常识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批判。“王氏则竟以知行为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35)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47页。其引用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说,是以苏氏知和德有先后秩序也,即知先德后之说,以此证明王阳明以知行为同一物有悖常识。他认为,说不知就不能行是正确的,说知行合一则是错的。最后举出光波、声浪之类的生活常识来进行批判,认为有了光明黑暗才能消失,先有敲钟才会听到声音。声音由于太近,误认为是同时发生的,其实不然。批判的武器还是知先行后论。
综上所述,在写作《王学》时,章太炎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还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考察一下《议王》。
在上一节中我们曾经指出,1907年的《答铁铮》一文由于受到“日本阳明学”的影响,章太炎不但赞成王学促进了明治维新的观点,而且开始认可王学在“事功”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今人学姚江,但去其孔、佛门户之见,而以其直指一心者为法,虽未尽理,亦可以悍然独往矣。”(36)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8卷),第388页。“虽未尽理,亦可以悍然独往”可看作章太炎对王学“知行合一”说的一种独特理解,在获知过程中去展开行动,在独往独行的过程中修正自我,知与行可以交错展开,在“悍然”的勇敢而又不计后果行动中开创其事业。
在1914年将《訄书》修订成《检论》中的《议王》中,章太炎对王学的“知行合一”论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说:
其言“知行合一”者,知有节序,行有衰次,特未有定也。定别之,则不可以齐概。且夫行者,不专斥其在形骸,心所游履与其所见采者,皆行也。心之精爽乍动,曰作意。未有不作意而行者,作意则行之耑矣。是故本其初位,行先于知也。心所取象为之意言,然后有思。思者,造作也。取象为思,造作为行,是故据其末位,知先于行也。……舍是二者,知行固不能无先后。文成所论,则其一隅耳。然惟文成立义之情,徒恶辩察而无实知,以知行为合一者,导人以证知也。斯乃过于剀切,夫何玄远矣哉?(37)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68-469页。
章太炎虽然固执地认为“知行固不能无先后”,但还是认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论有自己的道理。首先,章太炎认可了王阳明的“立义之情”,初衷为“徒恶辩察而无实知”,厌恶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知识,也就等于承认了“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独创。其次,他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要以“知行为合一”,是要引导人们去“证知”,在实践中去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证知”的说法和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3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是一致的。
在此之上,章太炎对“知行合一”的内容加以自己的说明。“知有节序,行有衰次,特未有定也”,是说“知”和“行”互为表里,各有差次,不可分离,表里顺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解释符合王阳明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即知即行。
“且夫行者,不专斥其在形骸,心所游履与其所见采者,皆行也。”所谓“行”,不单单指身体形体的运动,也指心的发动、思绪过程和思维结果。这和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是一致的。“以色变为行,是即以心之容为心之行也。此只直觉之知,本能之行耳。”
“心之精爽乍动,曰作意。未有不作意而行者,作意则行之耑矣。”人的思维过程有一个从认识到精神的过程,而人的精神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展现出来。这就叫做“作意”。这符合阳明所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之命题。用现代话说叫知识的正确性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体现。
“是故本其初位,行先于知也。心所取象为之意言,然后有思。”精神驱使人的行动,其结果再反馈到人心,于是有了再思、反思。这又和阳明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相契合。用现代话说叫行为的正确准确性反过来又会影响对事物的理解,产生正确的认知。所以说“思者,造作也。取象为思,造作为行”。这已经颇有“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味道了。
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虽然还认为“是故据其末位,知先于行也”,这时的“知”先“行”后,已经不是指不可逆转意义时间顺序上的先后,而是如同阳明所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说,说“知”在“行”前,指的是“工夫”修养的一般历程为先“知”后“行”,将“实践”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时说“知”“行”不分先后。有时看起来似乎是“行”在“知”先,指的是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片段。之所以要颠倒顺序、反复讲解,是因为“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3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5页。。从上可见,到《议王》为止,章太炎对“知行合一”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
最后考察一下1924年撰写的《〈王文成公书〉题辞》。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对王学已经有了全面的理解。他在该文第一节中首先赞许王阳明的“心即理”说,认为此论出自朱熹的“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举世震而愕之”。随后说:
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40)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111页。
这一段对“良知”也有了独特的理解,章太炎认为“良知”可在“发于事业”或“为时位阻”时得以实现,以达到“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的目的,而这一改过为善的行动即是“知行合一”。章太炎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来源于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的言行妙在“恶文过,戒转念”。“恶文过”指的是子路“闻过则喜”,是王阳明“改过为贵”思想的渊源。“戒转念”指的是子路“终身无宿诺”。子路的“知行合一”体现在“闻斯行之”,所以“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事功”作用。
关于“知行合一”之说来源于子路之说的意义,与其说在学术上,毋宁说在于对“知行合一”的态度和运用。刚才我们已经指出,早在写作《议王》时,章太炎已经对“知行合一”有了基本理解,《〈王文成公书〉题辞》里,章太炎已经在显示他的王学知识了。因为该文的目的是为《王文成公书》写一篇《序言》,而大凡书序的写作,不外乎彰显著者的生平事迹,简要介绍该书的内容和思想。将子路说成“知行合一”渊源,除了有提高“知行合一”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目的之外,更可看作是章太炎对王学“知行合一”的运用,也即他的“知行合一”说来源于子路的说法,并非来源于他对思想史的考证,而是自觉或不自觉运用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知识去分析子路言行的结果,发现了子路这个“知行合一”的典范。这种运用,犹如他运用佛教(或庄学)知识对包括王学在内的儒学进行解说、整合儒佛一样,都属于一种即兴发挥。可见到《〈王文成公书〉题辞》,章太炎已经对“知行合一”说有了新的体会。
如前所说,应该将章太炎的王学评论看作是他对王学本身和“日本阳明学”的学习、吸收、鉴别、再造的过程。理解其在“知行合一”过程中的“日本因素”,则在于《议王》的主题本身就是以“王学适合于日本人,所以在日本取得了成功”为事实前提,讨论王学适不适应于中国的问题。这个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哲学思想方面,章太炎说:
学有玄远而无阡陌者,可易也。有似剀切而不得分齐者,可易也。王文成之学,所失在乙,而不在甲。而世更以虚玄病之,顾宁人、王亦农攻之为甚。……故曰,以文成为虚玄者,非也。(41)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67-468页。
世间普遍认为王学虚玄,特别受到顾炎武和王船山批判。章太炎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反而认为王学的缺点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也即切中事理但没有头绪。
在“事功”方面,章太炎在《议王》中说:
王、徐者,其道阴鸷,善司短长,乍有祸乱,举之以决旦莫之胜,可任也,而苦不能布政。……然效陈、叶者,阔远而久成;从王、徐者,险健而速决。(42)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67页。
意思是说,王阳明以及徐阶(阳明后学,明代首辅)的学问只适合于“短长”之际。“短长”指死与生、生命有危险之关头。《尚书·盘庚上》载:“矧予制乃短长之命。”孔传:“况我制汝死生之命。”(43)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在“事功”政治方面,则指形势特别紧急的生死关头,也即国家有难之际,启用王学可以一举扭转局势,“从王、徐者,险健而速决”,但是不适应“布政”,也即太平时候的施政。所以章太炎在《议王》中继续说:
至德者,惟匹士可以行之。持是以长国家,适乱其步伍矣。故曰: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夫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44)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70页。
这种具有“至德”之匹夫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是王学的“易简直截”“即知即行”“快刀快刃”的性格决定的,和前引《答铁铮》中所说王学的性格“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也是一致的。
结语
本文站在笔者独创的“日本阳明学”视角,从三个方面对章太炎的王学评判进行了再考、分析和重新定位,认为章氏的王学修养在历史背景、方法论、对明治维新与阳明学关系的态度、对“知行合一”的理解等方面受到了“日本阳明学”的影响。诸多先行研究看到的章太炎在王学评判时具有从低到高的倾向,实际上是章太炎对王学本身和“日本阳明学”所谓“两个阳明学”的学习、吸收、鉴别、再造的曲折过程。但直到最后,他对王学的评判还是有所保留,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王学评价始终掺杂有他个人的学术偏好,诸子学(庄子学)、经学(左传)、佛学之类的有色眼镜太多,妨碍了他对王学义理的充分理解,最终认为王学不如佛学。从王学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王学从根本上摆脱了佛学的束缚才取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翱翔,章太炎偏偏要再以佛教来解释王学。既然已经获得自由,偏偏还要再去给人家戴上旧的枷锁,岂能有好结果?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暂且打住。
不过,和梁启超受到“日本阳明学”的强烈影响相比,章太炎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局限于学术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梁氏以政治家的身份,真心想从“日本阳明学”的武器库中找到几样利器,以从精神上武装中国民众;而章太炎走向世界之前是一位在国学方面有所造诣的学者,当他通过日本书籍了解到东西洋近代思想时,如同一个长期在黑暗中呆惯了的穷人,突然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看到满地都是金银财富,立刻不辨别真伪地大加攫取。虽然他得到了许多真金白银,但是也捡到了一些中看不中用的镀金品,“日本阳明学”就是这样的镀金品。与梁启超信奉井上哲次郎、晚年大谈“知行合一”相比,章太炎一开始就对“日本阳明学”没有什么信心,犹如他本人和井上哲次郎的若即若离关系。虽然他相信“日本阳明学”成就了明治维新,却认为明治维新只是还政于天皇而已。虽然他认为王学有自尊自信、无私无畏、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却相信王学不太适合于中国人,也不适用于当时他投身的革命,只适用于乱世而不适合治世。这些看法,皆可谓见仁见智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