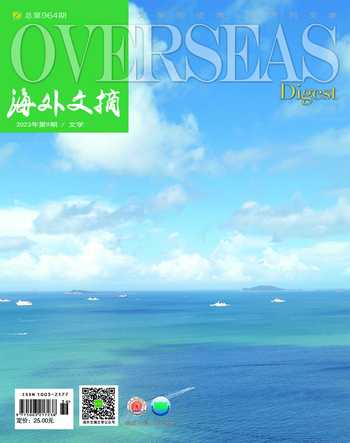错失的“良机”
徐良
T 先生已是耄耋老人,他的人生,足够配得上一曲黄霑先生的《沧海一声笑》。
其实,T 先生并不是行走江湖的侠客,只是他的人生轨迹,似乎比侠客更有故事。T 先生也不是什么身居高位的要人,没有大隐于市的资本,而是择了一处极其偏僻的山地,好在此处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世外桃源”。
生于旧社会,饱尝童年苦楚,历经风吹雨打,遭遇身心磨难,看淡人情世故,安享太平晚年,一个世纪的事,T 先生几乎是一样都没落下。他左手酒、右手琴,哪怕刚刚在台上被“批斗”到吐血,转眼间,他就蹲在角落里“锯”起了弦。就算是晚年的乡间生活,T 先生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不大的两居室房间里,一台麻将机、两架电子琴。
对,就是这其中的一架电子琴,好像是在庚寅虎年的初春,这架琴发出了一组充满杂音的旋律,是我学写的《海塔情歌》。我看见一双受痛风折磨而严重变形的手僵硬地在鍵盘上摩挲,T 先生执意,我站在他身后,忍不住哽咽。
我们约定了下一次时间,我却错失了机会。再一次上山,我是和两位忘年挚交一起去的,我们甚至去晚了,只在桃花深处的一座小土丘前,矗立良久。
那一次,我随省里的一家杂志社回故地采访,T 先生在社区偶遇到我。我们故友重逢,紧紧握手,不愿话别。
T 先生一定要让我到社会活动室,他的老年乐队要现场再演奏一遍那支曲子。我很想去,只是采访的汽车已经启动,我不得不随队离开。
我们的情义被汽车卷起的尘土阻断,T 先生的热情被汽车甩了很远。
T 先生虽是小学退休教师,但他的学习热情却令人折服。写作、摄影,都达到了专业水平。他曾带着我一起去乡间采访,不厌其烦地修改文稿。他的责任和热情,仿佛是燃烧不尽的一团火。
我是在夜晚翻看微信朋友圈时知道的,T 先生那团可爱的火光永远地消逝了。
我很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一定要急匆匆地随队离开呢?我自问,难道就是为了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吗?守规矩是道德的,可守规矩又得到了什么?
T 先生是给了我机会的。如今,我只有翻看我的婚礼VCR,那是T 先生的作品。
L 兄已是肝癌晚期。表面上一副吊儿郎当的L兄,其实是一个并不“聪明”的人。我当时在故地流浪,L 兄并没有看不上我,反而在我危急关头,不遗余力,江湖救急。
在那座充满阳光的小县城,我和L 兄往往会在晚上的第二台酒场上相遇,然后再一起去赴第三场。尽管我胆量很大,但酒量甚小。L 兄是海量,他很少丢人。后来,他干脆开了一间酒吧,以他的性格,四海兄弟,生意自然不在话下。
我一直在想,不管酒量大小,酒精进入身体,对人体的伤害会不会是一样的?由外到内,我早已是遍体鳞伤。好在,酒不是乱喝的,特别是深夜的酒,喝进去的都是浓浓的感情。
烟伤肺,酒伤肝。L 兄的倒下,我深感恐惧和诧异,他重情重义,把酒当仇人,不知道这是不是酒精在报复他。
我知道剩下的时日不多,我不会再浪费机会。L兄每次相约,我都无条件赴约。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两盒高山樱桃,我很愧疚,我们在酒店茶叙了很久,好在他依然桀骜,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L 兄是顽强的,他与病魔抗争了一年多时间,直到最后,完全无法走动,连采血也得委托医生朋友上门。我在电话里听见他的声音,仿佛真有些妥协和无奈的口气,不,应该是被病痛折磨后的有气无力,我想应该是的。
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我终于放弃了。我委托朋友前去吊丧。我无法接受一个曾经站得很直的男人倒下。
后来的酒局,有朋友善意地劝解我少喝几杯。我和别人一样,无法理解我自己的怪脾气,我狠狠地回答道:“好兄弟L 是站着走的,难道我们要躺着生吗?”我独自端起酒杯,豪饮而尽。
L 兄也是聪明的,他把男人做到了极致,把男人的魂带进了下一个轮回。而我们,继续上演着生活无尽的无奈和辛酸,也被迫面临着生活无尽的丑陋和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