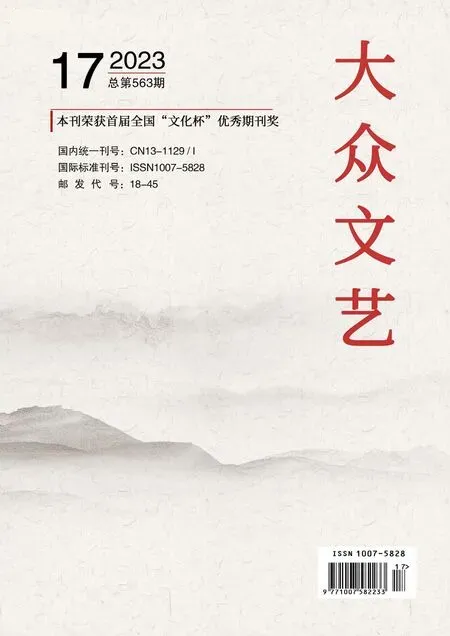交互界面图标的隐喻
——以广州百年音乐家数字档案为例
卢冰虹
(广州大学,广东广州 510006)
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下,由数字化控制的人机界面设计,正逐渐转向凸显智能化应用的界面功能,从界面视觉系统的视角,图标是一种将文本内容转换成图形元素的应用形式,界面设计过程中,图标不仅实现观众对复杂信息的快速识别,更具备引导用户开展对应需求的交互活动的作用。这些设计在于服务用户更高效的运用信息进行有效转换;但不单只停留在视觉感官上,而是对交互体验是否流畅、是否能够符合用户对交互的预期判断,也是交互体验的深层知觉感官体验。
一、图标的隐喻
1.图标表征
以特定符号呈现、具有高强识别性和功能性的图形,称为图标(iсоn)。图标是界面中一个系统或者多个系统并存的重构状态,在呈现图形视觉风格的同时,传递其表征背后蕴含的信息,用户通过对图标形状联想这些信息,进而实现智能化的人机界面交互活动。
作为一个导向型的功能图标,在设计上需要符合促进用户正确判断功能的元素,这种元素的选择通常来自受众通用的认知,例如被广泛使用的“无线网络”图标(图1),由一个点和三条弯曲的线条组成,应用广泛使无线网络图标在使用者大脑中形成长期记忆储存,用户在看到无线网络图标时首先会联想到其对应的主要功能,并以此为中心点扩大联想的范围,也涵盖与其相关的副功能。而在提供这种认知的前提下是图标已经经历了较长的适应阶段,能够被用户正确辨识。但如果这个图标重新被设计成与原来截然不同的模样时,就会产生排斥或难以适应的后果,并且对以往的认知习惯产生混乱,最后导致在浏览界面时消耗过多适应时间,逐渐消退浏览兴趣。所以在针对大众普遍认知的图标时,设计者通常在设计上不会做过多的改变,避免出现错误判断。

图1 无线网络图标(网络图片)
2.隐喻知觉
“隐喻(Меtaphоr)”在文字上通常用作修辞说法,在解读上具有多样性。但在不同设计方向上隐喻的表达方式也各有不同。通常以某种感官体验、个人主观思想等生理评价作为隐喻依据。
建筑设计中,艺术家常常通过建筑的造型及内在空间的表现,隐喻并传达出设计者的理念与情感。勒•柯布西耶(Lе Соrbusiеr)曾提出建筑无限生长的问题并作出他的解答。建筑的生长其实就是扩建,但怎么合理运用空间实现建筑的无限生长,是对建筑标准化的考验。无限生长的最初原型可以追溯到1929年勒•柯布西耶为曼达纳姆(Мundanеum)方案规划的“世界博物馆”建筑,这个设计概念成了后来许多项目的参考和基础,为设计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参观者会先从建筑顶部进入馆内,由三条相邻的甬道以同一条螺旋线展开由上而下进行参观,以达到实现叙述与即时的可视化同步。[2]在北非菲利普维尔的博物馆方案中更加完善了无限生长的解释(图2)。建筑遵循黄金切割法,以螺旋的方式向外延伸,满足建筑元素的标准化同时能实现无限生长。勒•柯布西耶对通过建筑无限生长的思考赋予建筑生命,赋予记录实时的年轮,以隐喻的形式阐述现代主义建筑的不一样的生机。

图2 博物馆鸟瞰图
艺术创作上,艺术家也会通过创作来表达个人情感或观念,创作手法通常是开放性的;写实或抽象;摄影或雕塑,创作领域广泛。而艺术家在创作时也会反复思考,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意图,最终呈现的作品往往具有创作者本身独特的观点和当下时代特征。就像被称为“波普艺术教父”的安迪 • 沃霍尔(Andу Warhоl),以常见的日常生活物品作为主题创作,在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中频繁出现。他的代表作《坎贝尔浓汤罐》(Сampbеll's Sоup Сans)广为人知。作品以32幅帆布画着不同口味的罐头画组成,通过丝网印刷技术进行绘制。作为以工业手段绘制的艺术作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艺术界中产生轰动,评价也随之褒贬不一。他曾声称“我就喜欢无聊的东西。”[3]这些通俗单调的事物成为他波普艺术创作中的元素,麻木的重复排列,营造强烈的冲击感。相比于传统高雅的艺术观念,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更多呈现的是大众化、空洞麻木的视觉体验,这也模糊了艺术的界限;是优雅还是通俗,这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艺术的传统认知。安迪•沃霍尔这种泛滥式的重复,隐射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商业经济发展繁荣下人们对世态的麻木冷漠,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使人们逐渐向欲望倾斜。
二、界面图标的隐喻效应
1.图标在界面交互上的有效隐喻
网页界面产生的交互行为,实际是人与计算机进行有效信息交流。界面交互中,图标对用户最直观影响的是引导功能和联想效应。通常在设计中会以本身所具备的第一功能作为主要参考对象,而参考对象的元素来源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对象功能的理解。通过功能项的实用性和延展性的特点设计图标,使用户看到图标时联想到日常生活中具体对象的使用方式和功能范畴,最后引导用户进行初步判断,达到预期的目的,起到有效隐喻。所以图标的隐喻传递的不只是单一的功能,是将相似或相互作用的功能作为一个集合。
2.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界面功能分析
正确的隐喻设计往往使交互体验更为流畅,这就需要在设计前期的反复试验和用户感体验调查,避免隐喻的错误造成无效引导。廖宏勇教授的《图形界面的隐喻设计》中归纳了隐喻设计的五点原则[4],恰当的联想来源于合适的隐喻。图标中的图形元素设计需要对应合理的隐喻,以及完全隐喻地避免和是否需要作出隐喻项都需要在设计中反复斟酌。以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中的粤音有界面中专辑图标为例(图3),设计上选择以唱片为图形主元素,色彩选择上呼应主界面色调;整体图形线面为主,将唱片图形截取四分之一并放大作为专辑图标;因为专辑本身涵盖不同介质载体作品,采用唱片作为图形元素的原因主要是来源于日常生活中音乐专辑多以唱片或СD为主:唱片和СD在造型上相近,但唱片的产生早于СD,而在我们记录收集的广州百年音乐专辑作品中多以唱片为主要媒介载体。唱片图形也多用于各类音乐软件中,例如网易云音乐播放界面中,显示专辑封面就以唱片图形呈现,用户在互动过程中也能获得亲切感。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的专辑图标以唱片为主图形,本身涵盖的媒介载体不止一种,也为避免用户在联想过程中产生偏差,导致在辨别图标功能时的错误解读。所以选择大众普遍接受并能快速理解的视觉符号作为图标,人们在接触到图标后进行的同类别认知联想,能够合理诠释图标中的隐喻项,最终达到提供信息样本的目的。

图3 粤音有约(作者原创)
三、基于隐喻设计的界面优化
1.界面层级的合理归纳
作为数据库前端的界面应用,通常需要将信息合理视觉化并分区归纳;优秀的界面设计使用户在操作时能够流畅交互,增强用户体验感。而数据库本身包含的信息内容无法通过一个界面完整输出,信息所涵盖的门类广泛。以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为例,所储存的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电子书等等,就需要进行合理分类归纳,统筹层级划分。当单个界面无法承载过多的内容量时,就需要通过必要的交互加工,进行简化浓缩。在诺埃尔•卡罗尔(Nоёl Сarrоll)的《艺术哲学:当代分析美学导论》中提到:“当然,一个样本不必拥有它代表的正品的全部属性。照标准说,样本只拥有其例示的正品的部分属性。”[5]即用户在浏览首页界面时所接收到的是全部内容的精简提炼,代表这类内容中的一个明显属性特征,通常以视觉符号或文字呈现,但实际内容量会大于用户可视范围;使用户在浏览时快速识别可用信息,提高人机交互效率。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界面中通过将粤音有约板块的内容划分三个部分,提取每个部分内容中相对于个体的明显属性作为样本,通过图标和简练的文字进行展示,在浓缩隐喻其中内容时也完成引导交互的效果。
2.优化方案
当单个界面无法解释过多的内容量时,就会通过交互行为扩展界面层级,使信息量有效地层次分化,用户在体验感官上会更加流畅,提高浏览兴趣。在孟沛、王毅的《网络交互界面隐喻设计模式研究》提到:“交互行为特色与其承载的内容是分不开的,只有内容与形式完整合一,隐喻模式恰当,才能够称为一个设计良好的界面交互。”[6]界面交互设计的信息有效层次化的前提是进行前期内容量的整理和分类。在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中,展示人物界面就通过以近现代作为区分(图4),用户在将鼠标移至近代人物框中,会浮现近代代表人物音乐家冼星海的人物图像,移至现代人物会显示陈小奇的人物图像,以此来作为划分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在避免信息分类矛盾的前提下,通过视觉体验上拉近用户浏览的亲切感,以人物图像进行联想,从而产生继续浏览的兴趣。

图4 二级界面(作者原创)
交互界面中的隐喻项怎样能正确呈现,才能使用户在浏览时能够进行适当的联想从而获取可用信息?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以前期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对受众人群和交互方式进行理论分析,通过界面设计的八条黄金规则[7]为参考作为交互界面的依据,适当通过隐喻手法构架合理交互情境,建立虚拟情境型隐喻设计模式[8],合理运用资源开发,通过设计与广州百年音乐相符的视觉形象,使用户在浏览时能够身临其境,营造自然的人机交互。
总结
综上所述,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交互界面为视觉平台,通过合理的隐喻设计引导用户在浏览音乐数据库界面时完成流畅的交互体验。隐喻作为一种方法,需要通过图形文字甚至是媒介作为载体来体现,恰当的隐喻使交互行为和界面功能能够自如发挥相应的应用功能,是人机交互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广州百年音乐家数据库作为面向大众化社会性服务型网站平台,在交互体验上需要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整,但用户体验存在主观意识,所以需要把握实际应用需求和设计者设计方向的平衡,需要合理的隐喻设计辅助界面交互的呈现舒适的视觉体验和交互体验,在实现音乐资源数据库建立同时满足社会性服务需求,实践服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