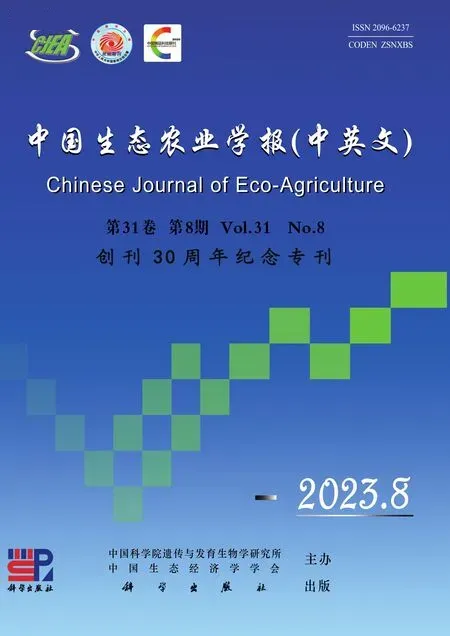发展中国生态农业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兼论生态农业在我国兴起与发展的“前世今生”
王松良,施生旭
(福建农林大学 福州 350002)
农业是支撑人类生命和永续繁衍的支撑产业,为古往今来各国政府之重中之重的治理内容。在迄今1 万年的世界农业发展历程中,先后走过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此阶段农业以化石燃料为核心启动力,也称为“现代化石农业”或常规农业,为了便于叙述,以下统称“常规农业”)。常规农业在经济生产力提升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孕育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诸如人口爆炸、食物短缺、能源缺乏、资源衰竭和环境恶化等危机和气候变化,几乎失去生态生产力(也可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全球农业生态化转型(也可称为“绿色发展”)极为迫切。
我国以农立国,农业是社会安定、国家兴旺和国土安全的基本保障。自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基本解决温饱难题。2022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8 653 万t,至2015 年以来连续8 年稳定在6.5 亿t 以上[1];1978 年我国农业产值仅为1397 亿元,2022 年达到78 340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10%[2]。但时至今日,我国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日益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双重约束,依赖化石能源投入维持产量的常规农业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势在必行[3]。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经济学规律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新型农业体系[4],也是世界常规农业在经受长久的危机之后的替代农业模式之一[5],其目标与当下我国农业迫切需要的生态化转型内涵高度一致[6]。更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快速追求常规农业的同时,我国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进行了生态农业理论和实践探索,征集遴选不同区域性、行业性、高度代表性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体系,赋予“中国生态农业”称呼[4,7-10],后者为当下我国农业生态转型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行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本文回顾了生态农业在世界和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提出中国生态农业作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根本途径的基本任务、技术体系和创新机制。
1 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
1.1 世界生态农业: 从常规农业的替代农业之一到可持续农业的主要载体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陆续有学者反思以化石能源投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包括有机农业、生物(动力学)农业、自然农业和生态农业在内的替代农业模式[6,11]。其中,“生态农业”一词由美国土壤学家威廉姆.艾布瑞克特(William A.Albrecht)在1970 年提出[6,12];1979 年,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省(PEI)召开第一届加拿大生态农业大会[13];随后生态农业在加拿大的部分农业区域如Saskatchewan 省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14]。在全球一些区域实践的基础上,1981 年英国农学家玛莎.凯丽-沃辛顿(Martha Kiley-Worthington)正式定义“生态农业”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的、低输入的、经济上有生命力的,以及在环境、伦理和审美等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n ecologically self-sustaining low input,economically viable,small farming system managed to maximize production without causing large or long term changes to the environment,or being ethically or aesthetically unacceptable)”[5,15]。此后,在美国、加拿大部分地区、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保加利亚、立陶宛、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英国、波兰和斯洛伐克等,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等,亚洲的孟加拉国等,陆续进行生态农业的实践[16-25]。
随着世界各国常规农业的弊端不断被报道和揭示,农业的生态化转型也成为全球现代农业发展的最新趋势[11]。特别是在1987 年布伦特兰夫人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26],199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荷兰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农业环境大会,定义可持续农业的内涵,即“管理与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便确保获得并持续地满足当前和今后世世代代人们的需要。因此是一种能够保护和维护土地、水和动植物资源,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活力、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农业。”[27]并出台了关于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丹波兹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发达国家常规农业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和方向[28]。1992 年法国提倡“农业的多功能性”,获得其他欧盟国家的呼应,后者出台了“共同农业政策”和“农业环境计划”;同年日本颁布《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极力推行 “环境保全型农业”;1998 年韩国开始实施“环境友好型农业”,以此促进常规农业的生态化转型;1999 年美国在各州逐步推行“农业最佳管理措施”,颁布农业最佳实践指导和激励政策[28]。在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拉丁美洲各国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陆续发动了自下而上的生态农业运动,如2003 年巴西国会率先实施立法来保障全国性生态农业的持续性发展[29]。拉美国家的生态农业运动往往包涵了对食物主权的追求,影响深远,直接导致2010 年12 月20 日联合国食物权利特别官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尔(Olivier de Shutter)递交了一份题为《Agroecology and the Right to Food》的报告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 Council),并在2011 年8 月3 日的人权委员会大会宣读[30]。在这份里程碑的报告中,“Agroecology”一词两用,既指农业生态学学科,又指在前者指导下的生态农业实践。报告指出,生态农业既是解决世界食物总量(food availability)的途径,也是解决食品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甚至促进营养均衡(adequacy)的方法,还是实现农民赋权(farmer empowerment)和农业可持续性(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的根本出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烈反响。随后FAO 成立生态农业分部,在其网站上设立专业的“生态农业知识库(Agroecology Knowledge Hub)”。2014 年FAO 主持召开第一届生态农业国际研讨会;2015 年召开了拉美、非洲和亚太等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研讨会;此后,陆续召开了一系列的区域生态农业国际会议,其中,2016 年在我国云南召开了国际生态农业研讨会;2018 年在罗马召开了第二届生态农业国际研讨会。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后石化农业时代不可阻挡的洪流,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载体[5,28,31]。
1.2 中国生态农业: 作为世界可持续农业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模式
20 世纪80 年代不仅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也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在这个年代之初,诸多学者就对70年代中央政府提出的含“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农业“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反思,提倡应用生态学和系统论思维思考“农业四化”存在的潜在问题。1979 年马世骏教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等八字生态工程原理[32];同年,全国农田生态系统科研协作座谈会在华南农学院召开[33];1980 年,全国第一届农业生态学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召开[34];1982 年全国第二届全国农业生态学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农学院召开[35];1982 年全国第一次农业生态学教学研讨会在华南农学院召开[36]。上述学术活动标志着我国学界正式引进了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学科及其思维,并启动培养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人才;同时,生态学者和农学学者们利用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思维对农业“四化”的提法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尽管我国农业尚未正式进入现代常规农业阶段,但由于人多地少的严峻冲突,存在过度使用土地的情况,农业生态系统已处于脆弱之中,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国农业的复兴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各个层次、各个亚系统的复杂问题[37]。在这个背景下,西南农业大学的叶谦吉教授在四川农区遭受生态灾难后首次正式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8-39]。他指出,“总之,农业的未来,要求在农业生态系统主宰一切的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立足近日,放眼未来,促进和维护良性循环,为我们这代人以及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理想的经常保持最佳平衡状态的生态系统,我们可称之为高效生态系统亦即生态农业。”[40]他随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概念,即 “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原理,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吸取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精华,通过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复合循环机理,建立起多目标、多功能、多成分、多层次的组合合理、结构有序、开放循环、内外交流、关系协调、协同发展的农业系统的一种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41]。
在上述学者的生态学思想引导下,全国各地开展生态农业的尝试,在实践中先后提出“一字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十字型”(种养加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等生态农业模式[5,42]。20 世纪90 年代政府开始致力于生态农业的示范推广工作,1993 年农业部等7 部委联合发文推动51 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工作,到2000 年提升为生态农业示范点,示范数量达200 多个[27,43-44];至2003 年底生态农业示范(点)县达到600 多个,其中国家级100 多个,省级500 多个;为了促进生态农业发展,2003 年农业部向全国征集370 个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从中遴选和确定10 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模式: 北方“四位一体”模式、南方 “猪-沼-果(稻、菜、鱼)”模式、平原农林牧复合模式、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模式、生态种植及配套技术模式、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生态渔业及配套技术模式、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利用模式、设施生态农业及配套技术模式和观光生态农业模式等[45]。
与此同时,中国生态农业体系基本形成,不仅具备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内涵,即“中国生态农业”是 “运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成果和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实现功能良性、生态合理性的一种农业体系。”所谓 “功能良性”强调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的“经济”可持续性,而“生态合理性”是应用生态学思维和农业生态工程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平衡[10]。也定义了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外延: 即第一层次,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太阳能转化、生物能利用、废物资源化;第二层次,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的“接口”工程,达到能量、物质、信息、价值流良性循环;第三层次,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协调。加上总结出诸多可供推广的中国生态农业模式,形成了与国情、农情吻合的中国生态农业体系,被称为“中国生态农业(Chinese Eco-agriculture,CEA)”[9,43,46-47],成为世界可持续农业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模式[7-8,48-50],也获得国外学术界的认可[51-53]。
2 发展中国生态农业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2022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建设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也是题中之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应建立在全面解决“三农”问题、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的基础上;也应建立在全面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突破资源和环境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制约的基础上。在这个大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与我国国情、农情适应的“中国生态农业”必定成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2.1 发展中国生态农业是全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
由于受到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严峻的“三农”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难题。农村经济难题表现为: 现代产业经济链条设计上长期分配给农民的产业利润偏低,导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村环境难题则是因为人多地少的资源矛盾导致以牺牲农业生态环境追求农业的经济生产力;农村经济和环境难题的交织必然产生农村社会难题[54]。其中,农村环境难题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55]。幸运的是,“三农”问题终于在2003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4 年开始至2023 年连续出台20 个“一号文件”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工作来抓,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的历年 “一号文件”,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环境友好型” “生态相容型”农业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方向加以推广和发展。2013 年农业部启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的编制工作,从2013 年7 月起,为了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围绕我国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模式等问题,中央到各地开展了密集的深入调研。2013 年12 月聚焦“三农”工作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求今后农业工作的重点内容要确保农民收入、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提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5 项重点任务,包括: 优化发展布局,稳定提升农业产能;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农田永续利用;节约高效用水,保障农业用水安全;治理环境污染,改善农业农村环境;修复农业生态,提升生态功能[56]。每一个任务都涉及农业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农村环境难题的解决。
中国生态农业是应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农业生态工程方法,把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经济上可行、生态上良性循环的农业体系,其本质上把农业各个生产组分通过它们的“食物链”关系实现“接口”,从而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和能量得到循环利用,以减少系统外的物能(化肥、农药)投入,减少废弃物(污染)排放和食品残留。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可以有效地治理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村生活环境,解决农村环境难题,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解决,是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55,57]。
2.2 发展中国生态农业是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首。我国是人口大国,满足不断增加人口的口粮需要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由于过去40 多年常规农业在我国的高速发展,造成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特别是耕地和土壤质量的破坏,进一步导致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面临严重挑战: 一方面,我国耕地资源少且禀赋严重不足[人均耕地不足0.1 hm2,不足世界人均耕地(0.4 hm2)的1/3];另一方面,由于过度施用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带来的耕地土壤结构破坏、污染与食品安全等难题。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9 年,全球化肥施用总量为1.67亿t,我国农业化肥施用总量达0.54 亿t,占32.34%,我国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200 kg·hm-2,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 倍多;同年,全球农药施用总量350 万t,我国当年共施用农药139.17 万t,占39.67%,我国每公顷耕地施用农药8.16 kg,是美国的3.62 倍(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I0A02&sj=2020)。由于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和畜禽粪便的不合理处置,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化恢复能力,对农业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是全面实施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建设战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国农业的生态转型比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为急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从7 大部分28 条细则提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等的措施[58];2018 年7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2020 年3 月又印发《2020 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2021 年8 月农业农村部等6 部委联合印发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中国生态农业把农业生产的若干环节“接口”起来,上一个环节的 “废物”成为下一个环节的“资源”,由此形成一个自净的生产体系。这样的自净生产体系能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的内部资源,减少外源物能投入,使生产环境走向健康,从而保证生产出安全的食物,保障安全食品的有效供给和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59]。上述一系列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文件的出台,为作为农业绿色发展基本手段的“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保障。
此外,考虑到农业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约占大气温室气体的25%,发挥农业的碳汇、减少其碳排放也迫在眉睫[60]。中国生态农业一方面通过发挥土地空间的植被覆盖,尽可能让碳氮固定在土壤和产品中,最大程度上发挥农业的碳汇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农林牧副渔的有效“接口”、农工商“一体化”,实现对有机肥和饲料在植物生产和动物养殖的平衡、尽量减少对市场化、工厂化生产资料的依赖,既降低生产成本,又有效减少农业生产和消费过程碳和氮的排放[59]。可见,大力发展中国生态农业还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助力履行一个农业大国向世界关于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庄严承诺提供技术支撑。
2.3 发展中国生态农业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通道
自2004 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20 个“一号文件”中,2 个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即2005 年“一号文件”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和2018 年“一号文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从前者承载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20 个字发展目标,演进到后者承载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20 字发展目标,体现了国家战略关于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正从经济发展向生态建设跃迁。
中国生态农业是在农业生态学原理指导下构建起来的适应我国特色国情、农情的可持续农业模式[8,48,50],能融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目标[61]。从国外对乡村发展的定义看,乡村振兴的原始内涵仍着眼于乡村经济问题,乡村振兴反映一个恢复经济繁荣的容量和能力[62-63],所以“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与国外乡村发展策略不同,由于在过去国内纯粹追求经济发展,除了面临农村经济难题外,乡村所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也已成为难题[54]。因此,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一定是乡村的生态产业的“兴旺”,同时,“生态宜居”自然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生态农业的本质是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变革,把农业生产的若干环节“接口”起来,上一个环节的 “废物”成为下一个环节的“资源”,由此形成一个自净的生产体系。所以,中国生态农业有望把“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的目标融为一体,并对 “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标对应,中国生态农业有3 个核心任务[62]:
一是农业产业由纯商品经济的产业向生命保障的公共事业转型。由于单一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常规农业忽略农业的(产品)生产、(人民)生活、(乡村)生态,及最终支撑全体国民生命的“四生”多功能性。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为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产业[64],这样特殊的生命产业不能仅由单一的市场经济机制实现,需要把它转型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事业,让社会参与投资和定价,协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
二是农业生产由生态上的恶性循环向生态上的良性循环转型。长期把农业生物高产放在第一位,过度投入各类基于化石能源的化合物,导致耕地土壤破坏、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最终产生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难题,威胁国民健康。只有通过发展农林牧“接口”的生态农业,才能扭转上述生态上的恶性循环为生态上的良性循环,协同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
三是农业经营从破碎链条向“种养加” “农工商”一体化转型。长期以来,基于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贸易和服务在地理上和经营主体上都是分离的。一方面,造成从事生产的农户分享到整条产业的利润很低,是农村经济难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消费者和生产者从地理上和心理上都被有意拉开距离,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65]。中国生态农业强调“农养加” “接口” “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是解决农业产业破碎化和农村经济难题的可行途径。
3 推进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3.1 建立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技术体系
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既要大力研制单项生态农业技术,更要重视将单项生态农业技术整合成地域适应性更广的、能体现整体效应的技术体系[66]。通过40 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生态农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三大技术体系,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撑[55]。
3.1.1 应用多维用地技术体系促进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多维用地技术是利用生态学的生态位和生物演替原理,开发利用自然空间资源的一种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在垂直空间上,利用农业生物的不同特性及其对外界条件的不同要求,将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机结合,建立多个物种共栖、质能多级利用的农业生产方式,也称立体种养或立体农业。如方兴未艾的“林下经济”,就是利用林地资源和环境栽植农作物、中草药植物、食用菌,甚至养殖畜禽,形成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农林牧复合系统,以充分、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系统外的物能投入,形成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
3.1.2 应用物能多级利用技术体系建立自净的生产系统
物能多级利用技术是利用生态学的食物链和生态金字塔原理,采用食物链加环的方式组建新的食物链,使物质能量通过食物链中不同生物的吸收多次转化、利用,形成无废物、自净的生产体系。例如,稻田养鱼就是一种最简易的生态农业模式,利用稻株之间的水体空间加入“鱼”食物链环,实现多元目标: 首先,为保障鱼类生存,稻田中不宜多施化肥和农药;其次,鱼类会取食稻株上的有害生物,鱼粪可以肥田,能够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再次,鱼类在稻丛之间攒动,促进稻田土壤养分还原反应,大幅度减少甲烷排放,减缓温室效应。
3.1.3 应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体系保障食品安全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是利用生态学的生态位、生物种间关系原理,综合应用栽培技术、物理手段、生物防治和农药的合理使用,挽回农作物因有害生物造成的损失,实现农药实质减量,不仅维护农业生产环境的健康,也保障城乡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的安全供应。
3.2 建立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机制
毋庸置疑,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中国生态农业建设尚存在许多体制和机制上的约束[67-69],建议借部署实施《“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和探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之路径之机,未雨绸缪地加快在绿色农业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夯实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理论、人才、制度和法规基础。
3.2.1 加快建设农业生态学科,完善中国生态农业理论体系
生态学是生态文明和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70-71],农学与生态学融合的农业生态学是建设中国生态农业的方法论[5,8,72]。和发达国家和国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南美洲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态学理论构建远远落后于生态农业的实践[73]。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应加强农业生态学科建设、科研投入和专业教育,在全国农林高等院校设立农业生态学本科专业,并发展从本科到博士教育的完整的农业生态学学历教育体系,为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储备理论基础和相应人才。
3.2.2 完善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全面兑现生态农业产品价值
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制度建设必须先行[74]。一方面要构建中国生态农业的绿色行动清单制度,主要指导第一线生产者认清什么是生态农业和如何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另一方面是生态农业产品的认证制度,让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者分享到应有的收益。当务之急是研究和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农田生态补偿机制[75],其内容包括: 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获得补偿? 谁能获得补偿? 补偿多少? 谁来补偿? 如何补偿?
3.2.3 尽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促进多规合一、保证监管有效
发挥法律的监管作用是规范中国生态农业健康发展的最高保障[69],目前有关中国生态农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但较为分散,且可执行性较弱。首先,需尽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梳理现有的与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相关的一切规划、规章、条例和法律;其次,深入探究当下我国农业资源与环境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约束,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形成更具实效的发展生态农业监管机制,夯实建设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法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