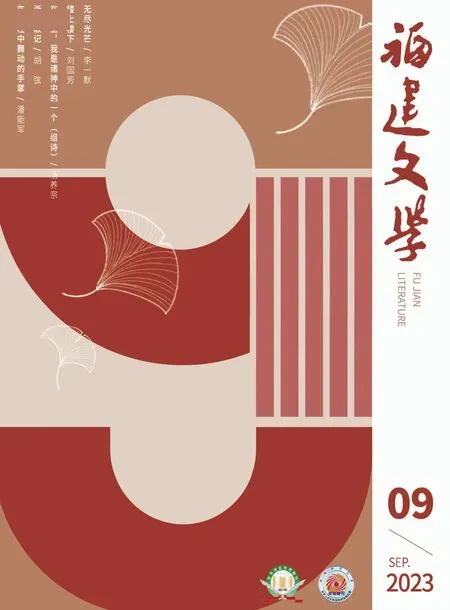故乡,我的词语长草了
2023-10-03 00:11:10杨健民
福建文学 2023年9期
杨健民
河流不再柔软
曾经在那里捞蚬子、溪鱼、河蟹
如今溪水不淡定了,老得比唐诗还快
流年是一片上锁的瓦房,檩条青筋暴露
雨水柔软,溪流坚硬得如同失眠
当故乡被端起时,我收拢了一声涌动
爷爷说:老天淋湿你,也会晒干你
只有顺水而来顺风而去,才是你的抵达
我仿佛看到爷爷挑菜担时换肩的位置
在那座石桥下,他拨开一片薹草水泽
河流不再柔软了,像一条销蚀的眼缝
我丢失了一个词,找不到更多的词
我盯着平白无故的河床,想割掉一些芦苇
那些多余的蛙鸣,无忧无虑地在镖射
我决定留下瓦上的三两只麻雀,说说那一片水
然后去寻找
这条偷走我的记忆的溪源
怀念一棵树
那棵树曾经砸坏我家的猪圈
猪仓皇逃出,就像一记漂亮的扣球
台风像十万枚符号抛向地面,慌不择路
谁能摁住风的情绪?旋涡的语言是疼痛的
只能叩响季节的暗门,让词语在旷野里逃逸
后来我去当知青,去上大学,树也没了
那年我回老家,故乡的回声略显浑浊
那片龙眼林热烈而静寂,如同夜构成的唇
最年长的老树一旦默不作声,太阳就会走偏
就会让青蛙鸣叫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如今我不时怀念那一棵树
就像把故乡的呼喊植入深处
故乡没有虚度,我还是那个制造词的人
继续捕捉老树的颜色,递给太阳
晒谷场
这里已经长满了草,我看着草生长
永远的一万两千块砖
就像两个世纪前的沙之书,词语完整
傍晚的风,一定是我怀旧的主角
深陷龙眼林的月光,让旧事一桩桩解缆
那些充满硬度的方言说着田野的风
说着当年晒谷场上说过的美人以及八卦
我抽着一缕又一缕炊烟,看蝴蝶纷飞
晒谷场记下了丰收的微醺和晃荡
那些季节,人间万事在磨着一堆慢念头
晒谷的小姐姐如今哪里去了?有些事
在流年到来之前已经翻开
她告诉我,晒谷就是把太阳捧在手里
不能对雨漫不经心,要有一种疾走的眼神
晒谷场有两条道,一条返回大地
一条留给不下雨的天空
在任何有风的地方,就有田野的词语
猜你喜欢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22年6期)2022-06-23 04:46:53
课外语文·中(2022年1期)2022-02-16 01:08:06
科教新报(2020年36期)2020-11-09 09:09:11
当代陕西(2019年10期)2019-06-03 10:12:24
中学生博览·文艺憩(2019年5期)2019-05-17 06:17:44
海峡姐妹(2018年3期)2018-05-09 08:20:48
作文评点报·中考版(2018年1期)2018-02-09 18:06:47
读友·少年文学(清雅版)(2018年4期)2018-01-14 01:11:58
新农村(2017年6期)2017-06-27 08:14:41
幼儿园(2016年19期)2016-12-05 19: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