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屋山下
张国龙
米铁桥一家三口顶着烈日鏖战了七天,收割完了所有的稻子。
经年累月风吹日晒,爷爷早已一脸古铜色,沟壑纵横的双手青筋暴突,佝偻的身板包裹着厚厚的暮气。米铁桥和米李花满脸黑里透红,清瘦的身影里仍旧忽闪着青春的气息。汗水从早到晚流淌,带走了他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就连脚步声都更加轻巧了。
稻子收完了,山湾立即闲散了下来,山梁沟壑们也慵懒了。随处都是稻草,牛怎么吃都吃不完,就省得专门给它们找草料;红薯藤割了又长,铺满了旱地,猪们也有吃不完的食料。丝瓜、苦瓜、茄子和西红柿挂满了屋前屋后,现摘现吃,新鲜与丰盛自不必说。硕大的冬瓜和南瓜随意躺在田间地头坡上沟里,它们大得惊人,米李花背两个回家都有些吃力。一个冬瓜或南瓜,一家三口至少可以吃三天。人吃不了,只好喂猪。猪跟着人吃,自然长得油光水亮。丰收的季节,喂猪喂牛不必为食料发愁,既省时间,又少费心。水田彻底闲置,休整大半年,它们也需要好好恢复元气,心安理得歇息一个漫长的冬天。地里的红薯、花生什么的,不到秋后是不会收割的,家家户户暂时都没有要紧的活儿。
最先唤醒春天的鸟儿们不知不觉已经不见踪影。山湾不动声色地做好了季节轮转的准备,整个村庄终于可以长时间闭目养神了。
即便最忙碌的爷爷,现在除了翻晒稻谷和烟叶,大多数时候也是待在院子里躲避毒辣的太阳。今年风调雨顺,爷爷粗略估算了下,大概收了两千五百斤稻谷。除了三个人的口粮和上交的公粮,怎么说也能剩下一千斤,有两百多元的纯收入。晒干的稻谷装进了一个个硕大的箩筐里,摆满了堂屋、阶沿和院坝。爷爷一看见它们就自言自语:“家中有了粮,心里才不慌。”他时不时围着箩筐转悠,随手抓一把稻谷捧在手里端详。大半年来,爷爷终于从早到晚都笑眯眯的了。
爷爷一笑,院子里的一切立即就轻松自在了,黑儿也不用从早到晚躲进柴房里。爷爷一直抱怨,这年头还担心有贼来偷啥,并不需要养条狗看家护院。多一个活物就多一张嘴,咋说都不划算。因此,爷爷对黑儿向来恶声恶气。黑儿也知趣,尽量避开爷爷。米铁桥不嫌弃,也不亲近黑儿。唯有米李花喜爱黑儿,时常为黑儿打抱不平。黑儿不撵鸡鸭,不偷吃鸡蛋鸭蛋,不胡乱咬人。天黑了,它会寻找还没有回家的人。独自一人去山坡上干活儿,只需要唤一声“黑儿”,它就忠心耿耿地跟着。

“只要人不生疮害病,只要不发洪水不天旱,只要猪牛鸡鸭不得瘟病,再苦再累的日子都有盼头儿。我就是想不明白了,大的小的男的女的一个个为啥都得跑出去?我们这里难道就容不下他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房子、土地、柴山坡,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就连生了娃儿都扔家里不管了。有本事生却没有本事养,那还算是人不?晓不晓得唆,猪啊,牛啊,狗啊,猫儿啊,哪个会把自己下的崽儿扔了不管?这年头人还比不上畜生了?就算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难道外面遍地都是钱?就等着他们去白捡?”爷爷戴着破草帽蹲在院坝里翻晒烟叶,兀自絮絮叨叨,“我都懒得说他们了,出去了就不晓得回来。就是猪牛鸡鸭天黑了都晓得落屋,他们还真就比不上我们家的畜生。我就说嘛,他们不回来,我们照样可以把日子过下去。‘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说‘养儿防老’,那都是哪辈子的老皇历了!”
“爷爷,你到阶沿上来歇着吧,当心中暑。我来帮你翻晒。”米铁桥戴着草帽,赤着脚跳下了院坝。青石板被曝晒得滚烫滚烫,他猛地跳了跳脚“嘘”了一声,赶紧跳到阶沿上,穿上了草鞋。
爷孙俩蹲在刺眼的日头下麻利地翻晒满院的烟叶,蒸腾的烟叶味浸淫了整个院落。
爷爷絮絮叨叨:“今年没啥虫害,烟叶又宽大又结实,肯定可以卖个好价钱。我估摸着,咋说也能卖个五十元。”爷爷居然“嘿嘿嘿”笑出了声。
爷孙俩很快翻晒完了烟叶,两个人满头大汗坐在阶沿上扯闲话。
米李花随手摘了两个大大的柚子,扔一个给了米铁桥。兄妹俩各自麻利地剥皮,三个人不约而同吸溜着酸溜溜、清清爽爽的柚子汁。
“今年的柚子也结得特别多。看来,我们家真要转运了。”爷爷乐呵呵望着满院子的瓜果,“再不转运,这日子还有啥盼头儿?老天爷也该开开眼了,我们家这两年遭的灾祸还少吗?唉,提起来我就想落泪。李花不是一再说燕子来我们家筑巢了,我们家真的该转运了。”
米铁桥递了几瓣柚子给爷爷,凑近了些,乐呵呵地说:“爷爷,我算了算,今年我们家的收入应该有一千元,你说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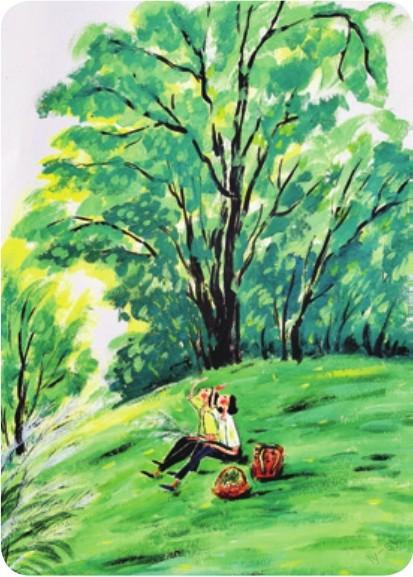
爷爷吃着柚子,好半天才接嘴:“你小声点儿,生怕全世界不晓得?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元。你忘了,你爸爸妈妈还留下了六千元的债务。要是年年都像今年这样顺当,那我们至少也得要七年才能还清。七年后,你晓得不晓得,我都八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能活几年?我要是干不动农活儿了,那些債务哪个来还?全靠你?你咋说还是个半大孩子。我们家要是一直这么穷下去,不怕你不愿意听,再过几年,你到了说亲的年龄,谁肯来提亲?”
“爷爷,你莫说那些,你看下湾的雷二爷,八十几岁了还照样耕田犁地。你可比雷二爷年轻多了。”米李花“嚓嚓嚓”刮着南瓜皮,忍不住插话。
“爷爷,你莫担心,你干不动了,还有我呢。”米铁桥架起了胳膊,“你看,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明年,我们家的黄牛就长大了,你就教我耕田犁地吧,我要跟着你把所有的农活儿学会。你教会了我,你就不用担心啥了。”
“农活儿有啥好学的?那还用学?你看看我咋个做的,跟着做就会了。你还是好好教你的书,教书比种庄稼轻松些。哪怕是代课,不是说还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你要是能成为公办教师,嘿,你这辈子就算是熬出头了。”爷爷敲了敲烟杆,准备抽一锅旱烟,“你是不是还要参加那个啥自啥考试?我看你哪有时间看书?你拿啥去考?”
“爷爷,是自学考试。”米李花更正,忍不住“扑哧”一声。
“爷爷,我想好了,我暂时不参加自学考试了。反正参加自学考试也没有年龄限制,等过几年再说。我先跟你学种庄稼……”米铁桥顿了顿,又凑近了些,看着爷爷皱褶深深的脸,“爷爷,你教我编箩筐的全套技术吧。要是我学会了,我们就能编更多的箩筐。一个箩筐可以卖三块钱,要是我们每个月都能编十个箩筐,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呢。”
“‘嘴巴两张皮,说话不费力’唆?”爷爷吧嗒着铜烟杆,白了米铁桥一眼,“每个月都编十个箩筐,那得用多少竹子?买竹子不要钱唆?不喂猪不喂牛了唆?不种庄稼了唆?说话不经过脑子,亏你想得出来。”
“爷爷,竹子根本就不是问题嘛。张云蛟的爸爸和罗大婆都说过,他们家的竹子我们可以随便砍。”米铁桥站起身跃跃欲试,“再说了,农闲才编嘛。还有,每天晚上少睡一会儿就是了。”
“人家叫你砍你就真去砍?你摸摸你脸皮有多厚?”爷爷啐了一口,“不过嘛,你学了这门手艺也有好处,至少挣几个油盐钱不成问题。说的也是,农闲时候,闲着也是闲着,编几个箩筐倒是也可以解解闷儿,总比坐吃山空强。”
“你啥时候教我?”米铁桥索性蹲在爷爷跟前,望着爷爷,“你就从教我选合适的竹子开始?你剖开篾条打好了箩筐的底子,我编箩筐已经没啥问题了。编箩筐不是技术活儿,剖竹子、切割篾条、打底子、锁口才是关键技术。这些学不会,我永远出不了师。”
爷爷的目光立即移向院前那片郁郁苍苍的慈竹林,他搁下烟杆,缓缓起身,清了清嗓子,说:“你去把弯刀给我拿出来,我们现在就去砍竹子。”
爷孙俩说说笑笑走出了院门,根本不在乎头顶的阳光晒得鸟雀们都出不了声。

“我去摘些瓜果回来。我预告下,今天中午吃苦瓜炒腊肉,还有凉拌黄瓜、茄子和西红柿,还有绿豆大米南瓜粥……还有……”米李花站在他们身后喜滋滋的。
午后,暴雨倾盆而下。
长时间劳碌,谁都疲惫不堪。一家人趁着这难得的清凉,痛痛快快睡午觉。其实,安安稳稳睡个午觉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风声,雨声,鼾声,混合在一起。被篱笆墙圈着的瓦屋一派祥和。
暴风雨是什么时候停歇的,三个人谁都不知道。
随着黑儿的低声吠叫,院门外传来了嘹亮的呼唤:“铁桥,我是云蛟。”
高大敦实的张云蛟笑盈盈地站在院门边,轻声召唤:“黑儿,你不认识我了?”瞥见米铁桥揉着眼睛出现在堂屋门口,他轻轻推开了院门,扯开嗓子说:“你们都在睡午觉?铁桥,暴风雨把我家的好多竹子吹倒了,我爸爸让我来喊你们过去帮忙砍,说你们编箩筐用得着。”

兩个少年快速跑进张云蛟家的竹林,张云蛟的爸爸正在“咔咔咔”砍竹子。这片竹林高高地站在张云蛟家屋后的山坡上。被吹折的竹子东倒西歪,差不多罩住了大半边瓦屋。
张云蛟的爸爸说话干脆利落:“我负责砍那些倒下的,桥娃儿,你晓得咋个选中用的竹子不?我们三个人,索性今天下午就彻底把这片竹林给清理了。”
“谢谢了,张老师。爷爷教过我,我晓得砍哪种。”米铁桥挥动着砍刀,满面笑容地砍起来,“这么多的竹子,编多少箩筐都够用了。”
张云蛟的爸爸问道:“桥娃儿,你自学考试准备得咋样了?再过三个月,可就要考试了。”
“张老师,我决定……暂时不参加考试了。”米铁桥停住了砍刀,慢条斯理地说,“我最近全身心跟我爷爷学编箩筐,等我完全学会了,我们家就可以多编箩筐卖。我想支持妹妹读初中……我爷爷还没有松口。如果我能够挣更多的钱……我爷爷……可能就没啥说的了。”
张老师“哦”了一声,继续挥动着砍刀。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说:“桥娃儿,你的决定也对,事情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辍学了,咋说也得想办法让你妹妹继续读书。她脑子够用,不读书了更可惜。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都是暂时的。”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