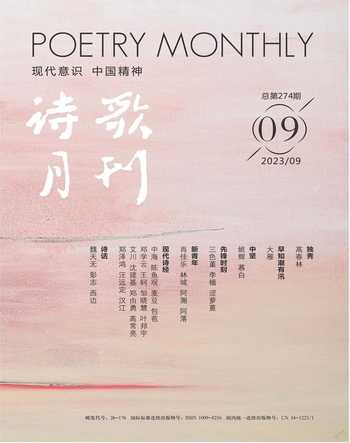请啄用我的银河(组诗)
大雁
乡耳
她听不得深夜的狗吠,每次,跟我回乡下
都带一盒德国产隔音耳塞
我正相反,我会把狗吠撕成一缕一缕,间隔开
仔细种在我耳蜗里
回城,她在柜台后面,在嘈杂的人声中
也可以入睡
我反而在寂静的夜里,辗转难眠,入梦也勉强
可在我梦里
我的耳朵四脚着地,啃骨头、吠蝴蝶、嗅花香
奔向田野,每夜
留下一条黄色疾奔的身影
这样也好,我的耳朵和她的耳朵,就各自安宁吧
无论是生长青草还是满贮人声
原载于《诗刊》2020年6月下半月刊
只有九
停电了
对面那栋巨厦
只有九扇窗口亮起了蜡烛光
我们来形容一下它吧
我身边的诗人说
这有九大朵黑暗
这有九小只在黑暗之蕊上停留的金蜜蜂
轮到我来形容时,来电了
金蜜蜂遮天蔽眼
九朵黑暗要被主人收藏起来了,像这次
烧不完的蜡烛一样
假设明暗交替的光与影,突然失真
进入了永恒照耀阶段
我会记起
世间只得九户心细的人
可以绽开九朵极小
只够自用的反对
原载于《星星》2020年第10期
进化
课桌倒退成树
我倒退成小猴
笔倒退成蝉;笔记倒退成年轮
老师,倒退成白云
课堂,倒退成十万年前的自然
问与答
倒退成雾雨的昏和寥星的晨
考试
倒退成电光破空或雷鸣震耳
最后的欢呼
倒退成新鲜火烬和覆盖一切的大雨
很多人同树多年,就要离别
结了一树酸酸的咽喉
树,与进化无关——我读书十万年
放下课本,用一秒得出结论
——爱一直被加工,那不是进化,那是
梦不愿倒行并呆倚现实的坚壁
我蹲在墙根,听上方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我因故被中断的东西
在世界上丛生
也许我没上大学,但我进化了一点点
树总是点头,我也是。这一刻,我葆有
恰当的孤独和对包裹我的绿化工人制服的喜欢
白花花的城区,像摊开的课本。行道树
有一丝后进生的傻气,犟犟地把大路两侧占领
木桶的一生
我
环绕过一个婴儿
环绕过几双冰凉的脚
我浸过菜、农具
现在我敞开胸膛,装粪
我去过河边和水井,幽会清凉的灵魂
现在我去菜地,私会老实的薯或根
我已经不能进屋
与人同坐同眠。没有装粪的时候
他们只会把我放在阳光里
暴晒
我装阳光——小孩子有时担起阳光
倾倒在喜欢的人的门口……
我发现阳光有点想装我,可我太小了
装我没意义
我有时被人踢几脚,嘭!
沉闷闷的回响,想是显示我
越来越健康也越来越衰老了
我是轻了还是重了?我更接近木还是土?
有人说我朽了,我肉里孕育的
花或菌子,说我要融化了
凹是什么?盛是什么?溢是什么?我是什么?
在流动、轻快、明透的对立面
我活过。或者我的作用,是证明对面活过!
不多想,反正,我记得我久久、严丝合缝地
环绕过短暂
水握
我选择
在他洗手时
伸出手去
要求相握
他慌忙将手
揩向油腻衣摆
我制止了他,也冲湿了
我的手
两只手,滴答着没区别的水
合一
固执使我独爱
和笼头下的流水
握手。导致水和我
都越来越不自信
因为可想而知的
柔和洁
直到他来了,他有只硬邦邦
染了某种重味的右手
这表示我和水依然相握
但有了第三者
不纯粹了
倒有力了
洗洋芋
妈妈在洗洋芋——这是我手术后
第一个梦的情景:洋芋像胆小的瘦婴
妈妈走过轰隆隆的大江,未停
直至浸足于我们家旁的小溪
为受伤的我洗浴
我已经蜷了,僵硬了,沾有土
或许沾有不太干净的梦的丝缕
现在,愿被妈妈
輕柔地搓,暴露出浅黄似金的肤泽
一只老手能把我勉强半裹
在空中小心甩干,再置入
铁脸盆中,用揉软了的报纸盖好
我将以最少的水分蒸发,度过她的安心岁月
这是一颗暂时肿胀的心——能做到的一切
我无手无足,是病所致?
我椭圆近卵,暗孕康复?
我有一身疑惑的凹凸。我枕着自己睡
头次睡出了三分舒服——离了土的窒闷
我回到悬浮又自转的旧家中
妈妈在厨房洗洋芋;我没玩手机,躺于水响中
暗暗笑了,刚才我偷哭过
妈妈你也在笑中哭过吧——以此清洁自己
没人看见,也不费水
上桌了,我最喜欢的芋菜
丝的、片的、粒的;脆的,糯的……
臀下的地球是润湿的——疗伤之床如孕芽之土
我抬眼,只见一条隧道——它是
有尽头的,它如口腔内壁,最暗处
有一个我能付出所有相信的
颤颤唱歌的老女人
请啄用我的银河
两只大公鸡中的一只
明天可能会被宰杀
拿出一些私存的熟干饭粒,撒成小径
我慷慨地献给它俩一条银河
明天早上
忘了摘掉护士帽的那人
倦乏地踩进门,倒头睡下
中午时我也许可以蹭她的鸡汤喝
入夜去找不久前铺设的银河
只剩几粒星子了,我心安
曾经围我左右的公鸡
终于融化进某个人的忙碌里
这个人对我的温柔有限啊
可对别人会像晨风,一阵一阵轻拂
我在偷偷节省、储存新的银河
为了那些黄绒绒、一天天长大
不久后会遁入夜空、去制造宁静的禽类
它们终究会长出抖擞挺立、不肯摘下的头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