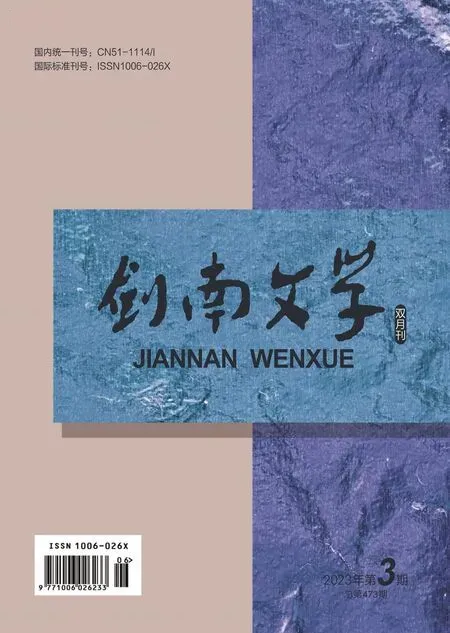木偶戏
□ 黄宗慈
周真宗把缝制好的木偶套在一只手上摇了摇。“摇啊摇、摇啊摇,”他脸上汗涔涔的,用感情特别丰富的嗓音唱,“轮回殿上,判一纸命缴,战场上的两人,仇眼对视,存于心的一念,凝注唯杀!”唱到这里,感觉气氛出来了,赶忙在另一只手上也套进木偶,轰然布阵,两只木偶一起落在桌面,急雨似地奔跑敲打。
“霎时,神决再开新章,太荒崩然失色。”周真宗提高音量,“啊哈!”喝一声,人也跟着站起来,“我乃是号令天下的藏镜人也!”脸上诡异一笑,暗呼:“反派好!没有反派唱什么戏?必须要有反派!”
自从那次出差之后,周真宗这个百万食品推销员的人生,就只剩下木偶戏了。
周真宗褪下木偶,把它们跟其他的木偶归拢到一起。这些木偶戏偶的线脚十分齐整,是周真宗一针一线、长年累月辛苦缝制出来的。缝好之后,还用毛笔蘸着颜料,在塞着棉花的小脑袋上,工笔画出一个一个脸谱。细看它们每个不同的表情,都出自同一张脸面,是那一次出差看到的木偶戏“藏镜人”的眉眼相貌。
周真宗在桌椅间焦躁地来回走,又是满头大汗。这地下室里的冷气机嗡嗡响,却吹不出多少冷风,加上没有自然凉的心境,实在闷热得慌。
那个他出差回故城的夜晚,特别热,半路上且感到饥饿。其实下午跟商家在馆子里吃过,只是那种应酬饭不好吃,总是太忙着探底细、套交情。周真宗真希望凭他自己,可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食品品牌,使人人叫好、处处抢手,他可以凭此在商场上硬碰硬,不需要溜须拍马,大把钞票自然滚滚来。然后早早赚足这一辈子需要的钱,早早退休享受人生。
所谓的享受人生,周真宗很明白要适可而止,就是不能挥霍,譬如,生活简单,只关爱必定要关爱的人。这点周真宗做得很好,他没有挥霍宝贵感情的习性。另外,他梦寐以求的旅游只限定在国内,不对,只限定在亚洲!也不对,只要不妄想太空之旅,就不算挥霍——周真宗无可救药地在这一点上,跟自己讨价还价。
不知不觉间,车子开出公路,在附近几个村镇忽悠悠地转,心里继续漫无边际地想:如果可以每天在豪华邮轮上度日,如果——其实,这么大热的天,只要能够在海边,面对夜色下的海面,听着轰轰的潮声,光脚丫走在松软的沙滩上,让海水一波一波涌上来淹盖脚背,如此,凉凉的海水、凉凉的月光、凉凉的海风,那该多让人享受啊!
忽然,周真宗被一片沸沸扬扬的声光吸引,开车寻过去,到大庙旁边停下。庙前面临时搭盖的戏台正在上演木偶戏,戏台上的男子挥汗如雨,还顿足捶胸地大声吆喝着戏文,加上木偶戏喧闹的乐音,再加上台下攒动的人头,十足一个大汗淋漓的夜晚!广场两边各一排摊贩,周真宗在灌大肠的小吃摊吃起来,一边叫来冰啤酒。听老板娘指着戏台,热心地告诉一个扶着脚踏车的男子:“你一定要看完这出 《藏镜人》,真好看。”
“不看了,该回家了。我今天过生日。”
“过生日喔,有没有吃猪脚面线?”
“吃过了。”男子笑笑,扶着脚踏车走了。
呃,《藏镜人》。周真宗从不知道木偶戏有这些名堂。他灌下两瓶啤酒,一点酒精居然在肚里掀腾。今晚老感到轻飘飘的,大概刚成交的大笔生意让他太兴奋了。他又替老板赚进一笔钱,周真宗自己的红利当然也为数可观。原来以为食品是小生意,可是周真宗经手的都是百万元的订单。
周真宗站起来,参观一个一个小吃摊,戏台上肺活量充沛的男嗓音继续在热情地喊:“金光闪闪,瑞气千条,大人物出现!”顿时台上砰砰乱响,台下一阵拍手叫好。周真宗站在人群后面,兴味盎然地看了一会,借着酒意和一身热汗,没头没脑地大声念:“金光闪闪,一阵冷风吹过!”喊完,对着两边投过来的眼光笑笑,接着到外面找车。车门一关,大庙前的人声一下被关到窗外。车里的时钟指向九点半,如果开快一点,再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家。
周真宗倒车,慢慢把车子开上暗沉沉的小路。小路在微微隆起的坡地上,笔直地伸向天涯海角。周真宗猜想快要上高速公路了,他加速急驶,两旁不知什么景物飞驰而过,天地间只剩下他和他的蓝色本田。朗朗明月把车灯照耀下的路面照得更亮,把车灯照不到的两边衬得更昏暗。
路两边的斜坡下,朦朦胧胧浮现黑黑的田野。就在那时,那辆脚踏车从黑暗里蹦出来。不对,周真宗是感觉撞击之后,才看到一件重物打在车窗上。是一个人体,打到右边的车窗再弹出去了。明晃晃的车灯里,一个男体摊开四肢,像大鸟一样飞起来再降落,然后侧脸趴伏在路边。是那个吃过猪脚面线的男子的脸,不远处摔下一堆支离残破的脚踏车。
这瞬间发生的一切,快得像电光石火,他措手不及,大脑里面“轰”的一声,急踩刹车,整个人扑在驾驶盘上,一阵心胆俱裂!周真宗盲目地再踩油门,向前没命地狂奔。肚里不知胃还是肠子,这时统统纠缠到一起,一根根、一寸寸地打结,打上死结,把他痛得冷汗直冒。
车子驶过一个小站,周真宗才稍微平复下来,却发现两只膝盖一直都在止不住地颤抖,需要两手很用力按住才勉强压下。“终于到家了。”周真宗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车子开到家旁边的停车场。
停车场很黑,其实只是一小块空地租给三家人停车。周真宗下车,软绵绵地摔了一跤,跪在沙石地上一阵发呆。终于撑起来拿着手电筒照车头,右边车窗上千百条裂纹,好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罩住千百个碎片,硬撑在那里。就像他的人生,在刚才那一霎已经粉碎了。
周真宗回到车里坐下,不知过了多久才出来,在巷子里走着。远远的,迎面两盏强光照射过来,周真宗退到墙边的黑影里。车子来到他身边,里面的男人摇下车窗:“阿宗,我一直要告诉你啊,就是碰不到,拜托你停车的时候靠边一点。你每次停太当中,我很难把车开进去。不好意思啊。”
周真宗机械地答应:“好的。”忽又惶然说:“我没有开车,我不会开车啊。”
那人一愣,转而笑了,没有再说什么,把车开走。巷子里一连好几扇红门,周真宗打开其中一扇,经过种着芭蕉树的院落,上到二楼,他太太黄媚照例在入口的玄关为他留了灯。周真宗直接到开足冷气的卧室躺下,黄媚在黑暗中偎过来。周真宗没有拥抱她,只感觉眼里干枯无泪。
“我一直等你到十一点才睡下。”黄媚说。
周真宗翻身背对黄媚,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直到听见黄媚轻微的鼾声,才因为实在疲倦,跟着入睡。恍恍惚惚间,周真宗来到田垄上,见一人坐在那里忽然摘下头,两手掰开头壳,开始一高一低抽着线,很认真地缝合里面肿胀的大脑。
周真宗看得“啊”一声大叫醒来,在冰窖一般的卧室里,周真宗汗流浃背,不敢再合眼。周真宗知道那人一定死了,周真宗自己也死了,就在那一个出差之后的夏夜。事发之后,受害者和肇事者一起死了。
周真宗从此无法在夜里入睡,只能在天将亮之际,黄媚赶着送两个女儿去幼儿园的那一点时间里,迷迷糊糊地昏睡一会。家人不在的空屋使他恐慌,外面的人海让他畏缩,更从此不敢碰车子。如此,白天、夜晚皆精神萎靡,那个梦境变得像幻影。幻影眼熟了,周真宗看清那个坐在田垄上的人脸,是那个吃过猪脚面线的男子,脸庞上有长过青春痘的痕迹。
周真宗哆哆嗦嗦地当场跪倒。“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这模样被进门的黄媚撞见,惊讶地问:“你怎么了?故意怎么了?”
周真宗依旧跪在地上,脸埋在两膝间啜泣:“我已经死去了!我已经死去了!”
黄媚替他辞去工作,过了三年,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女儿移居海外。原以为彻底改变环境,可以重新生活,没想到那个噩梦也跟着出国,周真宗还是无法在天黑之后合眼。漫漫长夜,周真宗养成在地下室听木偶戏的习惯。听得多了,自己也动手做木偶玩起来。两个女儿也跟着玩木偶戏,还在春节表演给同学看。缝木偶这件闲事,因此变得理直气壮。
黄媚做着两份工,一份是每天清晨五点到九点,在肉市做分装的工作,中午再到一家中餐馆做收银员。这样辛苦工作十多年,积存到一笔钱,更累积了宝贵经验。黄媚跟餐馆熟客唐太太交上朋友,两人在华人聚集的唐人街合开了一间餐馆。黄媚的生活圈虽然渐渐复杂,对周真宗的关照却始终如一。黄媚相信,那个溽暑的夜晚如果没有出过怪事,她能干的老公一定会凭自己的努力,变成千万富翁。虽然黄媚至今不清楚,那个夜晚出了什么事,但他对于亲友间纷传“撞邪”的说法,一直半信半疑。
“今天唐先生又去厨房里帮忙,我看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剥洋葱,就做了一杯珍珠奶茶请他喝。”黄媚深夜回家,经常告诉他餐馆里的琐琐碎碎。周真宗早就听说,唐先生自从二十年前出过车祸,人就显得呆笨。唐太太偶尔带他去餐馆打杂,免得他每天窝在家里。
这点跟周真宗的遭遇很像,两位太太除了做生意伙伴,相互间也特别体贴。周真宗从未去餐馆露脸,唐太太偶尔去他们家,匆忙进出时两人照过面,平常也没有来往。餐馆生意十分辛苦,两家人没有其他朋友,生活单调乏味。
“我实在看不出,唐先生从前会打太太,听说他原来脾气火爆,经常对唐太太拳打脚踢。”
周真宗听得微微一笑:“有这种事?”
“是啊,唐太太说的。她不会乱讲话,没什么好乱讲的。”黄媚转身上楼。周真宗见她好像不高兴了,也没有说什么。周真宗总觉得事不关己,到如今,除了气候,没有什么会影响他。黄媚前几天给他一包零头布,让他努力缝木偶,“只要手工做的都值钱,老公你就多多地缝,我将来替你卖。”
黄媚这一鼓励,周真宗的动作反而慢下来。周真宗认定自己活在洞穴里,或者像幽灵,他自己也不知所以,更从未想过做木偶赚钱。最近那张熟悉的吃过猪脚面线的脸,显得老迈富态起来,也不再摘下脑袋吓唬周真宗,只是神态从容地凝注双眼,跟周真宗四目对看。
周真宗经常被看得移开眼光,只有这样的时候能催促他一针一线、一起一落加紧缝木偶。“灵通长老仔细听着,云州有一名自称大儒侠之人,向本镜而来,此人乃属于太阳星宿。”周真宗在自己嘟嘟囔囔的唱念声中镇定自如。这是他缝木偶必诵的经,所有的妖魔鬼怪都降服在他的诵经声里。他每天凝神聚气,把整套整套的戏文反复背诵。
他们家几乎从不开火,两个女儿放学直接去餐馆吃饭兼跑堂。周真宗自个在家,随时热剩菜,按说已经非常方便。他却日渐疏懒,现在连微波炉热菜都嫌烦,只等母女三人下班回家,为他带饭菜回来吃。如果两手空空回来,他就什么都不吃。他的妻女俨然成了朝圣的门徒,而他就是在深山修行无所谓吃饭的印度高僧。
这一日,黄媚又带回他喜欢的滑蛋炒饭。周真宗已经一天没有进食,打开炒饭,依旧一口一口严肃地送进嘴里。黄媚在旁边拆看邮件,一边说:“下星期四是你的五十大寿,我已经订好一桌酒席。我们跟唐家两口,带上餐馆员工一起庆祝。”
周真宗听得呛出一口饭,连声拒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你从来不去餐馆,不知道我们餐馆里面也有宴会厅。里面安安静静,你见不到别人的。”
周真宗黯然无语,黄媚接下说:“五十大寿不做,人要倒霉的。”
“胡说八道!我就不过五十大寿。”周真宗突然发火。
黄媚着急起来:“五十大寿我都不给你做,人家会怎么说我?而且,你每天关在屋里关了多少年了?我们所在的国家长什么样,你知道吗?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你知道吗?”
周真宗哑口无言。到了星期四晚上,他的大女儿周欢开车回家接他,周真宗穿着过时的西装,委屈地跟周欢从餐馆的后门直接进宴会厅,迎面一张大圆桌铺着大红桌布,上面一套套餐具已经摆好。周欢扔下他说:“爸,你跟唐叔叔聊一会,我们大家略等一下过来。”
周真宗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唐先生,唐先生颤巍巍坐在背对门口的位置上,穿一身雪白西装,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才转过头。他打着浅蓝条纹的领花,领花上的脸清瘦苍白、略显浮肿,转头的姿势因为缓慢,显得像旋转的木偶。周真宗一下呆住:“是你啊——这次你的头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我每次都告诉你不会。你老是喊说我的头会掉下来,我每次都告诉你说不会、不会。”唐先生口齿不清却焦急地答。
“咦,你们认识吗?”黄媚跟唐太太同时进来,一起问。
周真宗跟唐先生心无旁骛地一起凝目对视,周真宗于是双手合十,嘴里开始咕咕哝哝地念:“摇呀摇,摇呀摇,风吹飘摇,人死过桥,十年恩十年怨,回首残照——”
“我每次都告诉你,你唱木偶戏好像在念经,不好听啦。”唐先生又是口齿不清地说。
“他们真的认识!”两位太太一起惊呼。
“请坐呀,寿星。”唐太太首先回过神来,把周真宗推到唐先生旁边的主位,“两位先生这么有缘,早该见面。我们太不会办事了,真是罪过。”
黄媚惊疑不定,张着嘴说不出话。厨房不停送菜进来摆满一桌,人也渐渐到齐,连大厨都抽空出来敬酒。
黄媚已经镇定下来,脸色平和地看着手足无措的周真宗和唐先生,忽然若有所悟地问:“老公,你们两位是那年你出差的路上认识的吧?”
周真宗没有听进去黄媚在说些什么,却瞬间站起身,拨开唐先生的头发:“就是这条疤,我看过的,就是这一条。缝合线这么难看,好像蚯蚓在爬,一点也没有我的木偶缝得好。”
唐先生突然眼泪汪汪地望住周真宗:“医生缝得不好看,麻醉也上得不够,我好一阵痛啊。”
“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没事了,我们都挺过来了。”周真宗把那颗头颅轻拥入怀,“现在没事了。”
次日,周真宗第一次开车送黄媚去餐馆。开车的技术在几分钟适应之后就跟二十年前一样,毫不含糊。周真宗惦记着唐先生,从今而后他的时间和精力、他全部的余生都属于唐先生。
周真宗带着一箱 《藏镜人》 的木偶,这些木便多半横眉怒目,此时再看,却一个个摇身变得慈悲、憨厚起来。那一个溽暑的夜晚,唐先生没有看完的“藏镜人”,周真宗要表演给他看。周真宗把唐先生的地址设定好,然后哼着烂熟的戏文,右脚轻踩油门:“灵通长老仔细听着,云州有一名自称大儒侠之人,向本镜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