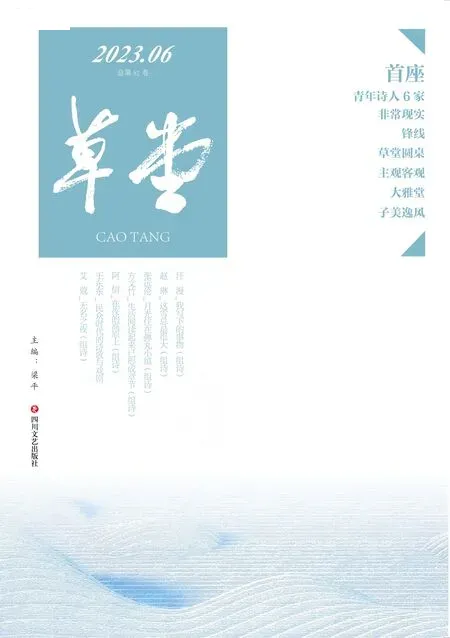在夜的高原上(组诗)
◎阿 信
[一块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牧羊人和他的影子坐着。
在一块石头里供着一座灰烬寺庙。
在一块石头被另一块石头撞响之前,落日
带着告别的长笛,与万物一一揖别。
在一块石头上留下灼热体液的雄性动物,
已在长风中解体。
在一块石头上雕刻点什么吧,不为记忆
只让小锤和錾子,在暗夜敲出簇簇火星。
在一块石头上雪花飘落,覆盖过往一切痕迹。
[在夜的高原上]
河流醒来,在夜的高原上。
黑色河面在发光,
那种暗沉的光。
河流只有在星月下才能真正地醒来:
古老的星月,唤醒血脉。
蛮荒中的生命负荷重力,充满野性。
牦牛群无垢的瞳孔,瞬间涨起血潮。
[记 忆]
伤口慢慢愈合。边缘泛绿
春雪在视域里模糊一片。
大陆深处,葬礼中的面孔肃穆眼神清凉哀伤。
背景的针叶林发出阵阵啸鸣:雪鸮鸟
正从那里箭矢般飞离。
一头熊,缠着绷带,兀自在荒原踯躅。
[心 经]
这一部河流的成长史,我们来读读。
或者,在星辰的微光下,收束气息,披霜而坐。
只我和你,在大地勉力修持。
[马]
马停留的地方雨脚密集。这马
没有人骑,它驻足在雨水中。马背
溅起水光,马的腹股沟滂沱一片。
我遇见过这匹马,我无法说清我
当时的感觉。
我在草原腹地的一顶帐篷里,而它
在天地之间。它似乎是
沉浸在漫天的雨水中。
就像我在庭院栽种下一棵樱桃树
我爱它,没有理由。
[雪中的湖]
雪中的湖
几个黑点(牦牛?),缓缓向边缘移动。
雪中的湖,被遗忘的上师,独自
冥想、静修,体验着瑜伽。
雪中的湖,地衣在暗处滋生;猫科
动物在月夜逡巡……
雪中的湖: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冷艳神秘
不可近亵。
雪中的湖,二十座雪山
供养着它。
雪中的湖,
通过一条暗河,源源向你输送。
[烤紫薯的味道]
烤紫薯的味道,在下桥后
通往篱笆小院的土路上,刚好闻见。
雪中那人,
明显加紧了脚步。
柴门紧闭,烤紫薯的味道
还是溢出来。
风愈紧,雪愈急,
那味道,飘出愈远,愈温暖、香醇。
雪中那人,裹紧衣服
侧身,低头,走得愈疾。
大片大片
苍茫风景,被抛在身后。
[经幡隧道]
本来是没有经幡隧道的。甚至
这条路也不存在。
椭圆形会议桌上,摊开一份
新景区规划图,几个脑袋围了上去。
皮卡车载来手拿经纬仪和游动标尺的人,他们
在雨雪中支起简陋的野营帐篷,住了几天。
高山草甸腹地,旗帜一样的
红花绿绒蒿开了(我眼里的星星亮了)。
那个夏天,挖掘机切开草原的皮肤,
露出黑暗的泥炭层、紫色的沙岩、幽灵似的
白色岩石……那些日子,
牧人骑着马,远远地驻足观望。
牛羊的身体出现反应,患上了严重的夜盲症,
接连撞翻几处围栏,和一辆
停放在坡地的摩托车。
鹰和乌鸦,像两组
遭到禁忌的词语,不再飞临这里的天空。
还有没有人记起:佐盖多玛乡的美仁草原
在星空下有多么美,多么幽静和寂寥?
几场秋雨过后,初雪如期降临。初雪
验收了一条蟒蛇般蜿蜒盘旋的水泥路。
人们惊奇地发现:事情并未变得更糟。
天空依然湛蓝,草原更加辽远,水嘛呢
风车一样转动。
镜头中一度缺失的巨型禽鸟,像从传说中
众神聚集的石头城堡再度起航,掠过
白首的阿尼玛卿神山,穿越
蜀锦般绚丽的云层,翩然飞临。
而牛羊,在啃食了十二世纪
自古波斯引进的
富含维生素A 的胡萝卜后,恢复了原初
清澈、能睹见神明的眼神。
岑寂的荒甸,涌来
潮水般的游客。
“本来是没有经幡隧道的。”但现在
出现了一条:像座头鲸穿越正在回溯的鱼群——
一条深海沟,彩色、透明的通道,
在刺目的光芒
和沁凉的草地气息之间。
人们试图抓住:那些从飞舞的经幡缝隙遗落、
又稍纵即逝的
“吉光片羽”,但注定是徒劳的。
失重的感觉正如那部著名小说所写:
“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所幸,在道路两侧,一望无垠的荒甸上
星空帐篷也建起来了:像一串串
晶亮的泡沫。
困于资本、新元素、抑郁症和人际关系学的人们,
通过预约,提前透支虫鸣、霜露,被夜色谨慎
包裹着的荒野的恐惧,
仿佛一躺下,就能重回人类的蒙昧时代;
一仰面,就能阅读浩瀚星空壮丽的史诗。
*语出当代作家弋舟的同名短篇小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