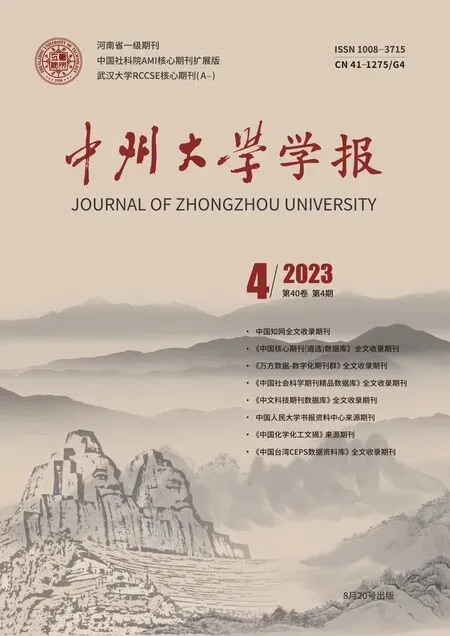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刘鹏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9年10月《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本质上,“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认同,其重要基础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文化传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各族人民创造,并世代传承、享用的活态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正是以非遗为中心,将非遗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整体保护起来,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延续活态的民族文化。自2007年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个具有地方性、文化特色鲜明、空间分散的区域文化保护举措,而维护地方文化生态、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保护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何协同?这一问题需要从建设逻辑上辨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也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辨析区域文化生态的生成机制,并分析其与维护族群生态、促进国族的认同的关系。
二、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
(一)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
人类关于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的 “环境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机械的“决定”了文化怎样去适应,早期将该观点运用于人类学的理论常被称为“人类地理学”。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可能论”。可能论源起于“历史特殊论”的博厄斯(Boas),其主要观点是环境只是一种限制或许可的因素,“环境的重要作用在于解释一些文化特质为什么没有出现,而不是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会产生”[1]。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文化生态学是文化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第三阶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人文学科。1955年,文化生态学的先驱斯图尔德发表《文化变迁理论》,把说明不同地域的、各具特点的特殊文化和文化类型的起源这一领域定义为文化生态学。
他将“生态适应”(人类以其生产技术开发环境资源以谋社会生活的过程)引入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注重解释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技术)、使技术与资源结合的社会组织等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核心”的概念,指“与生产与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合”[2]。并将“其他与文化核心关联较弱的文化特质,称之为次要特质”[2]。当然,无论是核心特质还是次要特质都是相互依赖的,只是在研究中,他将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思想意识等放在次要地位。
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都指出环境的客观基础作用,只是文化生态学更精确地指出“特殊环境”与“特殊文化”的对应关系。如梅州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围龙屋建筑,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区的土楼建筑,都是以不同的山区丘陵环境为基础的;再如海洋渔文化(象山)保护区,以海洋渔业资源形成了核心生计方式,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有 “开渔节”、鱼灯、渔鼓,特色饮食等非遗,与农耕文化迥异;再如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则以陶瓷文化为特色。
从上述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看,人类对自然环境创造性的利用,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斯图尔德指出文化生态学旨在寻求“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是如何协同共变的”[2],这一视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色呈现”[3]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启示,而区域内的特色文化往往是凝聚文化认同的纽带。
(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与族群生态
如前所述,早期文化生态学关于区域文化的形成,关注的“核心”是一定环境中资源被利用的技术手段和过程。但由于各种文化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斯图尔德所指出的“文化核心”就有与整体化为一体的危险。“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避免了这一困难。他通过追溯各种文化特征——它们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居住模式、宗教信仰和礼仪——同环境因素的联系来论证它们适应环境的、唯物的合理性”[4]。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如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以苗族、侗族为主,境内还有汉、水、瑶、壮、布依族、土家等民族。这些“临近的人群”既相互区分又密切交流,形成不同的节日、舞蹈、音乐文化,正是在“彼群”与“我群”的区分与交流中,产生了既彼此区隔又相互联系的地区族群。
就全国而言,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实体。如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三者是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人口的流动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区域文化;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则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其他则有汉族、藏族等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中国整体大区域的视角上看,上述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生态区的形成,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人口流动、汉族、各少数民族竞争与交融的结果。这些不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族群,实际上也是彼此互为生态环境的。
总的来说,拉帕波特、R·内亭推进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将“环境”的外延扩展,不再局限于自然,而是将相邻人群的影响纳入环境要素。也即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互为彼此的“生态环境”,可以称之为“族群生态”,族群生态也是文化生态的一个部分。
(三)文化实践与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
虽然,文化生态学的先驱之一拉帕波特已经注意到同一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影响,R·内亭也将“邻近的人群”纳入“环境”的范畴。但是,“斯图尔德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既不是自然,也不是负载着文化的人,而是资源被利用的过程”[5];而拉帕波特、马文·哈里斯等则尝试通过数据的收集,按照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系统,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研究受到批评。
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 “结构主义”“象征(符号)主义”“文化生态学”三个理论流派中,符号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之间针锋相对:“文化生态学者认为符号人类学者采取主观的阐释途径既不科学,又无法验证;而符号人类学者则认为那些文化生态学者都是唯科学主义者,只知道计算卡路里,测量降雨量,就是不肯正视人类学迄今所能确立的唯一真理,那就是:文化是人类所有行为的中介。”
而区域内的文化实践并不是被动受制于文化结构的约束,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人’: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
因而,在文化实践的角度上,特定区域内的文化生态是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并发展变迁的。现在的文化生态,是在过去文化生态变迁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生态是动态延续的。例如,海洋渔文化(象山)保护区内的渔民,自古以来就有开捕祭海的习俗,表达了出海平安的祈愿;当地政府将该仪式上升到一个盛大的典礼,祭海、开船等仪式传承了中华传统的“顺时取物”[6]思想;而其中有政府、渔民、游客、商业人士等不同人员的参与,并利用互联网采用了“云开渔”的新形式,其仪式内涵已经集文化、旅游、商贸为一体。新的开渔节并非简单地复刻传统,而是不同行为主体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形成的“传统的发明”,其组织逻辑、文化内涵、仪式形式都已发生变迁。因此,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注重人的作用,鼓励民众自觉参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而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保护区内文化、经济与社会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又是在不同人群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而区域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传统、区域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上的,因而,也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系统性。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激活地域文化认同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历程
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文社图发〔2004〕11号),其附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了设立1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2007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建设成熟后正式更名保护区)。
2010年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0〕7号),确立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条件。随后,2011年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在规范工作和规划编制方面做到了相对统一。
2019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指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至2022年,我国已建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七个已经正式更名为保护区,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生态保护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命名类型有以民族区域、区域文化命名的;也有以文化类型、特色文化命名的;有跨省区的也有不跨省的,研究者多有分析,不再赘述。而如何整体上保护文化生态,使其区别于对单个非遗项目的保护,则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上进行分析,明晰保护对象和内容,并形成系统建设模式。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目标,是为了延续非遗的生命力,也即“非遗的活态传承”;而从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来看,其保护对象应是整体的文化生态。将前述斯图尔德、马文·哈里斯、R·内亭等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的保护内容。
第一,是与非遗紧密相关的“有效环境”。包括:(1)生计活动所依赖的环境资源、传统古建筑、文物古迹周边的环境等。福建客家的土楼、梅州客家的围龙屋,都是与山地、丘陵的自然环境相依存,聚族而居且具有防御功能,其周边的自然环境应统一保护。
(2) 与非遗直接相关的自然资源。自然物质如石头、泥土、金属、木材、毛皮、纤维等被手艺人拿来加工改造。饮食制作代表地方特色,与物产、水土、气候等密切相关;而各类中药材的生长也需要特定的水土条件。具体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如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的海盐晒制技艺、闽南的制茶技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徽州三雕、宣纸制作、歙砚制作、徽墨制作”等。
(3)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不同族群及其生产、生活空间。非遗产生于民俗生活中,因此族群的生活空间、居住模式都应得到保护。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既有藏族、羌族还有回族;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多民族共存的范例,境内有藏、傈僳、纳西、汉、白、回、彝、苗、普米等九个世居民族,对这些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空间都应加强保护。与非遗文化产业相关的,则是对古镇、古街区的保护,并引导、鼓励非遗传承人入住。
第二,保护与非遗紧密联系的文化空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文化空间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这里包括传统节庆活动、民俗活动,也包括一些信仰、仪式举行的场所,如古庙宇、祠堂等。
第三,保护民间信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信仰与仪式具有调节社会关系、调节资源利用的功能。而作为象征的秩序,信仰与仪式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凝聚人群或族群,激活集体记忆,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其意义往往通过非遗的展演呈现出来。
第四,鼓励民众参与,保护与非遗相关的社会组织。文化是由人来传承和创新的,除常规的传承人保护制度外,还需要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恢复或支持传统的行业组织、民俗活动组织,二是引导建立新的文化保护组织。
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综合在一起构成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不再是针对特定非遗项目的保护措施,而是综合运用积极的和消极的文化政策,形成系统的建设,在对“自然——文化——人”三位一体的整体保护中,激活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内容
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域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地域认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7]不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在多样的地域文化生态保护中,如何促进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还需进一步探究。
(一)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
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是在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形成的,其文化传统、民俗风貌,也会受到外来文化、全国性文化制度的影响。
以客家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在清康熙以前,在粤东梅州地区的三类人群区别明显:一类是定居农耕的土民,也即王朝治内的编户齐民,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山谷盆地;一类是以游耕、狩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猺、畲人群,占据着山区林地;一类是以捕鱼为业的水上居民(文献称之为疍民或疍户),以舟为家,占据着河流。
上述三类人群,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彼此交流竞争。从明代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对猺人、疍民进行“编户齐民”的过程,至清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发布上谕令疍民上岸,削去疍民的贱籍。成为编户齐民,获得合法的地位,就要追溯祖先的历史,编纂族谱。
随着明清时期对闽赣粤交界处的进一步开发,儒家文化和国家礼制的影响,明清庶民化宗族建设的进程也扩散到梅州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该区域内的人群已经在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形成了某些同质性。当18世纪以后,粤东梅州的“客人”向珠江三角洲一带发展,与“广府”人竞争生存资源,矛盾积累激化,引起了19世纪的“土客械斗”,反向促成了客家人族群自觉意识。强调祖先的迁徙史和“中原正统”成为客家人的普遍认同。
而建立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后,粤东梅州的以围龙屋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祠堂、名人故居、书院得以修复,与之相关的宗族祭祀、丧葬礼俗中“香花佛事”仪式,祠堂修复时“安龙转火”的民俗仪式通过非遗保护获得合法途径。民间艺术如客家山歌等,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兴建的客家博物馆、非遗展示馆都是透过“地方的生产”建构记忆。而无形的非遗通过对器物、物质空间的激活,使物质遗产与仪式产生联结,最终成为仪式意义的一部分。也使得祖先、宗族的历史,村落以至区域的整个历史记忆被激活。
一个地域文化的空间,具有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通过文化生态的综合保护,不同时代、社会下产生的空间遗迹与活态的非遗一起,再现了村落、区域、族群的历史,伴随着客家宗族活动、民俗仪式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和空间的再生产,从而凝聚了客家作为汉族一个民系的族群认同。
(二)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
在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有14个,这些区域内是多族群共生的,不同族群形成了各有特色又相互交流的历史、文化。文化生态学家拉帕波特曾提出“地区人群”的概念,认为“尽管通过借用动物生态学的标准来指定一个地方群体所在的地域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可能的,但千万别忘了任何地方人群的环境都可能不止包括紧邻的地方实体……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地人同样可能参与地区系统……这些系统包括他们最重要的要素中在常规地区中占据独特地区的几个地方人群。这些独特的当地人的总和可称为‘地区人群’”。
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占据不同的资源环境,同时这些处于“当地”的不同族群也彼此互为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交流文化、互换资源产品。例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区。汶川、理县都是汉、羌、藏、回四族混居的地方;茂县羌族人口比例最高,北川则汉化程度较高。羌族生活的生态环境是在高山间的深谷中,称之为“沟”,羌族的村寨建在沟两边的半山坡。他们农牧兼营,也与其他族群货物交易。
在这种多民族共处的族群生态中,羌族在文化上形成汉与藏之间的过渡形态;在文化认同上,邻近汉族的羌族认同汉族,邻近藏族的羌族则更认同藏族。羌族也通过追溯同姓的祖先、迁徙历史,或在传说中将远祖追溯到炎帝、大禹,来获得对等的族群地位。[8]74
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羌族的村寨逐渐空心化,民族语言、文化受到冲击。特别是震后,很多羌族村寨坍塌、废弃,居住环境和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其震后的家园重建“融入了以保护非遗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建设,羌族民众的居住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得以重建”[9]。典型的传统村寨如理县桃坪羌寨、茂县黑虎寨等得到修复;北川新县城的建设融入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建设传习所丰富了非遗的传承空间;发展文化产业,羌绣、羌族草编技艺等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措施都起到提升族群文化自信的作用,既维护了羌族的文化传统,又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而维护了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
(三)文化资源转化与资源环境共享
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已经以一种新的、陌生的方式将全球和地方区域联系起来,区域内的城镇、乡村都不能避免这一趋势。国家、资本和技术科学引导的全球化策略,导致日益明显的“去地域化”效应,也即全球化忽略了地方的、区域文化的特殊性。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文化多样性”旨在重申地方特色的重要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重视地方文化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接合地方市场而非全球资本的需要。“而矛盾的是,依赖地域、文化、生态的在地化策略,在遇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时,依然需要将自己投射到资本与现代化的全球尺度上。”这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非遗的产业化、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地方的真实性为基础,充分认识到“以地方为基础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实践,是重构地方与区域世界的另类视野和策略”。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明确了传统工艺振兴应以传统技能为基础,地方文化旅游业的开发必须依赖地域特色。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乡村振兴、扶贫脱困、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基于文化本真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
从生态人类学“族群生态”的角度看,不同的族群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也即占有不同的生态资源、空间,因而形成地域特色文化。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9]1而不同地域、族群的区分和认同之生态背景是“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区域的政策扶助,如“西部大开发”等。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区域族群共享资源环境的一种新的举措。通过生态修复和文化再造,不同区域族群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地方特色为“他者”所理解、共享;而反观“他者”的文化,也使自身的文化自觉得以明晰。如此一来,使得“我群”和“他群”对彼此的文化、生活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形成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格局。
五、结语
将“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作为不同族群的形成和族群认同的生态背景,是历史人类学的一种观点。文化生态学关于“族群生态”和“地区族群”的研究,也指出不同的族群占据着不同的“人类生态位”,在族群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互为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交流与竞争。也就是说,在区域文化的形成和族群认同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是一致的。全国性文化制度在不同层面、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区域形成整合的力量,也使不同区域的历史进程嵌合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通过对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文化传统“再造”,充分维护区域的地方特色,在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时,激发区域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资源环境共享的良好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也是双向互动的:在国家层面,为维护文化生态平衡,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政策,与地方政府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目的结合起来,形成了影响地方社会的合力。最终,通过对区域文化传统的发掘、文化生态整体的保护,激活了区域的历史记忆,在传承中创新文化,促进区域文化自信的同时也促进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