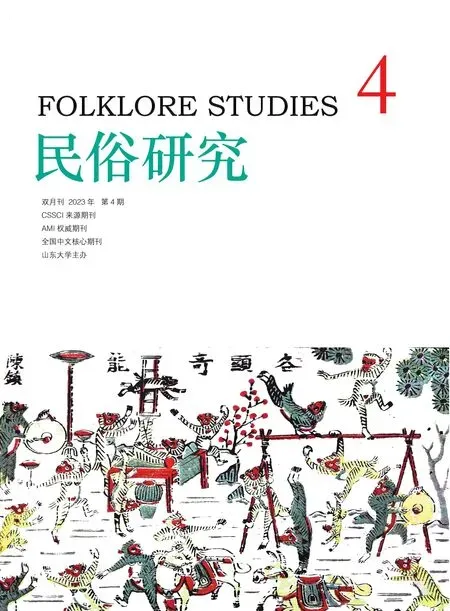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刘铁梁
一、文明视野与“民俗文化学”
钟敬文在百年人生的最后二十几年里,赶上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适应时代需要而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他出于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将时间和精力主要投放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不仅主编了《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而且发表了一系列主张将民俗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以《“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1989)、《民俗文化学发凡》(1991)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等为代表,系统地表达出他晚年学术思想的最新发展,特别具有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指引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钟敬文从民俗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中的地位问题开始深入思考,一直到“民俗文化学”的创造性提出,再到“中国民俗学派”的有力倡导,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和历尽各种风浪考验的老一代学者所具备的文明视野,确切地说就是面向中西文明之间关系的学术视野。这种视野,形成于近代以来中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互相碰撞、交流的现实环境,也形成于他对这种环境的意识醒觉、深切感受和行动反应。
当然,看一位学者有没有文明视野,有怎样的文明视野,有没有看到怎样的人类历史与世界格局的视野,都还会受到他所在的时代、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和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等条件的影响。钟敬文晚年所提出的“民俗文化学”思想,着重阐述了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的基础部分和深层部分,民俗学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等重要观点,体现出他此时的文明视野,已经与他在年轻时研究民俗、民间文学的文明视野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他受英国人类学派和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而形成“‘将民俗作为文化现象’的初步观点”(1)钟敬文:“著者自序”,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著者自序”第2页。,但是在那个年代,从国外舶来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大多都是渗透了一元进化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缺乏多元主体并存与互相交流的文明观。相比之下,晚年钟敬文的“民俗文化学”思想,却主要体现出多元和多主体的文明观,是在坚持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及其学术研究话语主体性的原则下,推进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新征程。而且,他正是以这一民俗文化学思想作为基石,才颇为自信地发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声音。
钟敬文晚年学术思想中的文明视野更加明晰化,或者说更加注意在文明论的框架下讨论问题。这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的那一场被称为“文化热”的大讨论。钟敬文被卷入其中,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位来自民俗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单枪匹马地被卷入其中。他因此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价值、重视民俗文化在其中重要地位等问题的讨论文章,后来都被集中收入《话说民间文化》(1990)、《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1996)之“民俗文化篇”中。这就为他文明视野的进一步形成和表达,提供了一个现实契机。他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对于文化问题讨论得很起劲(有人称它为‘文化热’),我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参加了这种学术活动”,“因为这些原因,我就创造了‘民俗文化学’这个新术语,用以涵盖‘五四’时期那些涉及民众文化的学术活动”,给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2)参见钟敬文:“著者自序”,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著者自序”第6页。
20世纪80年代以前,钟敬文很少使用“文明”这一名词,而在80年代以后,其文章中才多次出现这一名词,经常用“文明古国”来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主要是采取复数的人类文明的意涵。(3)梁治平总结了晚清以来直到当今,“文明”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和官方话语传播与运用中的不同内涵,大体可以分为“大写的”文明论和“复数的”文明论这两种,考察的一些著述都是在这二者之间有所选择或者兼顾,参见梁治平:《“文明”面临考验——当代中国文明话语流变》,《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然而,我们体会出钟敬文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所具有的文明视野,并不是因为看到他使用“文明”一词的增多,而主要是因为他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概念和首创“民俗文化学”概念的时候,在论述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和今后方向的时候,都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了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比如,他在《民俗文化学发凡》结束语中,将“民俗文化研究”与“历史(文明史)叙述”结合为一个整体,指出:“全人类民俗文化(各民族的基础文化)的科学研究和历史(文明史)叙述,正有待我们这个古国兼大国的这方面的学术成就给以助力。”(4)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34页。又如,他还使用“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概念,以此来审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古代风俗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说:
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因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等于古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型期。……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足迹也已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动荡。它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5)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
意思是,判断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的时间,不能只看到“五四”歌谣学运动这个标志性事件,还要看到在这之前,一批近代思想先驱,受世界格局和中西文明关系变化的影响,已经对民俗有了不同于过去的看法。(6)关于从古代风俗观向现代民俗观过渡的问题,钟敬文在20世纪60年代着力撰写了几篇论文,特别注意考察晚清时期出现的具有“现代的”“科学的”民间文艺观念的著述或创作,都体现出他本人以“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来看学术古今变化的标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艺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均收入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他们发现,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7)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再如,他在评论张亮采于1911年发表的《中国风俗史》时,说它“是从旧风俗观到新风俗观的一只渡船,或者说是一曲前奏”(8)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125页。。这些都说明,钟敬文晚年的学术思想发展,特别是关于中国民俗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研究关系问题的论述,始终没有离开他对古今中外文明关系史的认知框架及自己的存在感。
钟敬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注意和讨论中国人如何在中西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能够保持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也是当今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态度问题。如他在1983年就指出:
在学术上,不同国家的学术界对某种共同的人文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会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各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现实,各有自己的历史经历(包括那种被研究的人文现象的历史),加上各自研究目的和方法等的差异,因此,那种研究的结果,必然要呈现出或大或小的特色。这种特色有显著与否的差别,更有自觉与否的差别。(9)钟敬文:《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他在1991年说:“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世界的,而同时也应该是民族的。它应该有民族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一点,即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富裕,尽管外表上非常之光华、灿烂,但实际上是一个稻草人,没有灵魂,没有主心骨!”(10)钟敬文:《民族民间传统文艺的巨大作用》,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在1994年还说:“如果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11)钟敬文:《传统文化随想》,钟敬文著,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这种对于中西文明之间接触、交汇情势的认知,对于文化主体性及认同问题的关注,都是他在文明视野下看问题的明显表现。
最近一些年,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那场“文化热”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文明论”的阐释视野,如贺桂梅认为“‘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形态之一种,具备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内涵,成为当代知识界阐释中国的一种主要方式。在这种阐释视野中,中国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体’的当代延续,其国家形态是区别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独特政治体,而其文化认同则需要重新深植于古代传统的现代延长线上”(12)贺桂梅:《“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与此相关,王铭铭在近年提出和建构“超社会体系”理论的过程中,对于“文明”“民族”“社会”等含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参见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王铭铭:《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由此来审视钟敬文,他固然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文明体”概念来替代西方式“民族-国家”概念,但这并未妨碍他拥有上述的“文明论”视野,这就是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的连延演进与现代化的文明进程视为既发生交汇又并行不悖的关系,同时也认为“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13)参见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页。他就是在这种多主体文明历史关系的视野下,提出了“民俗文化学”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
反过来说,他以自己的具有民俗学专业特点的理论,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文明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他的这种理论贡献具有长远意义,应得到包括民俗学在内的学术界的重视、继承和发扬。然而坦白地说,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不妨借用一下甘阳的说法:“回顾八十年代,不是要怀旧,而是要通过八十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我们那时称为‘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人必须拉长历史的视野,反复思考这个大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生存论境遇。”(14)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2页。
二、文明主体观与传统文化整体论
只有理解钟敬文的文明视野及其个性表现,才能全面认知他民俗学思想的时代性贡献,特别是他的传统文化整体论和进行传统文化整体研究的主张。从广泛的影响作用来说,这种思想主张对于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加强文明间对话等学术和文化事业,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从影响民俗学今后发展方向的角度来说,由于提出民俗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结合为整体,并以此作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基础,因而就提供了一种主体性特色非常鲜明的学科方法论。
传统文化整体论的合理性,根之于传统文化内部形成的分化和互动关系的结构及其整体变迁的历史,也根之于各个文明或民族之间传统文化整体间的差异、接触、交流的过程。但是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在人们的文明主体意识得以增强的条件下,传统文化整体论才会在文化和学术话语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发生比较大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影响在整个20世纪特别表现在大批文化人士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发现和研究之上。如晚清和民国时期所发生的“眼光向下”或“走向民间”的歌谣学、民俗学等学术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兴起的关于新文化“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的讨论;1942年,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宗旨和文化大众化目标的确立。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每一次民族文化整体论的兴起,均以发现民间文化为主要的价值导向。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中,情况却有些特殊,民族文化整体论的声音,特别是关于民间文化的声音,除与“寻根文学”相关的评论外,显得相对微弱。我认为这与中国文化、学术界多年处于半封闭状态,突然开始接触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局面相关。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明主体意识的增强。与此相关的情况就是,关于民间文化的讨论,多局限在刚刚恢复起来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以及关注民间社会和文化的其他一些学科所组成的比较小的学术圈子里。而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文化整体论却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宣传。
值得庆幸的是,在那场“文化热”过了几年之后,钟敬文以他参与讨论的经验积累和长期的学术思考,不同一般地提出了以“民俗文化学”为标志的民族文化整体论思想,接着又在此基础上发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我认为,他的这些学术思想,特别反映出了在20世纪的中国,民俗学力图与传统文化研究结成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建构等发生作用的理想,也代表了民俗学未来发展的理想。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民俗学在世纪初的“初步崛起”和在世纪末尾的“再次勃兴”,“都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产生的”。(15)杨利慧:《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复兴的社会背景》,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本人曾撰文对钟敬文“民俗文化学”从酝酿到提出的思想过程作出分析(16)参见刘铁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及方法论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认为他之所以主张建立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的新学科,目的是解决当时两个领域的学术本该结合却严重脱节的问题。这两个领域就是中国的民俗学和上层的传统文化研究。拙文认为钟敬文的批评意见,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过于偏重上层文化和忽视中下层文化的情况,或者说是面对比较广泛的学界人士而说出的,但是对于民俗学界而言,这些批评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完整的历史与当代发展进程的认知,需要将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民俗文化学”概念,就揭示出这种方法论的根本内涵。
钟敬文最先是在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提出“民俗文化学”的。这篇论文,进一步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对待传统文化里的中、下层文化的共同态度和活动,并以“民俗文化学”这个草创的名词来给予概括。
关于民俗文化学兴起的主观动机,他说:
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代西洋文化洗礼的;同时他们又是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这主要是从民主主义角度观察的结果,同时还有西洋近代学术理论的借鉴作用)。(17)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钟敬文著,连树声编:《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钟敬文对于民俗文化学在四个方面开拓和取得的成就,作出了精要的评述。这四个方面就是:白话升格及方言调查,口承文艺的发掘,通俗文学登上文坛,风俗习尚的勘测探索。所有的评述都是为了考察这些学术活动和成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从传统文化再造的角度论证了民俗文化在传统文化整体中的重要位置。
仅以他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分析为例。他指出,能否利用从元、明、清各朝代延续下来的各种通俗文艺所使用的“白话”传统,并提升它的地位,是白话文运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他说:
……从文化心理上看,这种广泛存在的活文化(普通话)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阶级)眼中是鄙俗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尽管如此,但是要救亡求存,这是一个关口,非闯过去不可!(18)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第93页。汪晖在关于白话文运动价值取向上的一段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钟敬文考察“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提供一种参考:“由于不存在用‘民族语言’(‘民间语言’)取代帝国语言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在本土语言/帝国语言的对峙关系中提出问题,而是在贫民/贵族、俗/雅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与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实际上现代语言运动首先是在古/今、雅/俗对比的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书面语与方言的关系中形成的,即白话被表述为‘今语’,而文言则被表述为‘古语’,今尚‘俗’,古尚‘雅’,因此,古今对立也显现出文化价值上的贵族与平民的不同取向。”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445页。
他认为在这方面终于达到的成功“……是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的一大步,是当时学术界致力于民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它的一个基本方面”(19)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95-96页。。可以体会到,钟敬文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历史意义的评价,包含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结构中矛盾问题的关切,也包含了他对民俗文化学研究可以积极影响传统文化再造进程的自信。
在发表《“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三年之后,钟敬文又发表了《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正式提出建构一个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的新学科,说明和论证了建立这个学科的思想由来、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特点、民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位置、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体系结构、社会效用、方法论等问题。(20)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但是,对于后学来说,有必要阅读他在1986年以来发表的其他论文和随笔,才好体会他说的“把民俗当作文化现象”来研究的深意和心路历程。
三、文明体与学派
钟敬文的“民俗文化学”,就是在多主体文明历史的视野下,也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各种共同体社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自身传统文化内部多元、多层、多形态等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下,所作出的关于发展中国民俗学的论述。他所论述的这些问题,也在他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论述话语中有一定表达。因此,这里就出现了“文明体”与“学派”是何种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将“中国民俗学派”解释为研究“中国”名义之下文明体的民俗传统文化,而且是具有这一文明主体特色的民俗学派。各个文明体都可以建立自觉的民俗学派,各个学派不仅是对文明体自身,而且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平等交流,对所有人类的文明体都作出应有的贡献。
钟敬文在与“民俗文化学”相关的论述中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学理性意见,大多都与他的文明主体意识和学派意识密切相关。这里仅作出一些概括,并加以一定的阐发。
第一,传统文化是具有上、中、下三层结构的整体,所以研究者不能把中、下层的民俗文化放在考察的视野之外。否则,“那不但将使所得结果是残缺不全的,甚至于它是否能真正探得‘骊珠’——取得要领,也是可怀疑的”(21)钟敬文:《传统文化随想》,钟敬文著,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这是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根本原则,也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传统文化研究之所以不能缺乏对民俗文化的关注,除立场、观念、知识的差异外,还要特别看到,是由民俗文化的生活实践属性、身体经验性质、情感认同功能等决定的。
第二,民俗文化研究必须把握民俗与生活中个人、群体同在的特质。“像鱼儿生活在水里一样,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泡在广泛的各类民俗文化之中。”“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连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裔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22)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钟敬文著,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第三,应该从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关联来研究传统文化,“在同一个民族里,这种分离着、差异着,乃至于对抗着的两种文化,却又互相联系着、纠结着、渗透着,形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23)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钟敬文著,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这种关联,在地方传统文化的文献传承与生活传承(24)本人提出,这个“生活传承”的概念,大于“口头传承”的概念,也比“口头传承”更为完整地接近民俗的本质,其内涵是:特定民俗传统总是生成和传承于特定地域社会或其他共同体生活之中。民俗的生活传承方式,与以文献为代表的其他媒介的传承方式明显不同。后者是把从特定生活中获得的印象、记忆、叙事、物品等文化材料抽离出来,重新组织而保存于文字、文物、图画、音像制品等系统中,从而置于超时空的传播过程。钟敬文指出文化的上、中、下结构,主要说的是文化在社会阶层及其观念形态上的关系结构。但是这种关系结构也存在于生活传承与文献传承的分离与关联上。同时还要看到,文献传承系统,虽然可以脱离但也往往被纳入特定共同体的生活传承系统。反之,生活传承系统被包含于文献传承系统,则是不可理喻的。这就是民俗学为什么必须进入实地的民众生活当中,而不能仅凭文献等资料做研究的根本理据。的不同表现和互相作用上表现得非常具体。
第四,民俗文化研究具有的“现在学”性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可以参与各个地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参与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转化、发展的进程。经验说明,民俗志的调查与书写,是促进各个地域、各个主体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学术工具和媒介。因此,我们都可以像钟敬文一样说,“我深切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关系的东西”(25)钟敬文:“自序”,钟敬文著,连树声编:《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自序”第19页。。
第五,民俗文化研究应具有与自身传统文化一致的主体性特色。“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26)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页。,因而也才能够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和国民进行真诚的交流。
钟敬文的这些学理思考和学术理想,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持续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