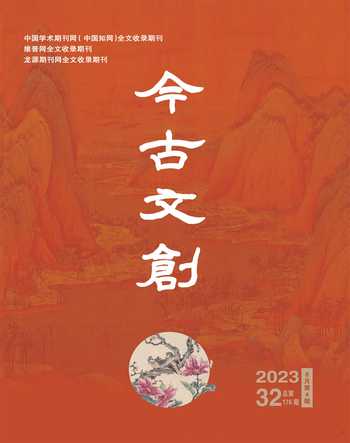疾病隐喻与道德选择 : 对苏珊 ·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人文思考
陆欣立 朱梦丹 归淑婷
【摘要】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文集《疾病的隐喻》以结核病、癌症等疾病作为重点叙事对象,探讨社会演绎变位下疾病隐喻的独特表达以及所引发的道德缺位问题。桑塔格将个人的症候与社会的道德环境交织结合,映射出疾病对人类道德身份与伦理价值的潜在影响。本文拟从疾病本身出发,通过对疾病的隐喻表征、疾病重压下的道德审判与认知升华以及患者的身份嬗变与道德选择,分析作品的道德意图与所指,希冀由疾病剥离出隐喻影子,以此发出疾病外衣下对身体解放的号呼。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道德;结核病;癌症;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4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桑塔格的疾病书写与后疫情时代个体疾病困境的隐喻”(编号:202210332036Z)结项成果。
身处后疫情时代,人类因为这种具有强大传染性的疾病遭遇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罹患疾病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个体社会道德与伦理身份的困境。谈及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一词,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独特的视角,结合自己的经历揭示了疾病对个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她缠绵病榻,病痛蜿蜒全身,卻叫她以愈发沉着、愈发冷静的眼光与笔触洞察造成疾病的社会现实。她在作品中剖析了疾病隐喻的类型,展露人性的善与恶、洁与不洁,传递给读者以独特且奇妙的阅读体验。对苦难的认识、对生命的谛视、对顽疾的反抗,造就了桑塔格清醒又尖锐的文学王国。
21世纪对桑塔格疾病叙事的相关研究日益崛起,近年来不乏高质量的成果。尤其是在经历大规模世界性流行病后,更是达到新的研究热潮,相关成果正在大量涌现中。Barbara Clow通过解释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两个假设悖论,在“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1]中展现隐喻语言在现代“前科学”中以及因果关系的论证中发挥的作用,努力解决现当代医学诊断和治疗中的因果关系的逻辑问题;Yianna Liatsos则是在“Temporality and the Carer's Experience in the Narrative Ecology of Illness: Susan Sontag's Dying in Photography and Prose”[2]中探究了无法治愈的癌症诊断所产生的时间失调如何阻碍人格和伦理意图。国内学者张艺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疾病叙事学转向——以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为例》[3]中嵌入大生命视域文化,为文学的研究范式创新提供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激发叙事转向上的后现代生命意识,拓宽大生命视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向;柯英的《〈费城故事〉和〈最爱〉中的疾病隐喻机制》[4]选择将两部展现疾病的电影作品与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展开互文性解读,以影视化表达理解疾病的隐喻机制,批判身体成为各种隐喻的载体,我们应当取缔疾病和健康的二元对立。鉴于此,本文将试从疾病隐喻的道德意义进行切入,以挖掘桑塔格文字中所表达的疾病的内核意义,进而探索社会“诊断报告”。
一、疾病的隐喻表征与错位转向
桑塔格明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隐喻”即“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说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5]。人类利用隐喻这一修辞手段,赋予了“疾病”更多内涵,将其所带来的影响从患者个体转向宏观世界的道德选择、政治立场甚至是某种意识形态[6]。疾病的隐喻正一点点地在人们的无限臆想与口口相传中最终成形,而被隐喻化的疾病,则成了人类想象中的影子和产物。
《疾病的隐喻》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处于美国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的碰撞时期。苏珊·桑塔格在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坚定地选择了对“疾病隐喻”的探究。与癌症多年的对抗和治疗之中,她不得不强忍癌症本身给她身心带来的强大痛苦,更需要承受由癌症隐喻化带来的具有耻辱性的道德审判。作为患者本身,后一种痛苦远比前者更为痛苦与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形式瓦解患者的心性,继而一步步走向投降、妥协。
论《疾病的隐喻》写作目的,诚然会提到去疾病的污名化与隐喻化,脱去疾病所蕴含的任何道德意义。桑塔格认为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最诚实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5]。把疾病与隐喻二者明确分开,势必是对人的解放,同时也可带来抚慰。那么,如若要摆脱所谓的隐喻,首先不可回避。它们务必暴露在阳光底下进行解构。
疾病一旦成为阶级地位的象征,便不由会被纳入种族或政治的讨论范围。如果说政治事件中沾染了疾病隐喻的色彩,深不可测的邪恶便会浮现出水面。马基雅弗利把结核病看成是早发现早治愈的疾病,改种疾病是人为可以控制其进程的;类比政治,暴乱亦是如此。
桑塔格从自身出发,借由自己对疾病本身的看法以及付诸疾病之上的隐喻的意义,掀开了当下社会文化中内含的巨大遮羞布:工业社会中节制消费的困难。通过隐喻义,桑塔格实现了对作品内核的多样化表达,对当时社会中沦陷败坏的风气与混乱的伦理秩序发出了猛烈批判。
二、疾病重压下的道德审判与认知升华
疾病本是在一定的病因作用下,人的一种异常状态,一种正常形态与功能的偏离。隐喻将疾病从仅仅是身体的非正常,转换成一种嵌套着一定“意义”的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继而走向疾病的隐喻。隐喻套在人身上的枷锁比疾病本身更加致命,且这种枷锁是隐形的,很难同疾病一样被疗愈。疾病与道德高尚和政治倾向不成关系,然而疾病的隐喻脱离原始的审美领域,跻身道德范畴,进入政治种族圈层,演绎成排斥异己的修辞武器,以掩盖真相。[7]桑塔格呼吁消除疾病隐喻,将疾病回到疾病本身。
桑塔格在文中提到了结核病、癌症、梅毒和艾滋病,这四种疾病都是或者曾是人们恐惧、避之不及的疾病,对人类影响极大。桑塔格认为结核病在一开始指向的是折磨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5]但在19世纪中叶开始,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结核病因此被浪漫地看待,甚至将它当作一种“贵族病”,[5]来提升自我形象。最常见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将结核病带来的身体苍白和潮红、情绪的高涨多加描写,患者大多生活奢华,患病反而使他们更加优雅,带来的死亡甚至是极乐般的,崇高又平静。而癌症恰恰相反,代表畸形和压抑,身体内的异变和痛苦以及治疗中切除身体某个部分让人们对待癌症有一种非理性的厌恶,很多人坚持格罗德克划定的等式:癌症=死亡[5]。围绕结核病和癌症的幻想是夹在自我审判和自我背叛之间的一种形式。梅毒患者,隐喻义被认作是一种上天的惩罚,将梅毒患者集体曲解为是遭到了不正当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批判,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5]。艾滋病的情况更为特殊,因为其痛苦无法治愈,传播途径被人们曲解成了更多的耻辱,艾滋病逐渐在人们心中成了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的传染病。
疾病隐喻带来的道德批判的影响比疾病本身更具“传染力”。桑塔格指出隐喻带来了另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将疾病妖魔化,把错误归咎于患者,用无情的逻辑将其视为犯罪。[5]人们本能惧怕疾病,不免惧怕患病人群。人们惧怕未知,惧怕未被人类征服、具有未知灾难的疾病。这等的惧怕和曲解,在疾病的隐喻的帮助下愈发滋长。部分疾病被强行与片面的判断挂钩,这样的理解给疾病的隐喻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可的疾病道德批判。它無形渗透在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中,由个体的不幸演变为了社会性的恐惧、厌恶和划清界限。这种隐喻发自个体内心,又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反馈,使得它感染了全人类。因为未知和感染力,让人产生恐惧,从一种道德谴责的态度评论病人,将病人划分为了不属于群体的异类,更有甚者,将自己身上所发生、所经历的不幸归咎于病人群体。桑塔格在书中指出:“为了强化效果呼吁人们进行理性反应,疾病隐喻被运用到政治哲学里。”[5]在主流媒体关于流行病的报道中,将病毒本体隐喻为“恶魔”“死神”“自然现象”,将对待疾病的手段与治疗方式隐喻为“战争”“考试”“比赛”。媒体运用这些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词语来隐喻流行病,一定程度上引导提高人们对病毒的认知,即需要警惕病毒、关注病毒,要凝聚人心齐心协力对抗疾病产生的效应。另一程度上,人们的关注同时对病毒产生一定的恐惧,这种恐惧逐渐偏离正确的轨道,扩散为对其他方面的极端恐慌。甚至出于对疾病特性的无知,碎片化的信息和谣言将矛头直指所谓的源头传染者,并成了“公敌”和情绪宣泄口,对病患的隐私进行道德批判和伦理羞辱。一旦有足够的信息以及“理性人物”的诞生,公众的理性才得以回归。即使理性回归,但对于病毒的恐惧已经深入到观念之中,面对部分突发情况时,防治成了部分人无视和逃避的工具,死板的条例遮盖背后最根本的人性,从而将简单的疾病问题引向了人性道德审判。因而我们呼吁,让患病的身体回归身体本位,使疾病不再分裂和异化人心,使疾病不再与其阴暗的隐喻义画上等式,摆脱疾病的隐喻对人类理性思想的束缚,重审人与疾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让人们睁开被疾病污名化蒙蔽的双眼,从而重构万物与世界的客观联系,找回人类生命的根本意义,捍卫真相与道德的归位。
三、患者的身份嬗变与道德选择
世间每一个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存在于疾病王国[5],那么疾病可谓是唤醒了蛰居于健康人格之上的潜在伦理身份与伦理意识。愈是严重的疾病,愈是加速了患者被迫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归因于可怕的、未知的疾病唤起了人类内心深处那份古老又神秘的恐惧。死亡率极高、难以医治的疾病被当作是外来的“他者”,患者就如同是挣扎在蜘蛛网上的猎物,难以逃离,不得不服从、顺应、接受疾病世界新的规则与法度。这个外来的“他者”进驻病人的身体,占据健康王国的领地,污染一切器官与系统,随意地流动、回溯、扩散、颠覆。而这一整个过程,陌生而敌意的一切紧紧裹挟着患者的身体,将患者囚禁于疾病王国的迷宫之中,逼迫他们做出身份转变的选择。
诚然,人无往不在社会之中,但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实现依附于个体与社会的连结。疾病隐喻恰恰割裂了患者与外界的关系网络,疏远、抽身,直至难以逾越的鸿沟。借用恺博文的躯体化观念,“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8]。亲情关系的变异、友情爱情的离散、社会身份的嬗变,都迫使患者进入一种失根的漂泊流浪状态。
患者无法达成社会道德身份的认同,根本上是疾病、个人、社会这三者关系的失灵。疾病的隐喻在个体的生活圈与有限的社会网之间来回编织穿越,缠绕着集体想象力的被隐喻化的疾病[5],把难堪的死拉近到人们眼前无限放大,继而再推远。时代的外部动荡与变化,肉体的疾病与心灵的复杂创伤,一步步异化、裹挟着患者。社会成了疾病滋生的温床,高密度的人口、高强度的工作、高度工业化,种种疾病在顷刻之间迅速扩散。文学作品中的道德选择,则是无可救药的顽疾面前,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的来回拉扯,必须要对自己的境遇和他人的存在做出一个选择。推之于现实社会,肆虐的流感病毒,体外的东西占领了病患的身体,使得个体成了异己。囿于隔离的环境之中,人们的同理心与关怀感无法真正对病患做出共情,仅仅关心自己所生活的一方天地,听不见远方的声音,最终走向冷漠。道德给了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规则[9]。而用道德的枷锁隔绝被虚构化的疾病隐喻的病人,却是人性的淡漠与自私自利。而破除这般枷锁的最好方式,是打破疾病所缠绕的一切隐喻含义,直面患者,承认患者合理又正当的社会身份,归还他们应有的道德身份。
归根到底,最实际问题在于人类在真正面对重大疾病时,能够转变自我中心的旧观念,去疾病隐喻,使疾病回归本身吗?《疾病的隐喻》映射了三种时序:曾经经历、当下正在面对以及甚至将来无法幸免,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可能已经告诉我们了答案。
四、结语
《疾病的隐喻》以其独到的视角,围绕结核病、癌症等症候进行论述阐述,对变形的道德化的疾病进行思考与评判。桑塔格通过多种疾病隐喻描绘了伦理缺位下,道德崩塌的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矛盾,疾病不再留于疾病本身含义,而是加诸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疾病与疾病、疾病与患者、疾病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关系仍需新的思路、新的解读范式努力去打破旧有的对立,回归道德真善本位,实现肉体与灵魂双在场。
参考文献:
[1]Barbara Clow. 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J], 2001.
[2]Yianna Liatsos. Temporality and the Carer's Experience in the Narrative Ecology of Illness: Susan Sontag's Dying in Photography and Prose[J],2020.
[3]张艺.后经典叙事学的疾病叙事学转向——以苏珊·桑塔格疾病叙事研究为例[J].天津大学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24):21-28.
[4]柯英. 《费城故事》和《最爱》中的疾病隐喻机制[J].鄱阳湖学刊,2019,(6):73-82.
[5](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6]郝永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文化研究关键词[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47.
[7]霍源江.生病也任性:苏珊·桑塔格与疾病[J].世界文化,2016,(08):38-39.
[8](美)凯博文.痛苦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M].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9](美)罗伯特·所罗门(RobertC.Solomon)&凯思琳·希金斯(KathleenM.Higgins)著.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M].张卜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