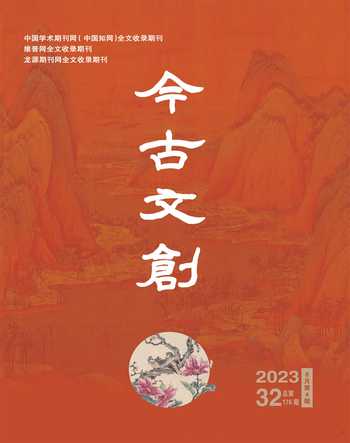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南京安魂曲》的创伤书写研究
王思宁 何晓彤 潘敏芳
【摘要】《南京安魂曲》讲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明妮·魏特琳作为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負责人,开设难民营,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本文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小说中的替代性创伤、民族创伤以及小说人物在抗战环境下为自我疗愈进行的创伤救赎,以此为读者了解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创伤性影响,呼吁人们反思历史,珍视和平。
【关键词】《南京安魂曲》;创伤理论;创伤复原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2-001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5
基金项目: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华裔美国小说中的抗战文学研究”(项目编号:xj202211845075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一般项目《二十一世纪亚裔美国小说中的战争书写研究》(项目编号:GD19CWW02)。
一、引言
美籍华人作家哈金是首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曾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海明威基金会/笔会奖等多项奖项。《南京安魂曲》是他从2007年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取材于大量真实历史事件,先后修改了32遍。书中的明妮·魏特琳在那个残酷、战火弥漫的时代,用自身的乐观、善良、正义帮助南京百姓度过南京大屠杀这段艰苦的岁月。
然而,魏特琳也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与磨难,这位怀着悲悯情怀孤身与各方斡旋的女性最终无力抵挡创伤和哀悼的心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南京安魂曲》中的创伤书写表达出作者哈金渴望通过自己笔下的故事来告诉世界这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唤醒人们对于战争的记忆,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直面历史创伤并实现真正的创伤救赎。
怀特海德认为,创伤小说通过文字唤起集体记忆,“历史通过记忆的修辞被改装,从前享受不到特权的声音被给予了述说的权力。”[1]94
书中的创伤书写及创伤复原的策略值得研究,而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大多从人道主义(孙柯,2018)、创伤叙事理论(林瑞韬,2020)、战争记忆(单德兴,2012)以及女性创伤(傅守祥、陈然然,2020)等角度出发,其中关于创伤理论的运用较少。
基于此,本文以小说《南京安魂曲》为研究对象,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小说中的替代性创伤、民族创伤以及创伤复原。
二、共情与自责:魏特琳的替代性创伤
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简称VT,这一概念是由McCann和Pearman提出的,最初是指专业心理治疗者,因长期接触患者,受到了咨访关系的互动影响,而出现了类似病症的现象,即治疗者本人的心理也受到了创伤。[2]
后来,其定义进一步扩展:由同理心引起的创伤体验,没有亲历创伤事件的人,通过听觉、视觉、触觉等途径得知相关讯息,间接暴露在创伤事件下,因为同理受害者而产生了类似的创伤反应。小说《南京安魂曲》中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校长明妮·魏特琳正是替代性创伤的典型受害者之一。
日军侵占南京后,魏特琳四次拒绝离开南京,她显然已经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即使是在面对更好的前途时,她仍然选择坚守南京,拼尽全力保护难民营的人。她勇敢抵抗凶残的日军,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保全南京数万女性,被誉为“金陵永生”,但这看似强大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疲惫不堪的心。魏特琳是一位美国传教士,自然不会像当时的普通南京百姓一样受日军欺凌,但她在同理心与责任心的驱使下,对受难者及其创伤共情,甚至产生自责、内疚心理。战争间接带给魏特琳女士的身心创伤与直接带给南京百姓的真实创伤一样沉重。
当她与助手高安玲来到火车站候车室看到三百多名伤兵时,她们又震惊又难过。亲眼见到一具具饱受战争摧残的真实肉体,亲耳听到痛苦的哀嚎与咒骂,如此视觉冲击和听觉冲击,给这两位慈悲为怀的女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3]18
魏特琳作为难民营的负责人,少不了见到这些残忍血腥的场面,每一次她目击创伤性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时,她都在切身体会受害者所处的悲惨情境,共情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
有学者在对替代性创伤进行研究综述时提道:“替代性创伤带给人们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让救助者重复体验了受灾人员的创伤经历,使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多改变,恐惧、无助、内疚、自责等负面情绪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2]91-93本顺报信途中失踪,日军在金陵学院强抢妇女,被日本人侮辱的女孩疯癫、自杀、被送去做人体实验,家庭手工艺学校的穷人被丹尼森夫人赶走……魏特琳把这一切都归咎为自己的过错,一直为此自责,她的内心“被悔恨和痛苦啃啮”。[3]101
面对日益猖狂的日军,魏特琳为顾全大局,保护更多的妇女不受侵害,无奈之下同意日军带走自愿牺牲自己的女性。事后,她陷入无尽的自责与痛苦,拼尽全力做一些事情来弥补,但舆论与责骂仍像龙卷风般席卷而来。
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真正的罪犯》,给魏特琳冠上了“人贩子”的外号。魏特琳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身心困扰,她认为自己“对金陵学院面临的所有问题,对难民妇女和姑娘们所遭受的全部苦难,都负有责任”[3]289。
美国精神病学家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写道:“当创伤患者曾目睹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4]50-51魏特琳多次目睹南京女性遭受残暴的对待,想救助却无能为力,陷入不停的自责中,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内疚感。
拉卡普拉提到创伤是通过重复而延迟产生的,创伤事件在其发生时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只有在一定時间间隔或潜伏期之后才能被感知,而此刻创伤事件又是被压抑的、分离的或是被否定的。[5]174
在南京时,魏特琳因为对受难群众共情,不停地在产生自责、内疚感,此时还没人意识到魏特琳受到的创伤。但这长期的劳累、丹尼森夫人的施压以及舆论的一边倒,令魏特琳感到身心俱疲,最终她扛不住了,开始精神恍惚,后来病症变得愈发严重,只好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
在小说的尾声中,爱丽丝寄来的信件告知了魏特琳的一系列创伤症状,这时魏特琳的创伤症状才开始被身边的人所感知。魏特琳“一开口就是责备自己,说她已经变成我和大家的负担了”。[3]292
露丝·雷斯(Ruth Leys)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特征症状——闪回、噩梦和其他再次经历、情绪麻木、抑郁、内疚、自主觉醒、爆发性暴力和高度警觉倾向——都被认为是这种基本精神分裂的结果。”[6]魏特琳开始有自杀倾向,被诊断为抑郁症,有时“情绪很恶劣,还指责我抛弃了她”[3]295,这些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
书中通过他人撰写的病情报告客观地展现出魏特琳的替代性创伤症状,像魏特琳女士这样一位善良勇敢的女性,在目睹了大量的罪恶与苦难后,也逃不过战争伤害的魔爪,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痛苦的生活,无形之中成为了战争暴行的受害者。
同伟大的魏特琳女士一样,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也是一位共情能力强的替代性创伤患者。在看到记录日军暴行的《魏特琳日记》以及相关的图片资料和纪录片时,她义愤填膺地写下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用文字重现那些血腥的场面。但遗憾的是,过度共情与负面情绪使她精神崩溃,在2004年以开枪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见,替代性创伤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亲历者的创伤。
三、动荡与屈辱:民族的创伤
《南京安魂曲》以高安玲的视角对当时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伤害进行尽可能客观地描写,着墨于残酷战争中底层人民的苦难,书写出这一沉痛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民族创伤。作者哈金评价《南京安魂曲》:“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与耻辱。”[7]这场战争不仅对个人和群体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更是对个人和群体所存在的民族和国家造成巨大的创伤。
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动荡中,以及这整个民族的灵魂长期处于屈辱苦痛和动荡中,民族创伤就会随之而来。在《南京安魂曲》中,日军的入侵使得南京社会秩序混乱,群众陷入长期的兵荒马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军队抓走了许多家庭的男人,难民中的很多妇女惦记自己的男人,来恳求魏特琳从日军手里把男人要回来。
作者通过书中的描述让读者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两个家庭的遭遇,而是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群体的遭遇。进而可以认识到,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所作所为在伤害无辜民众的同时,也在千百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刻下了沉重的创伤。
《南京安魂曲》中描写的日军暴行所带来的民族创伤,不仅仅是失去家园、死伤无数,更是民族尊严遭到践踏。在众多种形式中,对于生命的漠视是最大的践踏。生命健康权是作为人最基础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而一个民族的构成和根基在于组成这个民族的千千万万民众,对于所组成民族群体的民众生命的践踏,是给予这个民族的巨大创伤。小说描写了在当时兵戈扰攘的年代中,日本军队在城中大肆屠杀,烧杀劫掠,更有毫无顾忌地往街道上投掷炮弹,视人命如草菅。上至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被刺倒在血泊中;下至垂髫小儿,甚至尚在啼哭的婴孩,皆成为当时日本军队的刀下亡魂。
妇女被看作民族精神与灵魂的象征,女性形象通常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民族归属感,如“母校”“母亲河”“祖国母亲”等概念。而书中多处描述日军对妇女的轻贱与肆意凌辱,彻底轻视女性地位以及权利。正如严歌苓所说:“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8]157日本军人的强暴行径是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些性暴力行为所涉及的男性施暴者与女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性别政治意义上的,还是民族(种族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义上的。”[9]日本兵蹂躏南京女性身体时,隐喻着日军侵占南京。一位女性可能是一个母亲、妻子或是女儿的形象,当她遭到异族男性的性侵犯,受伤害的不仅是这位女性,还有她背后的男人以及所在的民族。虽然中国在领土以及人数上都胜过日本,但日军仍大摇大摆地入侵南京,暗含着民族尊严遭到践踏的耻辱感。
如果说在肉体上蹂躏女性是对她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侵犯,那么击垮青少年的意志就是对其民族意志的彻底摧毁,掐灭了民族得以延续的希望。
小说开篇,描述了日军四处屠杀平民的场景,他们杀人仿佛捏死一只蚂蚁般轻松。目睹这一场景的本顺,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小说中被日军俘虏的男性大多是本顺这个年龄,都刚刚脱离少年的稚气,却突然遭此横祸,产生巨大的心理创伤。当本顺在回忆起这些创伤场景时,“可怜地抽泣起来,两条瘦胳膊控制不住地打颤。有时候他会自己发起抖来,仿佛有人要来打他。”[3]91
虽然最后他平安回来,但整个人精神恍惚,沉浸在恐惧与抑郁中。书中写到一些青壮年和青少年被日军抓进模范监狱里没日没夜地做苦力,素芬的儿子便是其中一个。在魏特琳的努力下,他终于被放出来,但他却“瘦得皮包骨”“惊魂未定,自己说不出个整句子”[3]144。身体上的创伤或许很快就能复原,但侵华战争给这些青少年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可能需要用整整一生去疗愈。陶家俊认为,创伤“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10]侵华日军抓走这些瘦弱的青少年,并不单单只是因为缺乏劳动力,更是想“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3]75。
民族尊严关乎到每一位民众的尊严和权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而同样地,当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之时,民族尊严何在?哈金选择在南京大屠杀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书写出战争记忆与民族创伤,呼吁中华民族直面历史、敢于疗伤,更是呼吁世界人民不忘历史,珍视和平。正是在具体现实的民族创伤中,在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和出发的过程中,逐渐凝练了构成民族内核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个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也正是在这些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解构和精神内核的凝聚过程中,深植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的含义。
四、直面与重建:创伤的复原
在小说的后部分,魏特琳和高安玲在水塘边记录下河边的尸体数时有过一段对话。
“这里应该立一个纪念碑。”明妮说。
“如今到处都是杀人刑场。相比之下这里算不了什么。”我答道。
“不管怎么样,这里应该被记住。”
“人们通常都是很健忘的。我想那是生存下去的办法吧。”
我俩陷入沉默。然后她又说:“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
这段对话中魏特琳对于战争历史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记忆的遗忘而愤慨,诚然,遗忘可以让自我暂时逃脱创伤带来的伤害,但对于创伤记忆的遗忘,不过是在逃避所有从创伤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正如魏特琳所讲历史应当被如实记录,师彦灵指出:“批评追忆可以作为了解过去,从过去学习的方式,作为自我复原和共同体建构的催化剂,也可以作为反抗历史的记录。”[11]对于创伤的复原最重要的是不再抵触创伤记忆的闪现和重复,从而直面创伤记忆,直面创伤给自身带来的伤害,才能真正的复原和治愈创伤。
以小说中的美燕为例,美燕及其他十一个女生被日本兵从金陵学院抓走后,第二天又被放回来。后来美燕的父亲大刘的一系列反常表现,以及美燕站在学院门口,衣服下藏着一把剪刀,都暗示着日本兵对美燕这些女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为了不再回忆起那些耻辱与恐惧,受难女性集体选择对自己的创伤避而不谈,只是在心里暗自神伤,这体现了受创者的逃避态度,并不利于创伤修复和重构自我主体。
而后来,美燕带领女学生们高唱爱国歌曲,激起了金陵学院所有人的爱国热情,也得到了丹尼森夫人的赞扬。著名的创伤理论家拉卡普拉曾说:“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5]
美燕从对创伤事件避而不谈,到勇敢发声,通过高唱爱国歌曲表达对日本兵的痛恨与对尊严的捍卫。这些创伤患者通过歌唱叙述创伤、直面创伤、复原创伤,他们不再是逃避现实、隐忍失语的受难者,而是敢于反抗, 迎难而上的勇士。
小说中的美燕、本顺和路海都曾遭到过日本兵的羞辱,深受战争创伤打击,他们都是有着相似创伤经历的创伤受害者,而在小说中写到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目标,最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参军的方式进行创伤疗愈。
但对创伤经历的直面和述说只是开启创伤疗愈的第一步,卢珊认为“意识的主动参与不仅让被压抑的创伤记忆依照其自身的状态自行呈现,也让作为叙事的想象突破了自身的桎梏进入到創伤疗愈的层面”。[12]
美燕、本顺和路海在给魏特琳的信中写道:“要是国家亡了,我们的小家也不会安宁,我们个人的成功也毫无意义……总有一天,我会像一个战士、一个英雄那样凯旋。”[3]270
他们在信中展开了美好的对于未来的叙事想象,让他们的主观意识参与进创伤的疗愈过程中,也让他们踏出了重新整合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步。所以后来他们离开南京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加入抗日队伍,与外部外界建立了联系,帮助他们重新整合了对于创伤的记忆,在战争中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突破创伤曾经带来的自我桎梏,投入战场,在为国家而战斗寻求自我的心灵疗愈的同时,也给自己树立了安全感和信心。即使他们最后的结局并不幸运,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但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祖国,直面创伤,实现了自我救赎。
五、结语
《南京安魂曲》中,大量关于日军残暴的行为描写、民众对日军恨之入骨的心理描写,直面地展现了日本的罪恶行径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屈辱历史。余华评价这本书“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相和复杂人性”[3]3。
书中关于魏特琳过度共情的替代性创伤与战争造成的民族创伤,都在提醒读者战争与暴力所带来的创伤影响深远,给创伤者所带来的冲击强烈而深刻;给救助者带来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持久性;给一个国家与民族所带来的创伤甚至延续多个年代,并具有群体性。然而,这一系列创伤并没有阻碍创伤者寻求创伤救赎的脚步,哈金用冷静而细腻的语言,书写出战争受害者在面对恶魔与苦难时直面创伤与不懈努力,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作者通过纸笔为祖国与同胞发声,呼吁创伤者在唾弃轻视生命的行为,惩罚战争发起者之时,亦应吸取创伤所带来的教训,一遍遍地反思历史,从分析和总结中,从渐入正轨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得到恢复创伤的力量和勇气,建立安全感,重构对自我身份和集体身份的认同感。而施加创伤者也应在相关纪念活动中设身处地地感知创伤所带来的苦痛,反思自身行为,警醒自身以及后人,更加清楚道德责任,使社会发展更加良好。
参考文献:
[1]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M].李敏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2]马君英.替代性创伤研究述评[J].医学与社会,2010, (4).
[3]哈金.南京安魂曲[M].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4]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LaCapra,D.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Theory,Trauma[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6]Leys,Ruth.Trauma:A Genea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7]哈金.从民族经验到国际经验——专访美国国家奖得主哈金[J].南风窗,2011,(19):91
[8]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9]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J].读书,1999,(03): 17-24.
[10]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11]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32-138.
[12]卢姗.面向创伤的叙事与疗愈——关于《追寻卡西亚托》中的积极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20,(1):13-19.
作者简介:
王思宁,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何晓彤,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潘敏芳,通讯作者,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亚裔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