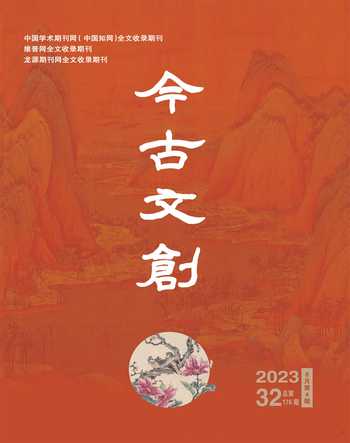浅析矛盾中蕴含的新力量
高雪敏
【摘要】被压抑的深层历史矛盾是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基本内涵。本文认为,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也隐含着作者的政治无意识,它体现了人类历史上必然存在的剥削与压迫境况。本文通过分析《土生子》中黑人的生存困境,阐释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深层矛盾,进而揭示出解决矛盾的集体欲望,将黑人群体与共产主义者联合,衍生新的力量。赖特审视奴隶制废除后的黑人困境,挖掘种族和阶级问题下的新力量,影响了社会群体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
【关键词】《土生子》;政治无意识;新生力量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2
理查德·赖特作为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中“抗议小说”的创始人之一,在黑人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土生子》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土生子》自1940年发表以来,广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国内外学者对赖特本人的思想也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少有学者从政治无意识角度探讨他的政治倾向和共产主义思想。本文以詹姆逊的三重视域政治阐释为框架,将政治无意识的关键概念与文本相结合,探析奴隶制废除后的黑人困境,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存的“恐惧”意识形态素等等,进而呈现困境中蕴含的新生力量和新意识模式及改变了的社会实践。
一、黑人困境:社會矛盾的象征性解决
《土生子》讲述的故事以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为背景。在这一时间段生活的北方黑人,多受到吉姆·克劳法的影响。吉姆·克劳法是内战结束以后,南部保守势力为了挤压黑人生存空间,实施种族隔离,而通过的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的影响逐渐在全国蔓延。在此背景下,北部大城市的黑人多聚集在贫民区内,且多数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住宅隔离和职业隔离问题尤为突出。这些历史现实都通过文本的形式走向大众。但具体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联系也不是直接相对应的,现实矛盾是以“潜文本”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因此本节首先需要通过文本中隐藏的线索将现实境况再次建构出来。再者,提及文本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叙事,借助作品的空间叙事方法,可以将文本背后的“潜文本”,即现实矛盾描绘出来,然后再分析作者对于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是怎样通过作品将其进行想象性或者象征性解决的。
在《土生子》这部作品中,人物存在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如别格租住的单间小公寓和道尔顿先生的住宅区之间。这些具体的建筑物空间可以抽象为一对对立的空间概念,即黑人区和白人区。学者加布里尔·佐伦也曾对叙事中空间再现的“地志的空间”如此解释道:“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它可以是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也可以是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间。”[1]58作品通过具体空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将对立概念中的黑白区建构了出来,以此映射住宅隔离问题和黑白群体间的生活差异问题。如主人公别格首次出现时就“站在两张铁床中间的狭长地带”[2]3,并且房间里还能听到黑色大老鼠的行动——“房间里薄薄的灰泥墙根响起一阵轻微的声音”[2]4。之后别格只能“把死老鼠包在一张报纸里,走下楼梯,把它扔进了胡同拐角处的垃圾箱”[2]8。这一系列的描写将别格居住的环境大致勾勒了出来。对比之下,白人住所就大不相同。别格初到道尔顿先生家时,就“站在一道防护宅子的黑色高铁栅栏外面”[2]49,进入宅子内部时,首先感觉到“脚下的地毯那么软、那么厚”[2]50,又看到“光滑的墙上挂着几幅画”,而后听到“从哪儿隐隐约约飘来钢琴奏出的乐声”[2]51。这两处住所环境的对比强烈反映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生活差异,这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建筑物分开,也将黑人和白人群体隔离开来。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确实存在,“20世纪初,大批美国黑人心怀所谓美国梦涌入芝加哥,为了解决住房紧张问题并彰显白人区别于黑人的优越性,白人人为地划分出‘黑人贫民窟”[3]134。通过实施住宅隔离政策,将黑人聚集在贫民区内。不只是住宅,职业也存在隔离现象。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被限制在不同的职业空间里,小说中别格的工作就是帮道尔顿先生一家开车,管理炉子、清扫炉灰等等,而道尔顿则经营着南区房地产公司。通过这些现象,将种族不平等问题勾勒出来。紧接着作者尝试解决问题,他先让黑人别格踏入白人区,再让其深入内部,将醉酒的白人玛丽抱回房间,打破黑人男子不能进入白人女性房间的禁忌。这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开端,但实际上,死亡才是矛盾的终结。别格为了自保将玛丽误杀了,自己也因此被判死刑。伴随矛盾主体的消亡,矛盾也终止了。玛丽和别格都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前者深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希望消除阶级差异和种族矛盾,而后者面对善意却不知所措。这两者的死亡是对现存的种族矛盾和政治策略的否定。也可以说,通过玛丽和别格的死亡,黑白之间的矛盾遭遇了象征性的死亡,种族歧视问题在这种文本形式中得到一种象征性的解决。但是,终极的社会矛盾总是不可能通过文本世界得以解决的,种族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黑人群体仍然存在困境之中。
二、现实焦虑:深层矛盾冲突的显现
奴隶制废除后,虽然黑人的境况有所改善,但黑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仍然面临被歧视的困境,他们对白人积压已久的恐惧也并未消除,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顺从态度。但是,也有一些受先进思想影响的黑人群体在此状况下,不断反思并努力改善不平等的民族境遇。在为民族努力争取的过程中,黑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苏醒。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仅为同样追求平等的黑人大众提供了一个机遇,更是唤醒了在阶级和种族矛盾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众多社会成员。在此背景下,白人统治者开始恐惧自身的统治会受到威胁。这些让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感到难以忍受,种族和阶级问题更加尖锐。因此在这一视域,作者想通过文本让大众看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深层矛盾,以及前者为了维持统治描绘的一个乌托邦理想。这一视域的关注点也因此“由个别的文本转向社会阶级、制度,文本也不再被理解为狭义的个别的文本或作品,而是集体和阶级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4]。
首先,“恐惧”表达的是一种群体(阶层)的情绪,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黑人别格、白人资产阶级者道尔顿、白人共产主义者简和麦克斯等人身上。别格对道尔顿或者白人的“恐惧”较为明显。别格第一次到道尔顿家,会很听话的回答“是的,先生(太太)”,心底的害怕使他小心翼翼。后来,此类恐惧甚至操控了他的行为,使他误杀了玛丽。从这些细节和行为可以看出,即使奴隶制已经被废除多年,这种对白人的恐惧依然残存在黑人群体身上。但道尔顿也恐惧别格,因为虽同为一家人,别格与母亲和妹妹的想法或者说与传统黑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别格的母亲和妹妹对白人的做法并不感到痛恨,她们的头脑中想的是听白人的话,白人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就去做什么,还要努力地认真地做”[5]。这是白人喜欢的样子。而别格没有工作,经常和朋友在街头鬼混,被指控盗窃汽车轮胎而送進教养所,还计划打劫白人的商铺。这些会让白人统治者感到困扰,但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却是玛丽的死。他们没想到黑人会这样残暴,并且公然地扰乱已建立好的社会秩序。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就这样在恐惧的状态下变得更加敌对,种族问题更加冲突。以道尔顿为例的白人不止害怕黑人别格,还担心简和麦克斯等“红色分子”。白人统治者对此潜在威胁不会坐视不理的,同时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他们想出了一个应对之策,即借助政治乌托邦力量来缓和此矛盾。具体如采用“遏制策略”,所谓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是指对压迫和剥削的历史现实的否认或者对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的逃避,体现在白人统治者身上就是对剥削历史的否认。具体体现在以帮助的名义,将服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到黑人头脑中。在文本中,道尔顿为别格提供了一份工作,帮助其缓解生活压力,道尔顿夫人也提议将其送去夜校学习。
此外,读者借佩吉之口还可以了解到道尔顿先生为整个黑人民族做的善事,“你要知道,他为你的民族做了不少工作……他已经向黑人学校捐赠了五百多万”[2]64。道尔顿夫妇的帮助都涉及教育,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被教授了适合其社会角色的意识形态”[6]168。学校通过教育向孩子们头脑中灌输的是被知识包裹着的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而统治者则通过教育为黑人描绘了一个平等互助的乌托邦理想。资产阶级统治者就这样利用不同的形式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实践。但是他们所描绘的乌托邦理想终究不会实现。划破这一幻象的是大众得知别格是杀人凶手时,报纸上刊登的“当局暗示奸淫罪”[2]273。没有证据,就评判别格的罪行是什么,这是在潜意识下做出的判断,体现了白人对黑人群体的偏见,统治阶级所塑造的黑白群体平等的假象就这样被戳破了。平等幻象的破灭,使得黑白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这无形中将黑人群体和共产主义者划到了同一立场,进而推到了同一战线。
三、新生力量:被压迫者的联合反抗
白人和黑人群体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一直在大众视野内的。但是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阶级问题也逐渐为群众所感知。在种族和阶级问题中,同为白人统治者压迫的黑人群体和共产主义者被推到了一起,他们的联合是困境中的一股新生力量。这些力量不仅散落在作品中,体现在简和麦克斯身上,还在作品所处的社会现实中不断生长,掀起了一个个的“文化革命”。所谓“文化革命”,詹姆逊认为通过这一进程,主体可以“获得新的习惯、新的意识模式并改变人类实践”[7]。文学可以帮助意识形态变形,可以推动现实社会中主体意识模式的改变。将《土生子》放到历史长河中来看,可以发现这部作品不仅将当时社会生各个产方式的文化主导观念的斗争与对抗都解读了出来,还塑造了一个新的意识模式,即借助作品中简和麦克斯的形象,为被压迫者提供一个新的选择联合被压迫者共同反抗。
首先,作品体现的两种对抗的文化观念可以从道尔顿、简和麦克斯身上看到。道尔顿为别格提供了一份工作,“工资规定每星期二十元,可我打算给你二十五元”[2]57,二十元用来补贴家用,多出的五元由别格自由支配,道尔顿看起来是一位友好慷慨的雇主,但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资本家,经营着南区房地产公司,也经管着别格的住所,别格“一星期付八块钱,只住一个老鼠成灾的房间”[2]197,即使如此道尔顿也不愿意减租。虽然“整个黑人地带到处有它的房产,连白人住区也有他的产业”。可是“别格却无法越界去住那边的楼”“尽管道尔顿先生捐助数百万元办黑人教育,他却只肯在这特定的区域租房给黑人住”[2]197。这些都暗含了白人资本家的文化观念,他们愿意帮助黑人,但帮助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是为了巩固已建成的并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对比之下,简和麦克斯则是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身上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特点。简第一次见到别格时就先伸出了友谊之手,“简笑容满面,摊开一只手向他伸过来。‘握住吧。简说”[2]76。之后还主动要求别格不要用“先生”这类敬语称呼他们。“首先,别管我叫先生。我叫你别格,你就叫我简。我们之间就这样相称。好不好?”[2]76这种像朋友一样直呼名字,无形之中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中无阶级区分,人人平等的观念。并且作为共产主义者,简也很尊重和信任黑人群体,“我们搞革命不能没有他们,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有气魄。他们能给党带来一些它所需要的东西”[2]88。不只是简,作为“党里最好的律师之一”的麦克斯,也在尽心地帮助黑人,亲自为黑人募集保释金。麦克斯也是别格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别格主动叫他给简带好,这暗含着别格在两种对抗的文化中,选择了后者,偏向新生的共产主义。主人公的选择,也是作者的选择。在工农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扩大的背景下,作者也在“1932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他自称党给了他无限温暖和精神力量”[2]2。作者用自身的行动影响着读者的选择。
作者及其作品可以凝聚现实中的力量,用其影响力推动社会发生文化变革,因为文学里的意识形态机制可以通过一种隐含的方式获得读者赞同,转变其思维。也可以说,通过敌对时刻下的“文化革命”这一进程,现实中的主体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模式,即与白人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压迫。其实,在这一视域,对作品进行阐释的活动本身已寓言化为一种革命的行为了,小说的历史意义也因此得以显现。
四、结语
至此,文章按照詹姆逊所勾画的阐释框架进行了三次阐释。首先探讨了文本背后的“政治潜文本”,勾勒出了现实中的矛盾,将问题进行了象征性解决。这些特定矛盾都掩藏在文本与叙事中的政治无意识里。然后,又将文本重建为不同种族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对话,将各种敌对阶级的声音围绕“恐惧”这个意识形态素展开,并通过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将黑人和无产阶级推到了同一战线。最后借“文化革命”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模式,将阐释活动寓言化为一种革命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文本还原到本来的面目。“历史在阐释循环中不断现身,乌托邦欲望也在阐释中从意识形态的遏制状态下释放出来,政治无意识也从寓言结构中得以恢复”[8]。
参考文献:
[1]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54-60.
[2]理查·赖特.土生子[M].施威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李美芹.论《土生子》的空间政治书写[J].外国文学,2018,(03):133-140.
[4]杨熙雯.詹姆逊阐释理论之初探[D].苏州大学, 2013.
[5]张晓敏.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思想内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6]孙路平.阿尔都塞的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读《土生子》[J].大学英语(学术版),2007,(01):168-170.
[7]陈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本阐释观及实践策略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2019.
[8]刘进.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概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