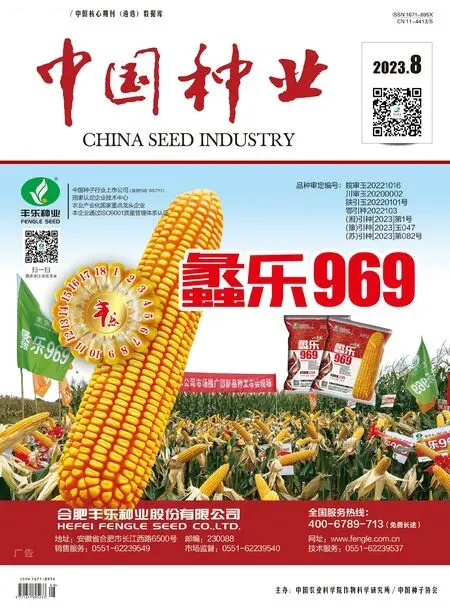中、美、欧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钟 辉 武雪梅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 10016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启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国内植物育种技术创新日益活跃、种业市场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完善育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保护水平,为种业科技创新提供知识产权强保护。
育种相关知识产权既包括专利等一般知识产权,也包括新品种权等独有知识产权[1]。其中,最重要的是3 种:对育种科研成果进行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权;对育种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保护的专利权;对育种过程中没有公开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资源、新杂交组合进行保护的商业秘密[2]。由于植物具有可繁殖等特性,通过商业秘密保护育种成果效果不佳[3]。因此本文探讨的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主要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
1 中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分离模式”
中国于1999 年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中第39 个成员。受国际公约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影响,当前我国植物品种及其育种方法保护的主要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对植物品种、非生物学育种方法分别以植物品种权和专利权进行保护。
1.1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也称育种者权利。中国于1997 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建立了植物新品种权。2021 年修订的《种子法》进一步提高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水平,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或者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并且除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外,在表达由原始品种基因型或者基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性状方面与原始品种相同[4]。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建立有助于防范商业装饰性育种的泛滥,推动原始育种创新。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是通过评审和验证的授权品种,对于新获得的植株个体或繁殖材料在审定授权前无法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有效保护。2021 年修订的《种子法》通过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对象,由授权的原始品种本身进一步向下游延伸至利用该原始品种进行简单育种获得的与原始品种虽有所不同、但高度相似的衍生品种,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但植物新品种权仍难以对上游育种材料、育种方法进行有效的保护。
1.2 中国育种专利权《专利法》排除了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专利审查指南2010(2019 年修订)》进一步解释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的植物的单个植株及其繁殖材料(如种子等)属于专利权排除的“植物品种”的范畴。因此,实践中排除专利权的“植物品种”的范畴比植物分类学意义上的植物品种更宽泛,目前中国植物育种技术的专利权主要涉及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方法,以及不属于繁殖材料的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
由此可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育种的育成成果,并通过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向下游延伸至实质性派生品种;育种专利权则仅能保护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方法和植物的非繁殖材料;二者之间既不相互重叠、也不相互衔接。在整个育种过程中,留下许多无法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真空,例如新获得的植株或繁殖材料[5]。因此,中国的植物新品种权和育种专利权可视为互不接触的“分离模式”。
2 美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复合模式”
美国为育种者提供了专利权和植物品种权的复合保护[6]。美国对植物品种可通过授予实用专利、植物专利、植物品种保护证书3 种方式进行多重复合保护。育种者可以根据3 种知识产权的特点从中自由选择一种或组合选择多种,以充分保护自己的育种智力成果。
2.1 美国植物育种实用专利权《美国法典第35编-专利》(35 USC,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35-patents)第101 条对可享专利的发明作出规定:凡是发明或发现任何新颖而有用的方法、机器、制造品、组合物或其任何新颖而有用的改进的人,可以获得专利,但须符合本篇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美国专利审查手册(MPEP,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明确了专利主题适格性的总体判断原则:(1)权利要求的主题必须是以下4 类:方法、机器、制造品、组合物。(2)权利要求不能涉及法定例外,除非权利要求还包括其他限定从而使其整体上明显超出了法定例外的范畴。法定例外是法院认为不属于上述4 类发明主题的类型,仅限于抽象观点、自然法则和自然现象(包括自然产物)。
由于美国专利制度对专利主题的适格性进行了宽泛的解释,因此,植物育种者可以对植物品种、植物器官(如花、果、芽等)、组织细胞以及上述产品的生产方法等申请实用专利权保护。实用专利权的客体对植物的种类、繁殖方式没有任何限制,可授权的客体不仅涵盖了广义的植物品种(包括植物植株、植物器官),而且还进一步延及由其直接获得的衍生物(F1杂交种、变体等),因而能够充分保护育种者的权益。
2.2 美国植物专利权除了实用专利之外,《美国专利法》第15 章还专门针对育种者规定了植物专利。植物专利的保护对象为无性方式繁殖取得的植物,但不包括使用块茎栽培的植物、野生植物、未栽培的植物,美国植物专利仅保护采用无性繁殖方式获得的植物后代。因此,植物专利的客体范围比较局限,主要适合于观赏植物、果树等少数植物种类的保护;实践中也仅能阻止他人采用无性繁殖方式复制受植物专利权保护的植物种类。
2.3 美国植物品种权美国1970 年颁布的《植物品种保护法》(PVPA,The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为有性繁殖植物、块茎繁殖的植物提供品种权保护,2018 年对PVPA 进行了修订,将无性繁殖品种纳入品种权保护的范围。美国植物品种权保护的客体包括有性繁殖、块茎繁殖或无性繁殖的植物种类,与仅适合保护无性繁殖植物种类的美国植物专利相比,美国植物品种权的客体范围更宽泛。美国植物品种权主要保护植物本身(延及F1种子),防止他人通过有性或无性繁殖复制授权植物品种,但不能保护除种子外的植物器官、植物来源的生化分子,也不能保护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因此其客体范围比实用专利更局限。
美国植物育种者可以根据其在植物育种过程中取得的关键智慧成果或智力贡献,确定最能体现其关键智慧成果或智力贡献的客体,进而从实用专利、植物专利、植物品种权中进行自由选择,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一项植物育种成果,3种知识产权之间并不互斥,育种者可以同时选择其中2 种或3 种,而不强制择一,因而重要的育种成果在美国经常可以获得多种知识产权的复合保护。
3 欧洲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模式”
1961 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等9 个国家正式签署UPOV,建立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制度,UPOV1961 规定成员可以选择育种者权或者专利制度进行保护。1963 年的《斯特拉斯堡专利公约》(Strasbourg convention)、1973 年的《欧洲专利公约》(EPC,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规定“成员国不应为植物或动物品种,或者实质上是生物学的生产植物或动物的方法提供专利保护”。欧盟采取的是强制选择型模式,即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为植物品种的发明与创新提供保护,发明专利制度为除植物品种之外的其他植物发明提供保护[7]。
3.1 欧洲植物育种专利权EPC 第53 条(b)规定:植物、动物品种,或者生产植物、动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不能被授予欧洲专利权。EPC 实施细则第26 条(4)将植物品种定义为:已知植物最低分类单元中的任何植物群体,不论是否完全符合植物品种权的条件,具有:(1)以一种给定的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表达的特征来确定;(2)至少表现出所述的一种特征,以区别于任何其他植物群;(3)作为一个分类单元,其适用性经过繁殖不发生变化。
EPC 对排除专利权的“动植物品种”做了严格限制。对于符合EPC 实施细则第26 条(4)定义的植物品种,无论是否有技术因素的介入,所述植物品种作为产品都属于EPC 第53 条(b)排除的范围;反之,对于不符合EPC 实施细则第26 条(4)定义的植物群体则不属于EPC 第53 条(b)排除的范围。
对于EPC 排除的“生产植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其中的植物则不局限于植物品种,而是涵盖了通过生物学方法生产植物群体或植株的方法;并且根据方法专利保护范围延及产品的一般原则,EPC 第53 条(b)排除的“生产植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还延及通过主要是生物学方法生产的植物。
在EPC 框架下,欧洲专利局(EPO,European patent office)审查实践中不断调整植物育种专利权的客体范围。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EPO 技术上诉委员会通过一系列判例法(Case law)逐渐明确了植物繁殖材料、杂交种子或杂交植物、植物细胞、转基因植物可以作为专利权保护的客体[8]。
因此,EPO 审查实践中属于EPC 第53 条(b)排除的植物育种相关主题包括3 类:(1)符合EPC实施细则第26 条(4)定义的植物品种;(2)生产植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3)通过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生产获得的植物(包括植物群体、植株)。除此之外的育种技术,则不属于EPC 第53 条(b)规定的排除。此外,EPO 技术上诉委员会还通过系列判例明确了有技术因素的介入产生的植株、繁殖材料、种子、植物细胞等均可获得专利保护。
3.2 欧洲植物品种权UPOV1991 年文本(以下简称UPOV1991)出台后,欧洲共同体以其为蓝本制定了《欧洲共同体植物品种保护条例》(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community plant variety right),使UPOV1991 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欧盟范围内得到统一实施。UPOV1991 第1 条(iv)对“品种”进行了规定,其采用了与EPC 实施细则第26 条(4)中排除专利权的植物品种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
欧洲专利权排除的生产植物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延及了由所述方法直接获得的植物,欧洲对其不授予专利权的原因在于生物学方法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方法、主要由生物学方法生产的植物仍是自然产物,因此不应被授予知识产权。除此之外,对于不授予专利权的植物品种、植物品种权保护的植物品种,欧洲将这两种知识产权体系中植物“品种”的含义统一,实现育种专利权和植物品种权的有效衔接。针对一项育种智力成果,育种者必需在植物品种权和专利权二者中进行强制选择。如果构成植物品种,则被专利权排除,只能通过品种权保护;如果不构成植物品种,则无法获得植物品种权,只能通过专利权保护。
欧洲的专利权和植物品种权二者互不交叠、相互补充,形成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模式”,这样既实现了两种知识产权类型对育种技术的充分覆盖,又避免了针对同一育种成果多种类型知识产权堆叠的情况。
4 总结
植物育种事关国计民生,鼓励种源科技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品种势在必行。在国际公约层面,目前UPOV 包括1978 年文本(以下简 称UPOV1978)和1991 年 文 本。UPOV1991 相比于UPOV1978 在保护范围、保护期限等方面均有所提高。据统计,目前UPOV 共78 个成员,签署UPOV1991 的有61 个,尚有包含中国在内的17 个成员仍签署的是UPOV1978,并且我国是唯一严格执行UPOV1978 的成员,其余16 个签署UPOV1978的成员也均对UPOV1991 的保护制度有所借鉴[9]。随着我国植物育种科技水平的快速进步,完善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保护水平,不仅是鼓励育种领域科技创新、维护育种者权益的迫切需求,也是为未来加入UPOV1991 做准备。
目前我国植物育种产业中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未能有效衔接,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真空[5]。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保护的“分离模式”不足以维护育种者权益、促进种业科技进步。对比研究美、欧发达经济体植物育种技术的知识产权制度发现,美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复合模式”虽然能够充分维护育种者权益,但对同一技术易造成多种知识产权类型的堆叠和重复,为后续的知识产权运用、侵权诉讼等带来较大压力。欧洲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模式”既能充分覆盖育种过程的各种智力成果,又能避免权利类型的重复和过度扩张。
尽管目前中国签署的是UPOV1978,而欧洲签署的是UPOV1991,但中国未来加入UPOV1991 的趋势不可避免[10],并且,中国的专利制度也是在充分研究了欧洲专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结合对中、美、欧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分析可知,欧洲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模式”对于未来完善我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欧洲现行的“双轨模式”同样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植物品种权和育种专利权的相互衔接而发展形成的,因此借鉴欧洲植物育种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权和育种专利权脱节的问题,并最终实现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对育种成果的协同保护。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