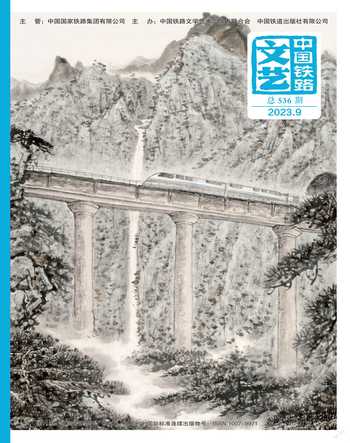藕花天
一
少年时光遥迢寻来。彼时,我的光阴在藕花天里细碎而悠长,像野荷渐渐黏稠起来的香气,粗手大脚地疏散着。
野塘里藕花未开,尚是尖红的菡萏。篱笆院里,小白狗趴在檐下,狗嘴贪凉触地,狗眼不耐烦地翻一翻,看两只俏皮的白蝴蝶低低飞,时刻警惕着不让其落到背上去。花脸猫喵喵叫着寻它嫩嫩的猫仔,娇声软气的,像小风挠人心尖。
姥姥在大太阳底下晒霉。高粱秆织成的箔经过旧年的汗水深一重浅一重地浸润,青春的绿颜色已变成黄脸婆。瘦小的老妇人在黄皮寡褐的箔面上,摆开陈年的衣物。一件件从樟木箱子里庄重捧出,座席似的整齐排列。斜襟的黑袄,肥裆的棉裤,尖尖如笋的绣花鞋,黑绒帽,绿棉袜。个个白眉赤眼的,顶着一头老阳光,舒舒服服地吐着潮气。
“晚两天,就到了南方的梅雨天了。咱这地界也下潮雨,沥沥拉拉,小孩子的清水鼻涕似的,下的人心里都长醭……”姥姥絮絮叨叨,“你娘就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大人娃们的衣物该晒一晒了嘛。那一年,我去南乡大妮家,你娘就潮坏了一柜子的好衣服,害得大娃二娃差点大雪天光屁股……”
娘在檐下闲适绣花。抬眼看篱前的蜀葵又开了两朵清红的花,不禁莞尔。那笑容纯净明媚如少女。姥姥的唠叨,小风一样吹过腮,刷一层薄薄胭脂红。
小婶隔着矮篱投进一把泼辣笑声,像飞来一篷灰喜鹊的鸟喧,喜喳喳洇开一团阳光。“杨娘呵!您老的绣花鞋像牛角哨描了彩釉。送我一双呗,放家去供八仙桌上,当古董。稀罕物,宝贝蛋,槐仙奶奶的花折扇。咯咯咯……”那伶俐的妇人笑得花枝乱颤像蜀葵。
姥姥迅速拿一块毛蓝头巾压住三寸金莲的绣花鞋。皱纹如菊的脸颊蒙上一层潮红,像被人窥见了赤裸裸一双弓背畸形小脚那般窘。没大没小的婶婶,一双大脚扑嗒扑嗒自在走过去,屁股后旋起一团得意的黄土。
彼时,塘上菡萏半红。村里花开如笑。小村里的花,自然有一点点野。含着笑,含着笑。盛开的花朵努力装作不张扬,是那种一低头的窃喜。却能让人暂时忘了时光的流逝。就像晒霉后的姥姥,只对着野花们发呆,痴迷。那些年离开小村的梦里,常常梦见姥姥。她笑眯眯地坐在故乡的篱笆院里,面前放一竹篮的红藕。那篮红藕盛着鸟鸣,露珠,少年,思念,都是故乡的味道。
二
塘上的红藕长了脚吗?活色生香走到娘的白篷布上去了。长尾巴的黑腹鸟也站到绣布上去了吗?闭着尖尖红嘴不说话。
爹正勤奋铺开一张隔年新打的箔,青枝绿叶地晒霉。
一箔汪洋的白阳光,托着娘花花绿绿的衣物。亮瞎人眼。滚了银丝边的软红小袄。绣了明晃晃凤凰的百褶的绸缎裙。描了红嘴绿鹦哥的花鞋。红被面子上大朵的富贵黄牡丹亮崭崭一点也不褪色,那香气像要跳到人怀里去。它们都是娘的陪嫁,也是爹引以为荣的阔气。一年一年都要展览似的晒。矮矮的篱笆遮不住的阔绰四下走。那是黑檐黄土墙的老屋多年来的荣耀。
当年娘是镇上杨裁缝的三小姐,虽然陪嫁就那么几件,也能在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里彰显爹的成功与骄傲。
“晒杨三姐的嫁衣吗?”有人从篱前过,手里拎几颗蔫头耷脑的恹恹绿苗,那是锄头误伤的小玉米。小黑布衫能拧下水。他把锄头从肩上卸下来,抱拄在颌下,用夸张的语气啧啧赞叹。惯常如此会换来一根纸烟。
“不晒要发霉了。可不要趁日头干燥晒一晒吗?这些好物件可不得及时晒!”篱笆里,爹加重了语气,年年都要强调那些旧物的好。
隔篱抛去一根烟。
那人不走,美美地吐着烟圈,大日头下站着,有一搭没一搭的,搜刮着干涩的语言继续夸箔上的物件好,时不时摇头深叹一句:“啧啧!村里没二家嘛,这些好物件!我屋里那位,当初就穿一件不露肉的囫囵衣裳过来的,只打了一块补丁,就算是嫁衣了。比不得朱先生阔气嘛。谁有你福气好?”
爹挺了挺腰身,小骄傲重上眉梢。
后面有人过来了。先来的那人烟卷也燃尽了。爹从薄薄的烟盒里新掏出两根,走过去,树荫影里站着。三个男人抽着烟,不说嫁衣,转说农事去了。
彼时,篱笆院。纸糊的格子窗。吱呀吱呀的旧木门。新木扎的矮篱笆。牵牛花翻过篱墙,一朵一朵探出来,举着水红淡蓝的小喇叭,明晃晃地耀眼。篱前的野生小黄花碎碎叨叨开得随心所欲,老屋看上去簪花满头的样子。有一些淳朴幽静,有一些闲美鲜喧,有看不见却触摸得到的一股子蓬勃气息。那是小院的味道,是娘的味道,是藕花天的味道罢。美得像南歌。
三
娘低头绣花,一朵,两朵。她只绣藕花。瘦瘦的妇人,眼神妩媚,也悄悄听男人们说话,只轻轻抿嘴笑,头也不抬。好像爹千宝贝万宝贝的那些物件,和她无关似的。
当然,那是寒门小户的爹的荣耀。对娘来说,那算得了啥?当初杨家大姐二姐出嫁,七大箱八大柜,满满当当,红了小半条街呢。姥爷恨三女儿私订终身,门不当户不对,米囤跳到糠囤里。就悻悻地随便弄几件红红的嫁妆打发了她。
想一想,娘居然不以为然。她就喜欢泥巴的村庄,泥巴的老屋。春夏秋的野花,那野生的密密匝匝香气追着人走。活脱脱的野趣,像她一双不裹的脚板,自由自在四下里走,没有羁绊。多好!
坐在敞篷似的檐下绣花,要风得风,要云得云。四季都可以戴花。想掐哪朵掐哪朵,哪朵水灵戴哪朵。花朵缠满篱笆,月光铺满小院。多好!
养一群肥肥的灰鸭白鹅,抱着小簸箩捡一颗一颗沾着新鲜粪便与羽毛的大个鸭蛋呀、鹅蛋呀,在铁锅里拿棉籽油炒了,滋滋啦啦的,香喷喷制造一盘人间美味。多好!养一只娇媚的花脸猫,生一窝白胖的嫩猫仔。喂一只小白狗,看它去追逐飛来飞去的蝴蝶撒欢。多好!
小灶屋低矮,高大的男人和儿子们弯着腰进进出出。躬身进来的他们,像给端坐在灶门前的妇人鞠躬致敬似的。有风的时候,风野性地乱吹,逗炊烟玩呢。粗大厚实的炊烟,囚在逼仄的灶间打着滚,不肯离去。熏出土蝉似的烧灶人,满面烟火色。她被呛成一朵流泪的蜀葵也心生欢喜。
娘喜欢小院烟火腾腾的生活。大姐二姐十指不沾阳春水,在深宅大院里生活,娘不喜欢。厚厚的胭脂水粉怎能遮得住淡淡的忧伤与孤清?每次相见,姐姐们也着实羡慕三妹野云似的生活。篱笆,炊烟,野花,白狗。粗拙,欢实,蓬勃。
庄户人家的生活。布衣,粗茶,淡饭。春天,娘像小姑娘似的和一群乡下女孩去垄上挖野菜,嘻嘻哈哈。笑声和脸庞都像露水洗出来一般明澈清新。一队鞋子上沾满新鲜泥土的女子,臂弯挎一竹篮青绿新嫩冒水的野菜,手里摇晃一枝明艳野花,逶迤着从垄上走来。身前身后笼着春光,前头犹有十万朵桃花开。美得像诗经年代。折身去塘里浣洗。一截截未经夏日漂晒的藕般的小腿,白白的脚趾引逗得几尾傻萌的小野鱼咬一咬,以为白藕。多好!
娘是个心有浪漫的妇人。光阴似乎没在她身上打下烙印。即使眼角生几条细细的皱纹,也似乎禁不住清澈无邪的笑声涤荡,云淡风轻地抹浅了。
姥姥晒霉,是爱惜旧物件,有柴米的烟尘味道。爹爹晒霉,晒的是光阴的荣耀,和支撑贫瘠日子的小骄傲。娘不晒霉,她只把一针一线的锦绣铺展在悠悠长长的光阴里,一半是满足,一半是希望。不恋旧,不回头,不遗憾,不羡慕。
缠满明晃晃野花的篱笆院,是她的童话城堡,里面住着她的王子和孩子们。她一直是没有南瓜车和水晶鞋的灰姑娘,可她极满足,极富庶,她有在人间做一个乡野民妇的快乐。
四
藕花开了。香气从塘上来。荷叶新翠,红藕扑簌,香气晃动,那是生命蓬勃的感觉,是美人的味道。彼时,野塘美得像诗经。
篱前屋后。爹的小瓜园里,小香瓜熟了,小白瓜熟了,花面瓜熟了,地瓜熟了,老艮瓜也熟了。二茬的西瓜小妞,藏在老绿的瓜叶下探头探脑。
娘的小菜园里也是花红柳绿,垂垂挂挂,熟了一片。
白月牙升上水一样蓝汪汪的天幕。那晚的月牙美又嫩。细弯的月边有一颗朦胧的孤星。像美人嘴边点了颗胭脂痣。那月儿,让人想起电影里柔嫩清新的林妹妹,十五六岁的年纪,清美得直冒一股仙气。
娘和爹坐在黑门楼下说话。娘膝头搭一条棉布的小围裙。脚边放着一个新编的竹筐,泛着莹莹的绿。她一粒一粒地剥蒜。脱了白衣裳的蒜瓣,白白胖胖地坐进小竹筐里晒着皎白的月光。
爹喝着大叶子茶,抽着一明一暗的烟卷。姥姥垂着头坐在矮矮的木凳上打盹。花脸猫不耐寂寞,不时拿脸蹭一蹭她裸露的脚面。老妇人拿手拨开肥绒绒的猫脸,继续打盹,发出微微的鼾声,像老猫。
月光里,娘和爹细声细气地商量着人间烟火事。
他们三儿子的婚期越来越近了。需要再打一座小厢房。小灶屋的烟囱也要修一下。还要造一个新猪圈,老母猪的肚子沉得拖着地皮了,不知道一个月后要新添多少小猪仔,不能让狭窄的猪圈囚住欢蹦乱跳的小猪蹄……这些事都需要实打实的银子来圆满。
爹说:“去卖瓜罢。”这些瓜蛋子今年长势真喜人。雨水足,阳光好。爹眯着细长的眼睛望着眼前的一片瓜地,像望着月光下一地白花花的银子。额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铺满欢喜。
“镇子小哇,腚坐的一片地。卖家比买家还多。二柱子家的瓜拉来拉去也没卖出去几个,倒是把他家几个半拉橛子(豫东方言,半大小子的意思)吃了个肚儿圆,欢喜的很呐。哪知道娘老子的难处!二柱子他娘急得抹眼淌泪……”姥姥突然清醒了,说了一串明明白白的话,心头万斛愁的样子,深深叹气。
娘不语,依旧低头窸窸窣窣剥蒜。姥姥见她不知人間忧愁的模样,气得狠狠拨拉开脚边撒娇的猫,气咻咻拎着板凳回屋睡觉了。
爹抽完了一根纸烟,没有点燃第二根,只从腰间摸出小烟袋,在烟袋锅子里压实一撮碎烟丝。他拿手里尚有一丝红意的纸烟头,按到烟锅子上,再狠狠吸两口,小烟袋就美美地燃起来了。再把纸烟头丢地上,拿脚尖子碾了。
月牙渐渐丰满了。林妹妹的弯弯黛眉变成了刘姥姥的卧蚕眉。月光也丰厚起来,露水也深厚起来。
娘拍拍两只手,抽下膝头的棉围裙,立起身子,走到远处去抖一抖,转身端起满满的竹筐回屋去。再转回来时,身上披了旧红的衫子,手里拎着一把蒲扇。坐下来,扑扑嗒嗒给爹驱赶贼似的尖嘴蚊子。
他俩沉吟着。月光也沉吟着。花脸猫和小白狗卧在脚旁,一边一个,软塌塌的小肚子一起一伏,睡得香甜,不知人间忧愁的可爱小模样。
月牙儿偏西了。
娘眼里清亮亮的,像落了小星与露水。身边的凤仙花与蜀葵在晚风里轻轻摇着花朵,像给娘执扇的挽髻婢女。娘突然欢喜起来,拊掌笑道:“有啦!有啦!朱先生,我想到一个卖瓜的好去处。”
爹看着她孩子般欢喜的面庞,月光下那般生动纯净,可不就比凤仙与蜀葵还好看吗?
五
露水在草本上卧睡未醒。虫儿伏在草丛里,叽叽地细碎叫着,声音格外潮,有点像清晨的空气,新鲜得过分。爹和娘起床了。
爹从淘草缸里控出最后一捞子青草,放进大黄牛的石槽里。再给大黑猪的旧陶盆里倒进半桶猪食,撵出鸭笼鹅舍里睡意正浓的小东西。关好篱笆门,嘎嘎叫的鸭儿鹅儿们只能在篱笆院里溜达,万不可撒出去的,要不然瓜园菜园可就会被打劫似的给祸害了。小白狗倒是勤快,围着忙碌的男主人撒欢讨好,一副睡足后的欢快与亢奋。
天边的月牙还没走,隐隐约约的,像躲在轻纱幔里的小美人,似乎要等着和太阳道别似的多愁善感。架子车上几个深大的竹筐里,沾着露水的黄白青绿的新鲜瓜装得冒尖。收拾停当,天还没有透亮。爹挎上袢绳,准备出发。娘推着那辆旧自行车,车大杠下的帆布兜里装了干粮、水壶、毛巾,还有爹的小烟袋。叮叮当当像晨曲。
爹和娘一前一后,在细细弯弯的小土路上走着。
彼时,天上,流云有点醉,斜斜地走,游丝软系的小模样。垄上,玉米新绿,长势喜人。塘里,菡萏绽红。一阵阵红藕吹来的香气,带着露水的潮润,和细软不燥的晨风一起,鼓荡起娘的旧红小衫和爹的对襟黑布衫子。他们脸上挂着清新明朗的笑容。走在开满萱草花的乡间小路上,像去吃席一般欢喜。
赶到镇子上时,狭小的集市已摆满瓜果蔬菜的小摊。农人们脸上挂着期盼的笑意。渐渐起燥的日头,在黄草帽下他们黝黑的脸膛上制造出细碎的汗珠。爹的瓜车吃力挤过熙熙攘攘的街面,晃晃荡荡,像穿过海面的一叶摇晃小舟。有三村五里相熟的,欠起身子打招呼:“朱先生,带着杨三姐哪去呀?有没有好去处,也捎带上咱呗。”
爹的瓜车被挤得晃荡,左右摇摆,大声回一句:“好着呢!先去探一探,好卖了,再回头叫上你。”
爹把瓜车停在供销社家属院前的一棵合欢树下。树上合欢开得正好,一朵一朵细细茸茸的花朵,纤柔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似的。娘捡起地上的一枚落花,像举起一柄小小的红折扇,遮在眉边,好生怜爱。
刚从车上卸下瓜筐,便有穿崭亮白短袖的男子走过来,一看就是衣食无忧的人。看见新鲜的瓜,男子忍不住啧啧赞叹:“好瓜!好瓜!这一看呀,没有三五年的经验种不出这好瓜来。”随手称了鼓囊囊一网兜,喜滋滋往家走。远远地看见他跟邻人打招呼,回身往合欢树下指,那人便径直朝爹的瓜摊走来,也拎一网兜去。
挽着鸭蛋似的灰白发髻的老婆婆颤巍巍走过来,衣衫干净,面容慈和。娘的嘴巴甜,婶子长大娘短的,像甜蜜蜜喊自家的亲婶娘似的。小秤砣高高的,让人欢喜。临了,送一根绿胖水灵艮瓜。“自家地里的,不值几个钱,老婶子拿去给孩子们拌凉面吃,可脆生了。”
抱孩子的年轻妇人悠悠荡过来,挑挑拣拣,嫌肥厌瘦的,总能说出个褒贬。娘一点也不恼,软声柔语,十二分的耐心。自恃优渥的妇人到底有些不好意思了,终究慷慨买了两大兜,付钱的姿势多少带些傲娇。娘甜甜笑着。
妇人打量着她,忍不住说一句:“你的发髻真好看!银簪子也好看。”娘笑笑说:“你的短头发才好看呀!又年轻又时尚……走,我帮你送家去。”妇人怀里粉团似的婴孩冲娘咧嘴笑,扎舞着藕段似的胳膊要娘抱。
彼时,热风在大地上游走,吹过瓦舍,吹拂老树,给人留下几树合欢。阳光从密密匝匝的红合欢花朵里筛下来,落在娘瘦瘦的身上。一额头粉腻腻细碎汗珠子的她,面容明净慈和,像送子娘娘。
六
南乡的大姨来了。
彼时,藕花开得正盛。像给老塘穿了红衣,搽了胭脂。野塘四周绿木树篱,像矮墙,圈起塘上无数朵红藕。多年后回想彼时情景,想起一个词——妖娆,妖娆得惊艳。
小架子车吱吱扭扭从陌上来,一路穿过多少野塘上的藕花香。小脚老妇人的臂弯挎一只白底蓝花的包袱,端坐在车上。二表哥推车。车旁跟着一个蓝花布衣的十一二岁女孩,脸庞清秀,眉眼间颇像大姨。
我和娘,还有新媳妇三嫂嫂,三人站在村头的野塘边,翘首迎接凤辇似的庄严木车。塘上的藕花朵朵都红了脸,香气送进衣服里、头发里。我偷偷看一眼身边软红衫子的三嫂嫂,唇红齿白的娇美模样,可不就像一朵极美极鲜的藕花吗?
大姨带给我们很多南乡的吃食,糯米果子,油酥饼,梅花糕,雪片糕,每一道点心都是大姨亲手做的。彼时已是地道农妇的她,举手投足间依然有曾经的清雅与端谨。
她送给我和三嫂嫂每人一块绣了清红藕花的白绸料子,嘱咐我娘找镇子上的好裁缝给做两件小旗袍。娘羞赧一笑,说:“庄户人家哪能穿那娇气衣服?放着罢。”
名字叫莺儿的小女孩,南音细婉地说一句:“料子是奶奶用两升新稻换的,藕花是她亲手绣的。”
大姨迢迢探亲而来,必定是要小住的。我和莺儿便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伴儿。两个十二岁的女孩,我甜蜜蜜地喊她“莺儿,莺儿”,像唤头顶飞过的一只好看的黄莺鸟。她脆生生地喊我“灵儿姑姑”,水嫩嫩的南音像心上吹过一缕沾了藕花的晚风,凉而生香。
彼时,乡下暑风起。热浪把俩小雀子似的丫头轰到野塘边。
多好!红藕花铺了小半面塘。野菱角也顶着一头小白花,透着野性的美,忙着给绿荷叶子镶边呢。雅得很,香得很。我恰恰刚读了娘珍藏的旧书,《诗经》呀,《南歌》呀。那些写荷的字眼,红花瓣似的一个一个直想从心里欢喜地跳出来。
拉莺儿一起坐在塘边,露出细瘦瘦的腿,垂进凉凉的塘水里左右摆荡。黑黑的小野鱼追逐着咬脚丫子,痒得我俩咯咯笑。
那时,我家篱笆院里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那是秋上的采菱“小船”。秋天时,我撑着它在塘上悠悠采菱,像南歌里走出来的小女子。
大姨看出了像乡下小子般泼野的小丫头的心思,再三叮嘱我:“万不可带莺儿下塘。”
“那木盆会翻的,塘水多深?淹死人也未可知。”老妇人的脸上布满恐惧。我绷着脸忍住笑,咋就会淹死人呢?秋上采菱,我一天在塘上穿行八百回呢!村上的孩子都这样啊。可惜,莺儿等不到秋天就会走的。我心里直想把那采菱的美好场面给她看。
我只好拉她坐在塘边。野塘像一纸的风吹莲动。
“头上顶一张荷叶的绿盖,像不像你们南乡的油纸伞?”我问莺儿。再蹚水摘一朵盛开的红藕给她,莺儿抱在胸前。藕花映红了白净的小脸。她两腮像搽了胭脂。可不就像一朵鲜嫩娇美的藕花吗?
我给她摇头晃脑地背唐诗《采莲曲》:“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背《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莺儿细声细气地跟着我背,一句一句很认真。慢慢地,清亮的眼睛蒙上淡淡的惆怅。小女孩垂下头,很忧伤地说:“灵姑姑,姨奶奶让你去读书,多好哇!奶奶不让我去读书,说女孩子会绣花,会做糕点,长大嫁一户好人家就行了!我好想讀书呃。我们村里好多男娃女娃都去读书了……”瘦小的莺儿伤心成一朵被掐断的藕花。
那一小段日子,我在塘边,教会了莺儿背好多唐诗。塘里的藕花也像被我教会背诗的样子,每一朵都是一张红笑脸,带着前世今生的味道。
月亮白润的夜晚,一塘的蛙鸣。两个红衫少年坐在小莲花旁边,看花看月亮。浮动的光影里,真像两朵出水的小菡萏。
彼时,少年的眼中,即使月亮,也是一朵白莲花。就那样,在天上,开呀开,开呀开。突然,月光跌下去,落在塘水里,有些银白的亮光。塘上大朵大朵的红藕,在月色里迷离柔凉,红蒙蒙的,像红襦绿罗裙的小姐,美得心里一痛。
日子过得极快,飞刀似的,割着相聚的欢悦。大姨带着莺儿要走了。
我俩的离别有了少年的愁滋味。像鲁迅的《少年闰土》。虽然我不是少爷,只是个被开明的娘送去学堂读书的乡下丫头,野生的藕花似的。但谁知道呢?会不会就一别数年,从少年到中年呢?浓浓的离情使两个少年抱头大哭。惹得大姨与娘也落了泪。千万遍地哄与劝,到底还是生拉硬拽地分开了两个泪人儿。
莺儿走了。带走了我的一颗心。无忧无虑的野丫头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苦涩滋味。我送给莺儿一本唐诗。不知道她会不会偷偷读,不会的字会不会找人教。
我追着车子跑了好远好远。很远处,云团缓慢撤掉,吐出浩荡的绿野,连绵不绝,像海。那辆小小的架子车像一叶小舟,倏忽间被吞进绿浪里去了。
彼时一别,莺儿似乎淹没进了人海,多年杳无音信。少年的我那想念是逼真的,是无限惆怅与忧伤的,心里的红藕开得正明艳时,会偶尔闪过一张少女泪水潸然的脸。
那个藕花天,十二岁的少年,生了第一缕人间的忧愁与牵挂。
光阴再长,都挡不住旧年的芬芳。如今的藕花天里,还是绵密而妥帖的好日子。舍不得惊动往事,那些人世间最干净的甜蜜、饱满和深意,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