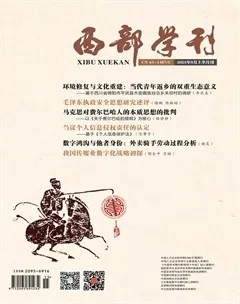夫人外交与萨拉·康格对中国女性的印象
郭明君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湘潭 411201)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在列强的欺辱下被迫打开国门。 这一时期,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的著作中经常是负面消极的,西方人在看待中国时往往带有歧视或贬低的意味。 来自美国的外交官夫人萨拉·康格随丈夫驻京之后,在一系列交往活动中,却能以友善的态度来观察中国社会,其著作中对中国的印象是较为积极的,尤其是她书信中勾勒的女性形象。 本文从萨拉·康格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社会地位的角度出发,总结在当时的外交图景之下她所形成的对中国女性的印象,并分析造成这种不同印象的原因。
一、动荡中的开放——来华之路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主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如清乾隆时期将对外贸易限定在广州,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西洋贸易,变“四口通商”为广州“一口通商”,而且外商具体的来华贸易只能通过洋行、行商等政府特许的机构和人员经办。 此外,清政府明确发布了“禁止番妇入省”的禁令,命令“各国夷人航海来粤贸易,每年春夏皆寓居澳门,至秋冬间因出进货物均在省城洋行交兑,即移驻省中夷馆。 其随带番妇向只准居住夷船”[1]。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的活动,对外国人正常的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从而迫使外商不能长期滞留中国。 这种受中国传统的“夷夏大防”和“男女大防”观念影响而形成的政策,逐渐引起外国人的不满,中外双方多次因此发生冲突和摩擦[2],如1830 年著名的“盼师案”,就将中外之间有关“番妇入省”的冲突推到了最高峰。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于上述条例的执行也逐渐松动。 如《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3]31,此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亦有类似的规定。 随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此之前颁布的相关禁令逐渐难以维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京师”[3]9,明确指出外国使节可携带家眷常驻京师或随时往来。 至此,外交官夫人才正式随其丈夫来华常驻。
随着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欧美列强趁机对中国进行瓜分。 美国在利用美西战争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后,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这片土地上,但此时西方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已经进入高潮,美国政府意识到自己将落后于他们,并认为这会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 为了保障和扩大其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来消化美国国内过剩的劳动产品,美国试图尽快参与到瓜分中国的行动中。 如1898 年,美国总统麦金莱在《国情咨文》中表示:“采取与我国政府一贯政策相适应的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那一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4]。
在上述大背景下,1898 年,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来华。 她于1843 年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与其丈夫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从小相识,于1867 年结为夫妻。 1898 年,继田贝(Charles Denby)之后,爱德温·赫德·康格奉命自巴西调任至中国,接替美国驻北京公使的职务,萨拉·康格随之常驻北京。 1900 年,他们在被迫经受了“庚子之乱”的围困后奉召回国,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康格再次来华赴任,直至1905 年辞职回美,夫妻二人一同在北京生活了7 年[5]1。 萨拉·康格作为当时各国外交公使家眷中最具代表性的夫人,积极地在京展开夫人外交,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述为信分别寄予亲朋好友。 1909年,她将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名为《Letters from Peking: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中文译作《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6]。
二、突破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女性形象的描绘
夫人外交是欧洲国家的驻使惯例[7]。 欧洲各国使节每到所驻在国,都须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茶会、游园、观剧等文化活动,或宴请其他政要官员及各国驻该国使节夫妇,以示友好联络,以便开展外交[8]。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西洋茶会皆由夫人主政也。”[9]1898 年萨拉·康格随其丈夫来华驻京之后,就通过茶会、游园等活动积极参与并开展夫人外交,并将这些交往记录在书信之中,向世人展现不同的中国女性形象。
(一)关于慈禧太后
在萨拉·康格的书信中,曾有多次觐见慈禧太后的记载。 她笔下的慈禧太后作为中国的最高当权者并不是完全固执保守的,萨拉·康格曾不止一次夸赞她非一般人的观察与接受事物的能力,认为她做了很多“从来未有事”。 例如《北京信札》中记载在开展夫人外交时,慈禧太后开始接见外国女性、开始照相、接受康格夫人的建议邀请美国画家卡尔为其画像,并同意次年把画像送至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等。
虽然萨拉·康格对慈禧太后这位“特殊女性”的评价与现如今流行观点大为不同,也值得继续商榷,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提供了另类的叙事空间。 如萨拉·康格认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展示了这位被故意错误报道的妇人的真实感情和个性”[5]204,赫德兰夫人也在回忆录中表示这些“有利于纠正外人对她的错误印象”[10]。 萨拉·康格书信记载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即体现出当时清政府愿意改变国际形象,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的态度。
(二)关于满汉贵族女眷
萨拉·康格对其他中国上层女性形象的描述也较为正面。 她通过夫人外交活动逐渐扩大了交际圈,礼尚往来的相互宴请使她与许多满汉贵族女眷变得熟络,这个无形的中美妇女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 越来越多的中国太太邀请康格夫人去自己家里聚会,她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从刚开始的中美双方的文化风俗,逐渐转变为对兴办西学和禁止缠足等相关政治问题的讨论。 例如《北京信札》中多处提及诸如各地女子学堂的创办、女性报刊的创办、徐氏三姐妹的学习、蒙古贵族妇女的办学发行等事例,无不展示出一幅清末女性解放运动的场景:
现在的中国和五年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了。处处都能感觉到变化,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变化特别明显。 北京城内现在有17 所女子学校,均由中国女性资助和管理,她们之中有一些是宫眷。 这些女士比以前更渴望在更多的方面受到教育……这些人的帮助更加激发她们想要了解高墙外的世界的炽热愿望[5]306。
总的来说,上述书信中记载的那些不论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交性的联谊,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上层的福晋和格格们试图打破高门大院的种种束缚、不再拘泥于自己闺阁的努力,她们想要了解外面世界的愿望逐渐日益强烈,这使萨拉·康格看到了中国妇女正在逐步与旧习俗告别。
(三)关于下层普通妇女
除了通过上述夫人外交结识的中国上层女性形象,康格夫人在日常生活的交往过程中接触过一些中国下层的妇女,在书信中对她们的印象也是较为正面积极的——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整洁干净。 如在义和团运动外国驻华大使馆被围困时期,萨拉·康格多次称赞这些普通的中国妇女,“她们照料着伤病员,通过不懈的努力表现出无畏、勇气和柔情……”[5]129;在福州游玩时,她看到了与之前记载全然不同的中国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她们不鲁莽,性情娴静……她们把舢板打扫得和自己一样整洁,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戴着花儿和银饰……”[5]131
总之,萨拉·康格的书信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流露出一种努力“挣脱”同时代人所秉持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立场和较为友善的态度,称赞中国女性不仅在穿着和行为上整洁干净、优雅得体,而且在思想上也开放进取、关心时政、有独特的见解和学识。 虽多局限于上层女性的形象刻画,对下层女性的着墨较少,但整体上还是对当时中国的女性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正面评价,是其对当时中国上层女性进步的肯定,对下层女性质朴的写实。
三、印象背后的暗流涌动——原因窥探
1750 年前后是西方形成两个极端中国印象的关键节点时期,西方美化中国的中国潮开始退却[11]。 随着礼仪之争、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失败等事件的催化,中国在西方人心中的印象逐渐进入下降的趋势,并产生许多负面印象。 十九世纪,随着一系列战争的爆发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最终完成了西方人心目中腐朽堕落、停滞落后、复杂多变的“劣等他者”中国印象的塑造过程[12]。
典型的负面印象有中国女性是“劣等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群体,例如1858 年出版的《宝楼氏画报》就在评论中指出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多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奴隶和玩偶[13]。 总之,她们要么被批评得一无是处,要么就是备受摧残和压迫的可怜形象。而在同一时期,萨拉·康格作为一位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西方国家外交官夫人,却在其留下的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北京信札》中流露出与上述提到的与众不同的中国女性印象。 萨拉·康格之所以可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女性进行评判,不仅受当时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她态度的影响,也与她的个人品行及背后的国家利益有关。
首先,受慈禧太后及满汉贵族女眷态度的影响。除了正式的觐见,上述书信中多次记载了慈禧太后与萨拉·康格的私下交往,慈禧太后甚至像朋友一样热情招待萨拉·康格,坐在她的炕上聊天。 萨拉·康格与中国上层的贵族宫眷经常相互宴请或者赠送礼物,她们彼此之间的礼尚往来、交往中日益形成的友谊,以及在谈话过程中中国女性明显流露出的思想行动的转变,都使得萨拉·康格对中国及她的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5]302。
其次,这是萨拉·康格对西方文明中固有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的结果。 萨拉·康格作为公使夫人常年跟着丈夫旅居海外,《北京信札》中提到之前在南美的经历让她得以反思:“南美的经历对我在中国大有裨益……经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一定是我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造成了这一切。”[5]3之前的经历让萨拉·康格意识到民族优越感可能会影响她的判断,故要改掉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平视的眼光观察中国。
最后,除去萨拉·康格自身良好的品质和个人修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正是处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时期,为了扩大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逐渐用干涉主义取代奉行多时的孤立主义,积极落实“门户开放”政策,故其“亲华”要求较为强烈。 1900 年9 月,国务卿海约翰在和谈开始后,就曾指示康格对清朝统治集团内亲外的改革派官员予以保护,将打击清廷内排外保守势力,拉拢扶植亲外的改革派势力作为影响清廷朝政走向的重要手段[14]。 故而,除了朝堂上康格代表美国推进亲华的“硬性外交”外,萨拉·康格在朝堂之外响应美国的对华政策,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展开“软性外交”,对慈禧太后乃至清廷其他王公贵族的家眷多持亲善态度加以拉拢,进而推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 所以,在她的书信中对于慈禧这个女性掌权者,以及上层贵族亲眷都出于一种赞美、欣赏的态度,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对异域国家的他者形象的塑造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之间利益发展变化的真实体现和反映。
总而言之,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萨拉·康格书信中对中国妇女的评价可能会囿于她个人情感方面,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公允的。 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她能够以平视甚至多带一丝友善的态度看待并记述这些的人与事,让读者看到当时中国女性的另一面。
四、结语
萨拉·康格在华的外交活动,与1900 年前后方兴未艾的时代大潮流相比,只是其背后的以女性交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幅近乎湮没无闻的画卷,但她书信中记载的中外妇女交流的情况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正在步入剧变的时代,以及一些中国人在这剧变的时代中不断努力调整步伐的实践。 即便这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与解放仍不能改变清政府的腐败与命运,慈禧太后对外交官夫人的友善与热情也不能改变她自身的弄权与专制。 但萨拉·康格书信中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固有的刻板印象,对于塑造和培养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此外,在这里仍需指出,尽管萨拉·康格的态度亲善且客观,但其本质还是一名西方列强驻华公使的夫人,她思想无意识的层面中还是流淌着隐形的西方主义的暗流,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