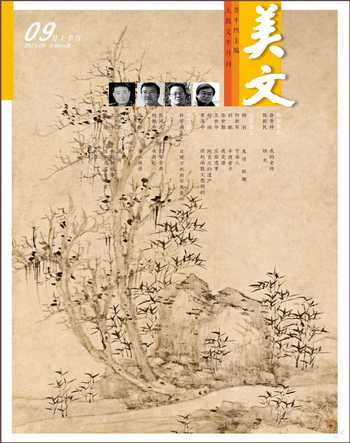淇河
田万里
二十八
深夜的梦里,河流不请自来,我仿佛是一尾鱼游来游去,自由自在。
曾经,我每天早上都会沿着河岸散步。河里的倒影伴随着我走过许多岁月,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仿佛青春的雕像矗立在岸边,仿佛刻骨铭心的往事倒映在梦里。
有时候,一个人来到淇河岸边,空空落落的心顿时踏实许多。河流仿佛童年的伙伴,在我心事重重的时候,来到它的岸边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淇河总是能理解我、呵护我。
淇河从来没有错过我开心的时刻。每逢这个时刻,它总是用浪花挑逗我一下甚至几下——它在我的眼里本来就是一条母亲河。
日日夜夜是它,时时刻刻是它。远在他乡是它,身在异地是它。梦里呓语是它,闲暇之余是它。热血沸腾是它,热恋冷思是它。天山之巅是它,天山脚下是它。字里行间是它,段段落落是它。前呼后拥是它,主题分明是它……
只要一有时间,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寂寞就会铺展开来。孤寂之中,随便写上几笔,便是我的故乡——樱城鹤壁。怪不得异乡求学期间,常常忍受这般浓浓的思念。
思乡之情凝聚起我的创作精力,故乡仿佛有一种伟大或崇高的魄力,引领我的脚步。它需要我去想它、思它、写它、吟它、念它、颂它、歌它、唱它、抚它、爱它……
这就是离开故乡多年的一个游子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沉默、一种坚毅、一种情感。
二十九
在他乡求学期间,我常常感到淇河在我的生命里,伴随着血液奔流。就像故乡的一山一水那样,附带着童年的故事来到我的身边。这其中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比如鹤山区矿务局北站汽车运输队家属院那个破旧的院落,至今都令我難以忘怀。
别看那个院落是多么破旧,但那是我三十三岁以前的家啊!从小到大我就生活在这里。咿呀学语是它、蹒跚学步是它、小学中学是它、风里雨里是它、寒冬取火是它、春天踏青是它、北山游玩是它、半夜星光是它、羑河戏水是它、雨中回忆是它……
一想起这些,身处异乡顿觉并不那么孤单了。淇河亦是如此,从此也不孤单了。
上课是淇河,下课是淇河。早上是淇河,晚上是淇河。看书是淇河,作业是淇河。恋爱是淇河,拥抱是淇河。散步是淇河,静坐是淇河。操场是淇河,跑步是淇河。电影院里是淇河,紫藤园下是淇河……
可以说,淇河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无处不在,相依相偎,不离不弃,难舍难分。
也许以后,我时时就可以像淇河一样那么流淌了。张嘴是淇河,闭口是淇河。睁眼是淇河,闭眼是淇河。伸出是淇河,收回是淇河。抬头是淇河,低首是淇河。写信是淇河,读信是淇河。电报是淇河,回电是淇河。长途电话是淇河,默默无语是淇河……
淇河无时无刻都伴随着我,就连它的流水声夜夜都会响彻耳畔。
淇河并不是一件孤单单的事,尽管它可以单独存在。
是否可以好好慰问一下它了?趁今夜月色浓浓,就给它写一首诗吧!或唱一首歌也行。我在梦里缠绕着它,亲吻着它,拥抱着它,欣赏着它……
同时,我不停地转换着角度,从各个角度观察着淇河的生态变化。
淇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赏,它依然是我童年时候的伙伴,是我小时候玩耍嬉戏的一条河流。
虽说我离开它已经很久很久,但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日夜都可以触摸它、爱抚它。
生态林仿佛是它的外表,河里的鱼儿可谓它的精灵。它与其他河流的区别就在于鱼儿承载着我的思念,已游入灵魂深处。
淇河有时候也是不可触摸的,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敢触摸。一旦触碰,思念就会像洪水一样朝我袭来。或者说思念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根本无法将其移出。
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偶而也有发生。思念一旦从孤寂之中挣脱出来,仿佛天地都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思念中的故乡在我眼前以千百种面孔交替闪现,这让我激动不已,但我只能在静默之中孤独地享受。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随手拍,就连照相机也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必须在写作中感受故乡,在思念中触摸故乡。
三十
其实,故乡的概念很宽泛,并非一景一物或所指定的位置。脑海之中随意闪现的某个熟悉的地方可能就是“故乡”二字安置的地方。
故乡必须是心灵空间安静的产物,是愈来愈浓的一种情感,就像埋放在记忆里几十年的陈酒,看似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一旦打开,从未变味的乡情就会在浓浓的思念之中酝酿出自己的佳酿。
思乡之情始终释放在我的写作和生活之中,灵感缠绕着它,构思围绕着它,汉字浸透了它,文章承载着它。它就像空气一样附在我的身上,从此我再也离不开它了。我把它压在书本里。我把它流放在文字里。
这样的空气,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
它在呼吸里进进出出,我的生命就像它的壁龛一样。这样感受故乡的结果,其实就是一种踏实、一种温馨、一种来自故乡——樱城鹤壁——的生死情结。
三十一
淇河也会以很单纯的方式久久地存在于我的体内。这样的寻根意义并非其他事物可比。
——它是崇高而伟大的。
关于淇河的自然生态,关于淇河的前世今生,其实我并不陌生,还是了解一二的。但对于淇河的深度必须由有关专家来解读,我尚需慢慢地研究。
一般人看到的只是淇河的表象,如果把手沉淀其中,冬暖夏凉的感觉只是身在淇河之外的感受。
淇河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对它的抚摸和界定,这说明淇河对于自身之外的关注并不反对——反而更受它的欢迎。
当那些来自它内部的自然和生态与外界的需求相融合的时候,大自然的界定和限制才能够显示出相对的正确性。
三十二
似乎我已经完全浸入淇河,孑然一身,在清澈的道路上愈陷愈深,愈走愈远。偶而掉落在身后的一些感悟,一尾鱼儿会把它导向另外一条路上。
在文字里,我所寻找的一个方向就像一种规律渐渐地浮出水面。不仅如此,由于光合作用下的芦苇荡在波光里悄悄地完成了一种组合,这样的话,河面上的逆光只是一种浮光掠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这样的审美观点都是成立的。
假如仔细观察的话,进而显现出来的一次与另外一次都有所不同。甚至,每一次都是有所区别的,每一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细节。
由此,我想起童年时的一个夏夜,蛙鸣四起,好像是淇河在欢迎我的到来。
仔细辨识,没有一处响起蛙鸣的地方是迟疑的,是忧郁的,是不安的,是徘徊的,是忐忑的,是前瞻顾后的,是犹豫不决的……
感觉里,蛙鸣铺天盖地而来,星光下是那么灿烂、那么皎洁。蛙鸣停留在耳畔究竟有多长时间?仿佛它们的叫声从来没有停止过,终止过。
期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没有任何物体可以阻挡蛙鸣的到来,即使在深夜的梦里。
三十三
此时,我基本上已经确定情感里的故乡情结——那便是淇河。
河流里游动的一尾尾鱼儿仿佛是我的生命细胞。那些孕育生命的细胞,一个个都是那么伟大,一个个都是生命里故乡情结的坚强支撑,一个个都是来自于故乡的亲人啊!一个个都是荡漾在文字里的亲情啊!
那些在文章中再三强调的、再三确定的情感,必须由淇河里的所有生物共同来完成。
自从写到了淇河,有关这方面的创作元素隐隐约约,不时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时而翱翔蓝天,时而潜入水下。时而蛙鸣阵阵,时而浪花飞舞。时而河水汤汤,时而游来游去。时而跃出水面,时而呼吸清香。时而浪花滔天,时而逶迤而行。时而急转直下,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心潮澎湃,时而静如止水。时而沉入梦乡,时而浮上案头……
三十四
我为淇河而歌唱,我为淇水而发声。
这条让我彻夜难寐的河流奔腾于字里行间,仿佛故乡的呼唤由远而近,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渐渐使我的思念清晰起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淇河就是夯实在生命里的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自然,一种生态。
也就是说,这是情感元素的具体体现,始终挺立于精神层面,塑造着我的思念和心情。无论再远的路,只要一想起淇河,故乡便不再遥远了。
至今想起淇河的美,我还是这么认为的。
淇河并非一种单一的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于此、沉淀于此,才使它在清澈中凸显出一种大美。
眺望它的时候,能够触摸到它的美。呼唤它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呼吸它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它的美。思念它的时候,能够拥抱着它的美。亲近它的时候,能够收获它的美……
三十五
當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仿佛这一切都已结束。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殊不知,淇河韬光养晦的大美之处,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现出来。
此时此刻,夜幕还没有完全退下,霞光随着淇河流淌的时候,与我,与岸上的树木,与花草,与樱城鹤壁这座城市共枕一梦,相互交汇在一起。
随着我对淇河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创作的构思方向又有了新的突破。
意念中的淇河似乎已经突破传统文化中的形式。在这种状态下,淇河的价值才会真正地凸显出来。
淇河在我的笔下,无论平静的状态多么优雅还是奔腾的姿势多么雄伟,它从来都是平易近人的。傲气已经融入它的浪花里,极少显现,但清澈却是它生动的面容,人见人爱。
说起来,也只有清澈才是它表现的最佳手段,更是它的生命之本。淇河恰恰在这方面最具有优势,能够掌握或充实其生命的,当然是清澈的河流和水质了。我在创作之中紧紧把握住这一个关键点,所写到的文字仿佛都是淇河扬起的浪花。
这些大美的精致,存在于一切自然生态之中。
三十六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把握住淇河的这一个关键点。我日夜追随着它、观察着它。
一年四季,风风雨雨,风霜雨雪,冰天雪地,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淇河大美的脚步。
淇河汛期到来的时候,我的脚步并没有踌躇不前。
时而河岸上,时而河岸下。时而山头上,时而峭壁上。时而花蕊里,时而草叶上。时而骄阳下,时而月光下。时而深夜里,时而星光下。时而风雨中,时而暴雪里。时而狂风中,时而闷热里……
淇河旱季来临的时候,我依然迎接着它。
时而一汪泉水,时而几滴雨珠。时而卵石之下,时而枯叶之上。时而龟裂之中,时而彷徨之时。时而抬头望天,时而低头凝思。时而夜色如墨,时而夜色匆匆 。时而徘徊不定,时而驻足不前。时而流连忘返,时而去意已决……
我早已发现生命之中的河流源于淇河。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是汛期或旱季,河流始终是充盈的、清澈的。无论淇河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一谈起淇河,在场的所有朋友似乎都能够感受到淇河的伟大之所在:清澈。
三十七
在人们眼里,淇河的魅力永远是强盛的、强大的。对于我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思念中的生命没有一天不属于淇河。
淇河之外的,或许是微不足道,或许是毫无任何意义。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张一弛,一进一出,一紧一慢,在这些行为举止里都是活生生的淇河在涌动、在奔腾。
三十八
实际上,看上去没有任何表情的河流,它的生命是极其丰富的。有时,从它缓缓流淌的波纹里就可以看出,而且,这跟当地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眼就能辨识出其表情,因为它内在的诗性已经浮出时间和空间。睁眼或闭眼之间,它的诗性就在河流之中不断扩散、不断扩大,而且在清澈之中更具有神秘性、永久性。
它从来不善于装饰自己,伪装自己,掩饰自己。
基于以上这类情况,随随便便或不经意之间朝淇河瞥上一眼,突然就会发现有它的地方,沿岸的生态总是那么美好。
喜欢感受大自然的人,一旦遇见淇河,心情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脸颊上就会多出一份惬意。
贴在脸颊上的那副面具早已融化在水里,鱼儿噙它而去。
三十九
大自然的面貌在人们的眼里完全且完美地体现出了原生态的色彩。由于这篇文章所倡导的主题引领,我不仅仅停留在自然和生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发现了河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就像大自然所拥有的世界一样,其灵魂深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物世界。
人类为了这样的环境而不断付出,为了这样的期待而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这里所见到的淇河儿女,实际上都已成为另外一种河流,成为了成千上万条河流。每一条河流都是这座城市的生态之脉,每一条河流都体现出充满生机的精神世界,而且,各有各的动态走向。
其实,只有这样的淇河才能够表现出来樱城鹤壁的精神风貌。
四十
时光荏苒,转瞬即逝。
我作为一位从淇河边长大的文学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成为一位生态方面的写作者。
蓦然回首,其实在我年轻懵懵懂懂的时候,或渐渐地就已经踏上这条原生态创作的道路。亦如原生态的自然,原生态的生活,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哲学等等。
至于当时创作的意图,我并不能诠释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些感受和体会,隐隐约约,时隐时现。比如所谓的原生态其实就是大自然和生活的本来面貌,就是尊重历史、哲学、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
而传统的散文、随笔等讲究的是形散而神不散,次之就是流水般的语言。
但在这篇文章里,我完全打破这些传统的写作方法,意识流、蒙太奇、时间差、时空交错等一些当代文学写作技巧相继运用于此。可以说句句为境、段段为意。唯有求新求变,才会拥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方式。
故而,这篇文章里无疑诠释出了中国式的唯美主义。
从事写作三十八年来,我一直试图打破散文创作的传统思维和写作技巧,另辟蹊径。后来,终于在探索之中捕捉住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感觉,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就是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和方式,才与大自然亲近了一些,融合了一些。
四十一
朝思暮想的时候,淇河便开始在我的生命深处跃跃欲动,期待着早日能够返回故乡樱城鹤壁。
西北大学图书馆是我课余经常去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当时因为我家境贫困,经济十分拮据,一个月的生活费用80元,母亲攒了很多河南粮票,去北站七粮店托熟人置换成了全国粮票,仅在学生食堂购买饭票就占去了50元。
其他費用的内容相对来说就丰富一些,比如来到大学南路吃一碗羊血泡馍,比如周末去边家村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或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趁周末休息的时间小聚一下,或几个同学约好去学生食堂跳跳舞,感受一下新时代的生活。
特别是每逢周日去学校图书馆阅读这件事,迄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已经被岁月清洗得干干净净,一点印象似乎都没有了。
2020年7月因采风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恰遇当时同租一套房屋的同学秦安江,是他无意中帮我回忆起了那些往事。
他说一个周日去学校图书馆的时候,偶而见到了我。他发现我还带着许多干粮。他一看就知道我又准备在图书馆泡上一天了。
阔别三十多年,今天又相聚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他感慨地说道:“那个时候,你真勤奋啊!”
他说那个时候经常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书,静静坐在紫藤园的条石板凳上看书。每一天都是那么勤奋地写作,直至深夜以后,才会上床休息。
四十二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穆涛同学的写作方式不错。他从学生食堂打来两道菜,搁置在书桌上,一边饮酒,一边写作。后来我也跟着尝试了几次,多打了两道菜,模仿着穆涛同学的写作模式,一边饮酒,一边写作;一边写作,一边饮酒。就这样,不大一会儿,我就已支撑不住了,什么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的,连我都不知道。
当我酒醒过来的时候,天已放亮。
四十三
也许这些事今天看起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屑,但那时却是一本正经的。可以说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司空见惯了。
比如某一位同学手里有一本好书,大家都用十分艳羡的目光看待他。这本书后来在同学们之间传来传去,你看我看,在外面转了很久,这本书才又回到那位同学的手上,当然书还是很新的,没有一页褶皱。
说白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爱惜书。凡是借来的好书,大家都掩饰不住珍惜之情、喜悦之情,仿佛创作上的一道课题,期待着同学们的潜心钻研和攻读破解。
就像一个迫切需要有所作为的人,我为此一直努力着。一旦在追求创作事业的道路上遭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感受到血脉里的河流汩汩而动,那是来自故乡的鞭策和鼓励啊!
这样的感觉始终困扰着我,解读着我,激励着我。
对于我来说,淇河就是创作道路上的一种原动力,而且是清澈的原动力。
这样的力量蕴藏于生命的最深处,从来没有中断过或停止过。即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放弃过。
四十四
我高举着这一条河流,高举着故乡樱城鹤壁,就像高举着一面精神上的旗帜。
这面旗帜既是清澈的,又是生态的,仿佛我的信仰已经在生命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创作上处于成长期的我,面对夭折的初稿,从来没有产生过气馁的想法。日常生活里的困难也从来没有让我退缩和怯步。
偶而焦躁的情绪没有什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否则,就会产生创作上的逆反心理。
关于这一点,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十五
一切文字都会在稿子上波涛汹涌,灵魂深处的波浪冲击着我、拍打着我,一种不可抵御的创作意识铺天盖地而来。
神来之笔的文字力量如果选择了我,我就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一步冲到写字台前。
温馨的台灯光下,迷迷糊糊的我便开始了写作,伏案疾书。
至于写的是什么内容,有时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恍恍惚惚之中,就像梦游一样,文字里闪现出风驰电掣的步伐和身影,其实,那是我日夜在爬格子的真实写照。
就在那一瞬間,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简直无法理喻。
面对一个个文字的突然闪现,我好像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这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性格上刚强的一种体现。
这让我再次确信这种伟大的创作力量就是故乡樱城鹤壁所铺展开的那一面清澈的旗帜,就是淇河在我灵魂深处的一种真实映现。
四十六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困扰我三十多年的梦。
那时,我的家还在鹤山区矿务局北站汽车运输队西家属院。这一天午时,由于我写作时间太长,可能过于劳累吧,就合衣躺下来休息了。
说是休息,其实脑子里还在想着创作上的事,似睡非睡,眼睛始终没有真正合上。就在那一瞬间,一个白胡子老头乘着祥云而来,仿佛一位仙人或圣者。
他见了我哈哈一笑,捋着长长的白胡须说道:“你不是一直想起个笔名么,这么说吧,你的一生先曲后直,先苦后甜,你看看叫曲直怎么样?”说罢,白胡子老头又乘着祥云而去,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顺手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曲直”二字,随后扔下钢笔又躺下休息了。
那一天午时,我坠入梦中睡得很踏实、很惬意。
四十七
至今想起来这件事,我依然不得其解。
那个白胡子老头到底是哪一位神仙?或者是哪一位圣人?期间我查询过很多资料,都没有合适的人选入目。截至目前,对于这件事,我依然处于困惑之中,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当这种机遇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果断地跨入人间天堂,并与仙人直接对话、沟通、交流,于圣人面前彻底敞开心扉。
尽管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奇梦而已,已经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我依然没有忘记。甚至感到这个梦已经化作我的骨髓和血肉。
为了记住这个托梦人,后来我就写了一首诗歌《托梦人》:当我闭目看见一只飞鸟/蓝天白云荡入痛苦/当梦破碎在一页页稿纸上/黄河泰山站立起我/所谓托梦人/用哲学的手指点江山/经典的坎坷/向前的路,很直很直/怕鬼的夜行人/不时看到路尽头灯塔般的传说/传说我就是闭目看见的那只飞鸟/风雨折不断的羽翅/在火把不灭的黑夜里穿行/迎面醒来的不是托梦人/而是我,当思想的笔吮满不幸和阳光!(1995年10月10日夜一稿)
四十八
从此,我便学会了倾听。
倾听淇河的水流,倾听淇河的浪花。倾听河里的鱼儿,倾听水下的植物。倾听远方的太行山,倾听美丽的鹤鸣湖。倾听云梦山鬼谷子的车辙声,倾听纣王殿练兵场上的厮杀声。倾听大伾山佛堂的声音,倾听石板桥下卫河的梦呓。倾听仙鹤腾飞于南山的英姿,倾听五岩山黄昏下的炊烟……
只有学会倾听大自然的一年四季,倾听生态的春夏秋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这些神秘之处都是书本里没有的知识和内容。
四十九
一个时代的责任和担当,决定了一位诗人的眼光。
对淇河的赞叹,也是一位诗人对所处时代的客观评价。从那一首首诗歌的意境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
在别人看不到的许多地方,淇河仍然显示出了令人难忘的神秘之感。
当我的双脚涉入它的意境时,我就懂得一个游子的泪水并非指泪水本身。其实泪水对于一个游子来说,就是酸甜苦辣的心情,就是不停奔波的脚步。
那个时候,我的周身上下几乎都被这种泪水浸透了,感觉所有毛孔里奔涌出来的或渗透出来的,仿佛是大大小小的淇河支流。
由于泪水的冲刷,涨潮的灵感引导着一位诗人,从此步入淇河的神秘之处。
这位诗人,这位沉浮不定的诗人,在淇河岸边寻找曾经的脚印和影踪。大声的呼唤犹如河流溅起的水滴,清澈地滴在每一片叶片上,在风中荡来荡去。
而我就像这一滴水珠,忽高忽低,飘来飘去,在空中寻找着回家之路。
五十
就像有人守在故乡的家门口,一直默默地期待着、守望着,唯恐我找不到家似的。在有关描写淇河的这些诗句中,有些是委婉的,有些是豪放的,有些是直奔主题的,有些是含蓄柔和的。
如果从字面上来分析,这些诗句就像高高的月儿一样,千百年来始终挂在清澈的河流里,挂在望不到边的千年芦苇荡里。
这些诗句时而像青蛙一样跃入水中,不大一会儿又爬到岸上来,蛙鸣四起,就像在诵读淇河一样。
时而跃上芦苇的叶子,眺望着明月,哼起小曲,就像荡秋千一样快乐至极。
时而像浪花一样奔腾,时而像水面一样平静。
时而穿过了清水湾,时而扬起了月花花……
这些诗句里的淇河,好像不是在文字里流淌,而是由许多树木花草组合而成的。名词就像星光一样灿烂、皎洁,动词就像流水的声音一样哗哗而去。
这样的意境在诗人的笔下,当然已经融入一些激情。
有些诗句是诗人的呓语,有些是激情的歌喉。有些诗句是思想的沉淀,有些是灵感的触觉。有些诗句是构思的想象,有些是深刻的感悟。
甚至,有些已经被雕刻在一块块石碑上了。
诗中的主题就像浮雕一样矗立在淇河岸边,矗立在人们的心里,激情澎湃。诗句就像雨中的河流一样声势浩大,浪花飞天。
一阵阵激流冲腾而下,仿佛势不可挡的思念,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离别之情。
五十一
悠悠淇河,乃我生命里的一种期盼和重荷。一想到这些,我对自己的选择更加无愧,矢志不渝。
在苦苦求学的道路上,匆匆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泊在某一个地方,或突然停止下来。或许在前方的某一个地方,遇见的就是这篇文章里的某一个开头,或某一个段落,或某一个章节。碰上的恰好是文字里流淌的淇河。
而生命里的淇河,正是文字里所流淌的、所向往的。
淇河不停地穿过我的生命,仿佛它就是这些诗歌作品的先驱。
我在别人看不到的一个地方触摸着它、感受着它、追寻着它、探求着它。它从来不会被眼泪所迷惑。
淇河的颜面就像绿油油的葉子,漂浮在水面上。
在我看来,淇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有多长、有多宽、有多大,而在于它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是故乡樱城鹤壁的母亲河,是从来不知疲倦的响水河。
从小时候开始算起,这条河流就一直在我的生命里流淌着、流淌着……
它时而超越我的生命,时而思考未来的归宿。它时而浸透我的构思,时而化作优美的诗句。它时而穿透灵感的空间,时而扬起诗歌的风帆……
五十二
在我诗歌转型的某个阶段,写作陡然跌入低谷。
相对而言,那些所谓的写作技巧几乎都已成为空白,一切所学仿佛突然从生命里蒸发掉了似的。平日里最喜欢的事情,现在对于我来说,总觉着毫无意义。
就是这个时期,淇河的水流之声又从灵魂深处回响起来。声音由小到大,渐渐响彻我的周身。这个时候的淇河,仿佛课外的另外一种读本,在文字里流来流去,最终对接上了我的情绪。
若干年后,当我回想起过去的时候,感受到了那时所接触的生活对于今天的写作就是相当好的素材。其中较为深刻的一些印象,当然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了。能够留在回忆里的,至今记忆犹新,栩栩如生。
就像从生命深处涌出来的文字一样,堆在一起就成了奔涌的淇河。回忆快乐而真实,在每一个段落里出现的时候,都像故乡的亲人,纷纷涌现在我的作品里。
如今,在我从事写作的三十八年里,依然没有一件像样的文学作品出现。为此,我经历了几多孤独,几多寂寞。这也是我常常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但不少读者却给予了否定。
五十三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写作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想法。写作这个念头,并没有融入我的生活。
在这之前,我特别喜欢读文学方面的书,小说、散文、诗歌都是我的最爱,古典诗词也是一样,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那时,因为我家距离鹤山区鹤壁集镇新华书店约有五六公里的路程,所以每逢星期天,我就会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后就赶紧徒步或骑自行车赶往书店。
来到书店,一待就是一天。
中午工作人员下班的时候,我就来到街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午饭没有好坏,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随后就坐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等啊等啊,焦急地等待着工作人员的到来。
回到淇县西岗乡迁民村姥姥家里依然如此。早上一醒来,就匆匆忙忙赶往县城老街新华书店。老街书店门面不大,面积很小,柜台上稀稀拉拉放着一些书,各个方面的品类并不太多,比如文学方面的书籍就特别少,还没有鹤壁集镇的那个新华书店的文学书多,但各种各样的书类几乎都有,内容十分丰富。
当然了,那时候购买书籍也是有限的。毕竟我们家里兄妹4个,父母工资有限,每花一分钱都有点舍不得。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站在柜台跟前看书,只要工作人员不撵我走,我就会一直在那里看书。
放假来到滑县四间房乡后马寨村我的奶奶家里,脑海里依然是怎么能尽快找到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不然,待在老家没有书看,就会觉着生活非常枯燥。时间一长,就更觉着没有什么意思了。
在老家总觉着时间过得太慢了,度日如年。
于是,我开始托人打听谁家有书,是哪一方面的书籍。一旦听说谁谁谁家里有文学方面的书籍,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借阅过来。直到离开奶奶家返回鹤壁时,村子里有关文学方面的书籍几乎都让我借完了,看得也差不多了。
五十四
回头再看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新华书店的地方很少。
即使有新华书店,柜台上的书也是零零星星的。有关文学方面的书籍可以说少之更少,几乎为零。在社会上来回传借的都是一些手抄本,比如《一双绣花鞋》等。
一张废旧报纸我都能看上十几遍,翻过来倒过去,哪怕是一篇火柴盒式的小新闻,或者豆腐块式的一篇小文章,或者是在路边捡到散落的几张书页,上面如果是文章的话,我几乎白天看,晚上读,越看越有味道。我心想,要是能找到这本书就太好了,我会一直读下去。就这几页文章,我都爱不释手,更舍不得丢弃了。就像捡到什么宝贝似的置于床头,写作之余就会拿起来翻看,认真阅读。
五十五
曾记着一个单位破产时,图书馆的书籍扔得满地都是。
当我偶而发现的时候,俯身就从中捡了几本文学方面的书籍,回到家后激动地连看几遍,都还嫌不过瘾。可见那个时候文学书籍是多么稀少欠缺,渴望读书的心就像是一头饥渴的狮子,书籍就是我的食粮。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的书籍,比生命都珍贵、都重要。
在文学创作方面,我的写作功底相对来说比其他作者薄弱多了,但我始终不甘心落后于人——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小无名的文学爱好者。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早日趋于成熟,我埋下头来成为了一个读书匠,并期待着某一天能够完全驾驭住所有的汉字。
当时我还在通用机械厂六车间做下料工作,工作期间休息时,我就会躲在摆放成品料的地方,并倚在那里悄悄地写诗——写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
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后来若有一天不写诗,就觉着周身上下非常难受,很不自在。
晚上加班依然偷着写作,下班后回家后还是写作。
后来由于写作太晚了,早上起不了床,八点上班肯定是迟到了。车间支部书记就会给负责签到的人说:“万里昨天晚上肯定是写诗写得太晚了,你帮他签一下到吧!”
期间有一次赴西安进修学习的机会,当我拿着从西北大学寄来的通知书找到厂长的时候,厂长沉吟了一下,说:“厂里只注重产值,不注重培养作家。你若想上学的话,就得自费!”我一气之下离开了通用机械厂,准备踏上求学之路。
五十六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诗,但工作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直到我离开工厂的时候。
就在我准备踏上求学之路的前几天,父母为我准备好了3000元学费,其中二舅卖苹果的钱也给了我一些。母亲怕我把钱弄丢了,就把钱缝制在内裤上。到学校交学费的时候,银行的收银员数钱时说道:“你的钱怎么有一股臭味儿?”
我听了脸一红说道:“天太热,汗臭浸上去的!”
当时没有钱住宿舍,我和同学秦安江就到学校外面村里租了个二层楼。秦安江大我几岁,就住在一楼,我住二楼。
我们在一起相处得还可以。虽然谈不上亲密无间,但也是无话不说。
之前听同学说他在《绿风》诗刊工作,诗写得不错,就很崇敬他,很敬仰他,时不时跟他在一起探讨诗歌写作的问题。
说是探讨,却经常受到秦安江的高度品评。我说我写诗很臭,得好好读书才行。
有时探讨的时间长了,误了去学生食堂吃饭的时间,干脆就自己做饭。安江嫂子郭亚非手艺相当不错,她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炒菜做面条。
现在想起来,总觉着郭亚非那时做的饭好吃极了,味道相当不错。
秦安江那时写的诗已经很成熟,《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绿洲》《西部》已经刊发了不少作品。每当看到给他寄来的那些报刊,我心里羡慕至极。
当然了,有时也想请他帮一下忙,这个想法在那时肯定是有的,现在想起来,依然感谢他。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