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音声
板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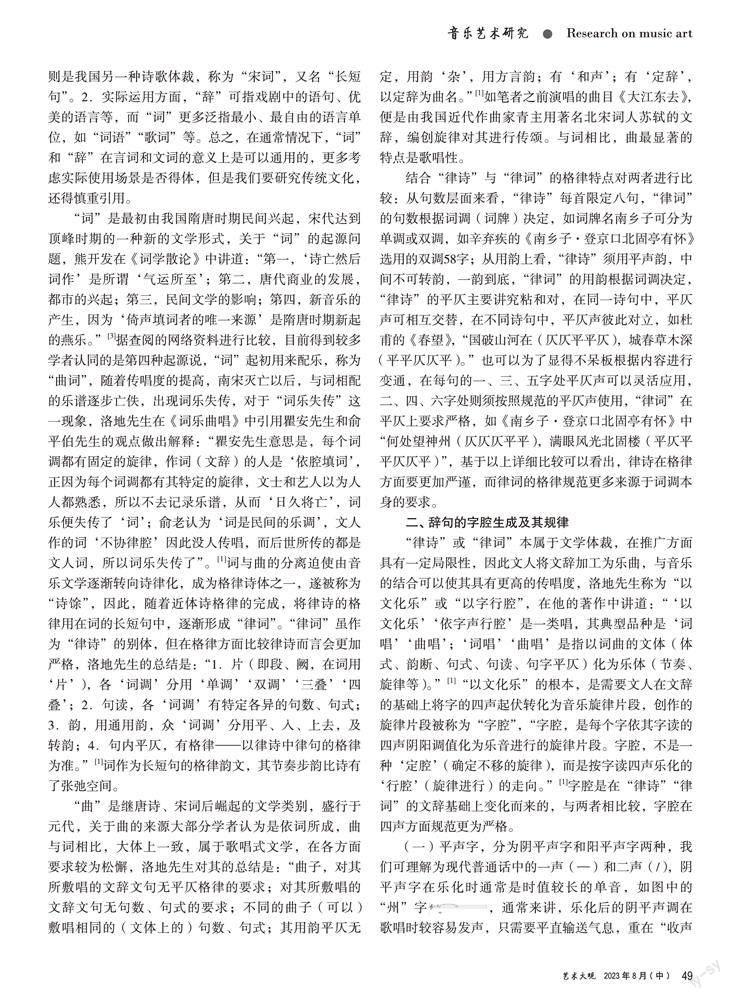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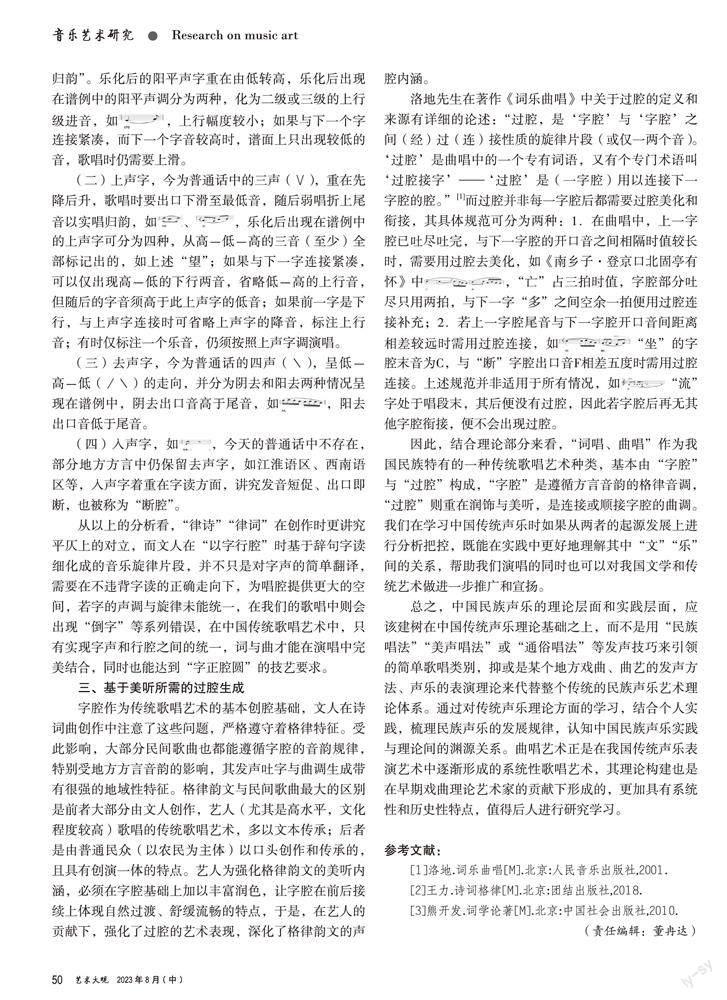
摘 要:中国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篇章,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音乐在不断地衍变,且中国歌唱艺术也在逐渐成熟和丰富。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歌唱艺术本体的整理,从传统歌唱中“以文化乐”一类“唱”入手,探究其采用文本的规范及向乐化时的规律,掌握“词唱、曲唱”的真正核心。
关键词:中国传统歌唱;曲唱;字腔;过腔
中图分类号:J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3)23-00-03
中国传统歌唱艺术是民族声乐的根基,随着历史变迁、民族融合的脚步在不断加快,我们却习惯用民族唱法来替代传统歌唱艺术,导致在演唱中民族风味的缺失,在声乐表演领域中,很少有人专门基于我国传统歌唱文献及理论展开系统梳理,因此需结合歌唱实践,从传统歌唱艺术的字腔与过腔生成及艺术表现出发,探索其基本特征,进而将这些学理性理论运用于歌唱实践,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另外,在我国传统歌唱艺术中,声腔的生成与方言音韵有直接联系,但也不完全是方言音韵及其声调的直接反射,而是遵从基本步韵规律基础上的艺术提升,于是,梳理字腔生成规律的同时,对过腔的强调和关注,便成为传统歌唱艺术研究的新思路。
一、 辞句的格律
恰如洛地先生所讲:“我国一切种类的唱,其构成,不外,文辞字读、节奏板眼、旋律、调——即‘韵‘板‘腔‘调四者。”[1]“我国是‘诗文之邦,自古以来,诗、词、曲,韵文极其发达。无论在哪个方面,包括在体式结构的发展高度方面,‘文远远超过‘乐。总体上,唱中的‘文‘乐关系,‘文始终是主、‘乐为从,文体决定乐体。”[1]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漫长,涉及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诗、词、明清小说,若从发展脉络去梳理讲解,体系过于庞大,所以仅从传统歌唱采用的文本视角去谈论,传统歌唱艺术文本构成主要以诗、词、曲为核心。
“诗”最早是由我国劳苦大众为反映现实社会所创作一种文学体裁,关于“诗”的类别,通常分为“古体”与“近体”,如何辨别两者:从格律上来看,“古体诗”通常指在唐代格律诗问世前的诗歌,创作方面在格律上并不是特别规范,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古诗”或“古风”;近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律诗”为代表,格律方面有严格标准,王力在著作《诗词格律》中讲道:“律诗有四个特点,每首限定八句,五律共四十字,七律共五十六字;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都有规定;每篇必须有对仗,对仗的位置也有规定。”[2]从发展层面看,诗与音乐不可分开谈论,最早的诗是用来歌唱的,如大家熟知的《诗经》《楚辞》都可以配乐演唱,诗乐演唱随着附着音乐的散佚、汉语言文字的成熟及格律诗的盛行所打破,格律诗出现后,以其作为曲子的文辞进行传唱,洛地先生称为“律诗入曲”,这种传唱虽在唐代流行,但局限于部分,更多是追求语言美而以吟诵形式传播,他在《词乐曲唱》中讲道:“事实上,律诗入曲,只是律诗付诸唱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量普遍的是‘吟唱、‘咏诵。”[1]从格律规范和传唱方式两方面都可区分古体诗与近体诗,而诗与词和曲相比,诗的结构比较规整,歌唱性在曲调的发展和音乐风格上因此受到限制。因曲谱的散失和古今汉语字读调值的变化,在今日基本坐实了以文字诵咏为诗,以演唱为歌的观念,诗乐分离也成为一种定式。
很多读者会对标题与正文中的“辞”与“词”较为困惑,笔者从两个角度进行比较性阐述:1.文学体裁方面,“辞”是专指在我国文学史上先秦、汉时期形成的一种新诗体,如大家所熟知的诗歌作品集《楚辞》,“词”则是我国另一种诗歌体裁,称为“宋词”,又名“长短句”。2.实际运用方面,“辞”可指戏剧中的语句、优美的语言等,而“词”更多泛指最小、最自由的语言单位,如“词语”“歌词”等。总之,在通常情况下,“词”和“辞”在言词和文词的意义上是可以通用的,更多考虑实际使用场景是否得体,但是我们要研究传统文化,还得慎重引用。
“词”是最初由我国隋唐时期民间兴起,宋代达到顶峰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熊开发在《词学散论》中讲道:“第一,‘诗亡然后词作是所谓‘气运所至;第二,唐代商业的发展,都市的兴起;第三,民间文学的影响;第四,新音乐的产生,因为‘倚声填词者的唯一来源是隋唐时期新起的燕乐。”[3]据查阅的网络资料进行比较,目前得到较多学者认同的是第四种起源说,“词”起初用来配乐,称为“曲词”,随着传唱度的提高,南宋灭亡以后,与词相配的乐谱逐步亡佚,出现词乐失传,对于“词乐失传”这一现象,洛地先生在《词乐曲唱》中引用瞿安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观点做出解释:“瞿安先生意思是,每个词调都有固定的旋律,作词(文辞)的人是‘依腔填词,正因为每个词调都有其特定的旋律,文士和艺人以为人人都熟悉,所以不去记录乐谱,从而‘日久将亡,词乐便失传了‘词;俞老认为‘词是民间的乐调,文人作的词‘不协律腔因此没人传唱,而后世所传的都是文人词,所以词乐失传了”。[1]词与曲的分离迫使由音乐文学逐渐转向诗律化,成为格律诗体之一,遂被稱为“诗馀”,因此,随着近体诗格律的完成,将律诗的格律用在词的长短句中,逐渐形成“律词”。“律词”虽作为“律诗”的别体,但在格律方面比较律诗而言会更加严格,洛地先生的总结是:“1.片(即段、阙,在词用‘片),各‘词调分用‘单调‘双调‘三叠‘四叠;2.句读,各‘词调有特定各异的句数、句式;
3.韵,用通用韵,众‘词调分用平、入、上去,及转韵;4.句内平仄,有格律——以律诗中律句的格律为准。”[1]词作为长短句的格律韵文,其节奏步韵比诗有了张弛空间。
“曲”是继唐诗、宋词后崛起的文学类别,盛行于元代,关于曲的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依词所成,曲与词相比,大体上一致,属于歌唱式文学,在各方面要求较为松懈,洛地先生对其的总结是:“曲子,对其所敷唱的文辞文句无平仄格律的要求;对其所敷唱的文辞文句无句数、句式的要求;不同的曲子(可以)敷唱相同的(文体上的)句数、句式;其用韵平仄无定,用韵‘杂,用方言韵;有‘和声;有‘定辞,以定辞为曲名。”[1]如笔者之前演唱的曲目《大江东去》,便是由我国近代作曲家青主用著名北宋词人苏轼的文辞,编创旋律对其进行传颂。与词相比,曲最显著的特点是歌唱性。
结合“律诗”与“律词”的格律特点对两者进行比较:从句数层面来看,“律诗”每首限定八句,“律词”的句数根据词调(词牌)决定,如词牌名南乡子可分为单调或双调,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选用的双调58字;从用韵上看,“律诗”须用平声韵,中间不可转韵,一韵到底,“律词”的用韵根据词调决定,“律诗”的平仄主要讲究粘和对,在同一诗句中,平仄声可相互交替,在不同诗句中,平仄声彼此对立,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也可以为了显得不呆板根據内容进行变通,在每句的一、三、五字处平仄声可以灵活应用,二、四、六字处则须按照规范的平仄声使用,“律词”在平仄上要求严格,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何处望神州(仄仄仄平平),满眼风光北固楼(平仄平平仄仄平)”,基于以上详细比较可以看出,律诗在格律方面要更加严谨,而律词的格律规范更多来源于词调本身的要求。
二、 辞句的字腔生成及其规律
“律诗”或“律词”本属于文学体裁,在推广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文人将文辞加工为乐曲,与音乐的结合可以使其具有更高的传唱度,洛地先生称为“以文化乐”或“以字行腔”,在他的著作中讲道:“‘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是一类唱,其典型品种是‘词唱‘曲唱;‘词唱‘曲唱是指以词曲的文体(体式、韵断、句式、句读、句字平仄)化为乐体(节奏、旋律等)。”[1]“以文化乐”的根本,是需要文人在文辞的基础上将字的四声起伏转化为音乐旋律片段,创作的旋律片段被称为“字腔”,“字腔,是每个字依其字读的四声阴阳调值化为乐音进行的旋律片段。字腔,不是一种‘定腔(确定不移的旋律),而是按字读四声乐化的‘行腔(旋律进行)的走向。”[1]字腔是在“律诗”“律词”的文辞基础上变化而来的,与两者相比较,字腔在四声方面规范更为严格。
(一)平声字,分为阴平声字和阳平声字两种,我们可理解为现代普通话中的一声(—)和二声(/),阴平声字在乐化时通常是时值较长的单音,如图中的“州”字,通常来讲,乐化后的阴平声调在歌唱时较容易发声,只需要平直输送气息,重在“收声归韵”。乐化后的阳平声字重在由低转高,乐化后出现在谱例中的阳平声调分为两种,化为二级或三级的上行级进音,如,上行幅度较小;如果与下一个字连接紧凑,而下一个字音较高时,谱面上只出现较低的音,歌唱时仍需要上滑。
(二)上声字,今为普通话中的三声(∨),重在先降后升,歌唱时要出口下滑至最低音,随后弱唱折上尾音以实唱归韵,如、,乐化后出现在谱例中的上声字可分为四种,从高-低-高的三音(至少)全部标记出的,如上述“望”;如果与下一字连接紧凑,可以仅出现高-低的下行两音,省略低-高的上行音,但随后的字音须高于此上声字的低音;如果前一字是下行,与上声字连接时可省略上声字的降音,标注上行音;有时仅标注一个乐音,仍须按照上声字调演唱。
(三)去声字,今为普通话的四声(\),呈低-高-低(/\)的走向,并分为阴去和阳去两种情况呈现在谱例中,阴去出口音高于尾音,如,阳去出口音低于尾音。
(四)入声字,如,今天的普通话中不存在,部分地方方言中仍保留去声字,如江淮语区、西南语区等,入声字着重在字读方面,讲究发音短促、出口即断,也被称为“断腔”。
从以上的分析看,“律诗”“律词”在创作时更讲究平仄上的对立,而文人在“以字行腔”时基于辞句字读细化成的音乐旋律片段,并不只是对字声的简单翻译,需要在不违背字读的正确走向下,为唱腔提供更大的空间,若字的声调与旋律未能统一,在我们的歌唱中则会出现“倒字”等系列错误,在中国传统歌唱艺术中,只有实现字声和行腔之间的统一,词与曲才能在演唱中完美结合,同时也能达到“字正腔圆”的技艺要求。
三、基于美听所需的过腔生成
字腔作为传统歌唱艺术的基本创腔基础,文人在诗词曲创作中注意了这些问题,严格遵守着格律特征。受此影响,大部分民间歌曲也都能遵循字腔的音韵规律,特别受地方方言音韵的影响,其发声吐字与曲调生成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格律韵文与民间歌曲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大部分由文人创作,艺人(尤其是高水平,文化程度较高)歌唱的传统歌唱艺术,多以文本传承;后者是由普通民众(以农民为主体)以口头创作和传承的,且具有创演一体的特点。艺人为强化格律韵文的美听内涵,必须在字腔基础上加以丰富润色,让字腔在前后接续上体现自然过渡、舒缓流畅的特点,于是,在艺人的贡献下,强化了过腔的艺术表现,深化了格律韵文的声腔内涵。
洛地先生在著作《词乐曲唱》中关于过腔的定义和来源有详细的论述:“过腔,是‘字腔与‘字腔之间(经)过(连)接性质的旋律片段(或仅一两个音)。‘过腔是曲唱中的一个专有词语,又有个专门术语叫‘过腔接字——‘过腔是(一字腔)用以连接下一字腔的腔。”[1]而过腔并非每一字腔后都需要过腔美化和衔接,其具体规范可分为两种:1.在曲唱中,上一字腔已吐尽吐完,与下一字腔的开口音之间相隔时值较长时,需要用过腔去美化,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亡”占三拍时值,字腔部分吐尽只用两拍,与下一字“多”之间空余一拍便用过腔连接补充;2.若上一字腔尾音与下一字腔开口音间距离相差较远时需用过腔连接,如“坐”的字腔末音为C,与“断”字腔出口音F相差五度时需用过腔连接。上述规范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如“流”字处于唱段末,其后便没有过腔,因此若字腔后再无其他字腔衔接,便不会出现过腔。
因此,结合理论部分来看,“词唱、曲唱”作为我国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歌唱艺术种类,基本由“字腔”与“过腔”构成,“字腔”是遵循方言音韵的格律音调,“过腔”则重在润饰与美听,是连接或顺接字腔的曲调。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声乐时如果从两者的起源发展上进行分析把控,既能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其中“文”“乐”间的关系,帮助我们演唱的同时也可以对我国文学和传统艺术做进一步推广和宣扬。
总之,中国民族声乐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建树在中国传统声乐理论基础之上,而不是用“民族唱法”“美声唱法”或“通俗唱法”等发声技巧来引领的简单歌唱类别,抑或是某个地方戏曲、曲艺的发声方法、声乐的表演理论来代替整个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体系。通过对传统声乐理论方面的学习,结合个人实践,梳理民族声乐的发展规律,认知中国民族声乐实践与理论间的渊源关系。曲唱艺术正是在我国传统声乐表演艺术中逐渐形成的系统性歌唱艺术,其理论构建也是在早期戏曲理论艺术家的贡献下形成的,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历史性特点,值得后人进行研究学习。
参考文献:
[1]洛地.词乐曲唱[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2]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3]熊开发.词学论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