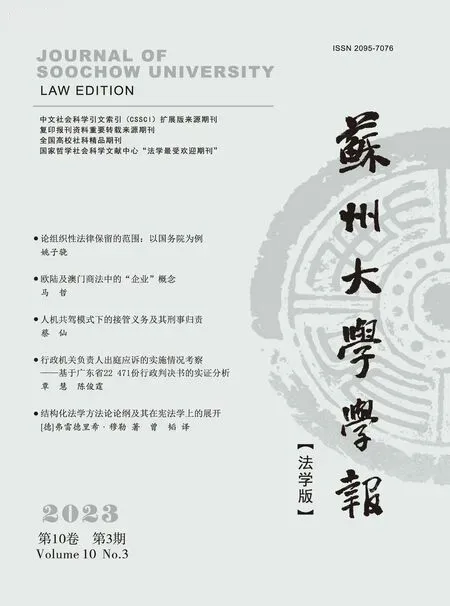论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以国务院为例
姚子骁
一、引言:“组织由法律规定”的现状与问题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组织性法律保留的本质就是法律保留原则在国家组织法中的适用,是指国家机构的组织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正式法律予以规范。现行《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共84个条文,占整部宪法条文数的一半以上。其中,除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两个机关外,宪法对国务院等国家机构都规定了“组织由法律规定”。该类条款所体现出的组织性法律保留(institutioneller Gesetzesvorbehalt)(1)institutioneller Gesetzesvorbehalt又译作“制度性法律保留”“组织法的法律保留”。德文Institution多表达“公共机构”“制度”的意思,因此其形容词institutionell直译成中文便是“制度性”。但“制度”一词在中文语境下所描述的范围并不特指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而是常常被用来描述某一领域的行动准则和规范安排,既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考勤制度”,也同样用于国家宏观体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种直译有损法律语言的准确性,而翻译为“机构”或“机关”又过于具体。从现有的中文语词来看,最贴切的翻译应当是“组织”。故本文将institutioneller Gesetzesvorbehalt翻译为“组织性法律保留”。对宪法和国家组织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它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国家机构,更因为它建立起法律与国家机构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以上述条款为依据,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单行组织法以具体规范相应机构的组织事项。
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并非现实世界中规范组织事项的唯一渊源,甚至不是主要渊源。目前,我国国家机构的调整习惯采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即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调整相应的组织事项,甚至直接通过机构内部的《试点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加以调整,事后再对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以确认改革成果。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跨度内,相应的组织事项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2)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2015年在深圳挂牌成立,该巡回法庭设立的规范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而非《人民法院组织法》。巡回法庭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存在近4年后,才于2019年获得了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9条的规范确认。而在这4年当中,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六个巡回法庭都缺乏法律基础。“组织由法律规定”条款的软弱可见一斑。
除了机构改革对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削弱外,在日常治理中,。以国务院为例,除《国务院组织法》的11个条文以及《海关法》等一些实体法对相关组织事项的规定外,绝大部分组织事项依赖于《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以及各部门的“三定”规定(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作为一部行政法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对国务院的内部组织程序、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工作机制、责任制度等组织事项作了规定。而“‘三定’规定一般由各部门自己拟定,报中编办审查,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办公厅以通知形式发布。”(3)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可以说,“自从1988年以来,尽管‘三定’规定不具有部门组织单行法的名分,但是‘三定’规定实际上扮演了部门组织单行法的重要角色。”(4)张迎涛:《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以“三定”规定规范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各类机构的组织事项也已经是组织法中广为诟病、老生常谈的问题了。(5)参见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张迎涛:《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就已经开始讨论狭义的法律与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职权法定”原则。(6)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以下;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29页。以此为基础,有学者主张“依法组织原则”应为行政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并开始与法律保留相结合。(7)参见姜明安、沈岿:《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组织——论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意义和途径》,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9页;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9页。这一阶段的研究建构起了宏观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内容较为零散,多集中于职权法定。而随着我国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的展开,公法学界对于国家组织的研究,特别是中观层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思考框架,尝试将成熟的法律保留原则引入组织法领域。(8)参见钱宁峰:《论法律保留原则在组织法领域中的适用》,载《现代法治研究》2016年第2期,第30页;王贵松:《国务院的宪法地位》,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220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抽象地介绍组织性法律保留的概念,但对其中的核心问题——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学者们要么忽略了组织法与行为法的区别,将“重要性理论”不经具体化便适用于组织性法律保留;(9)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08页。要么干脆放弃既有的理论积累,提出以功能结构合理化为主、辅以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全新标准。(10)参见王晓强:《行政组织法律保留原则及其保留范围研究》,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5期,第157-160页。本文尝试在法律保留的理论框架内分析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着重阐明哪些组织事项应当保留给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进行排他性管辖,为相关组织法规范的合宪性审查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所涉及的“组织事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概念,大到国家机构的设立、撤销、职权,小到配置办公用品等物质资料,都属于组织事项。然而,这些组织事项绝不能一概而论,机构内部组织的技术性调整和整个机构的拆分、合并显然不可能适用同样的规则。因此,本文将以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为依据,从各种可能的学说理论中筛选出最优解,再借助该理论阐明不同组织事项的本质区别,实现组织性法律保留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并最终建立起国务院的组织性法律保留制度。
二、组织性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法律保留存在着多种判断标准,包括传统的侵害保留说、以其为基础发展出的权力保留说(11)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33页以下。、以民主原则为主要论据的全面保留说以及“重要性理论”。由于组织性法律保留着眼于组织事项,显然不会直接侵害基本权利,明显不契合侵害保留说、权力保留说的理论框架,在此只需考虑全面保留说与重要性理论。同时,所选择的判断标准必须能够契合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法治国家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
(一)对全面保留说的否定
基础政治问题应当由议会亲自决定,因为只有它才是享受直接民主正当性的机关,因此也只有其有权决定政治共同体生活的重大问题。(12)Vgl.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 2.Aufl., 1984, S. 811; BverfGE 33, 125,(158f); 40, 237, (248f).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所具有的民主正当性是一切国家活动的必要基础。因此,纯粹从人民民主原则出发,在不考虑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等其他宪法原则对其限制的情况下,可以推导出国家全部事项的决策都由立法机关所保留。组织事项便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当中。这种理解下的法律保留强调了立法机关在国家政治中的优越地位。由此观之,全面保留说似乎与组织性法律保留最为契合。全面保留说的核心要义是所有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议会法律的依据,其代表人物德国公法学家耶施(Dietrich Jesch)认为行政权已经丧失了其在君主立宪制的时代所具有的特权,变成了纯粹的执行性权力。在议会民主制下,行政权只能依附议会而存在。任何可以由法律调整的国家事务,都应当由议会通过法律予以规范,因为只有议会才能真正地进行决断。(13)Vgl. Dietrich Jesch, Gesetz und Verwaltung, 1961, S. 204.在侵害保留时代,诸如给付行政、特别权力关系等“法外空间”对法律介入的排除,在全面保留说的面前不复存在,甚至还导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任何领域,国家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法律依据,其他国家权力都只是对法律的执行而已。
将全面保留说适用于组织性法律保留,已有实践。我国台湾地区曾经以单行法详尽规定各“部”“会”的任务、决议机制、编制乃至于其内设机关的名称、数目等组织事项。(14)参见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8页。这种近乎全面保留的状态世所罕见,广为诟病。(15)参见吴庚、盛子龙:《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17年版,第148页。然而学界对全面保留说的批评多集中于行政权也享有一定的民主正当性以及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加重立法负担两个方面,(16)参见萧文生:《国家法(Ⅰ)——国家组织篇》,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20页。但前者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只有当最高行政首长亦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时,行政权所享有的民主正当性才可能和立法机关等量齐观。在议会民主制下,行政权的民主正当性由议会赋予,无法反驳全面保留说。而后者则侧重强调实然上的不可能,难以成为规范上有效的论证依据。若要对全面保留说作真正的、宪法规范意义上的检讨,则必须回到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之上。
我国宪法没有片面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的优越地位。为了控制权力、保护自由,宪法将国家权力分配给不同的机关,使其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尽管代议机关产生于人民的选举,具有直接的民主正当性,但民主机制只能承诺“正当”的统治,而无法承诺“正确”的统治,所以人民民主原则并不是不可加以限制的。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突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优越地位。有学者在承认权力分工的基础上,坚持我国所采取的“民主集中制”或“议行合一”是“分权原则的对立物”(17)参见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载《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11页。,也是基于全国人大的“全权”及其优越地位,因而并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对全国人大的权力形成制约。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分工”与“分权”之间并没有如此尖锐的对立。我国宪法第3章已经将国家权力进行了规范意义上的划分,这绝非对“人民主权不可分割性”的否定,而是对国家权力的具体化,是建构国家的必需。无论今后是否再创设新的权力分支,也无论既有的权力分支作何种调整,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并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机构行使,这一宪法秩序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我国宪法的特殊之处并不会否定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只是相较于其他法秩序而言,我国的立法机关明显享有更大的权力,因而使得法律保留的范围得到了相应的扩张,但无论扩张到何种程度,行政、监察、检察、审判等权力也始终存在,宪法中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对于人民民主原则仍然构成限制,进而也会对组织性法律保留产生一定的影响。宪法对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处理,并非是要在议会干预权和行政的自主组织权之间作非此即彼的抉择。相反,它是要在法治国家原则、民主原则以及权力划分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划分两者的边界。(18)Vgl. Christoph Ohler, Der institutionelle Vorbehalt des Gesetzes, AöR 131(2006), S.350.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人民民主原则视作纯粹的立法权一元化,而忽视了宪法秩序下的权力制约与权力平衡。
组织性法律保留偏重于实现人民民主原则所强调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支配,但同时这种支配要受到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的限制,这就意味着,行政权、审判权等其他国家权力分支绝不纯粹是对法律的执行,也存在着需要由其自己判断与决策的事项。这部分事项有些本身就属于组织事项,比如内部人员的配置和事务分配计划等。即使不属于组织事项,基于判断与决策的需要,也必定会对该机构的组织产生一定的弹性要求,以便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全面保留说割裂了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忽略了国家机构依其所行使权力的性质一定会或多或少地进行决策,也就存在需要弹性、灵活调整的组织事项。目前,我国台湾地区也已经放弃了高密度的组织性法律保留。因此,全面保留说不宜成为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判断标准。
(二)重要性理论的阶梯结构
重要性理论是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一系列判决发展而来的。其核心观点是:越重要的事项,就越应当由立法机关亲自以法律决定。即以国家权力所涉及事项的重要性为标准,判断该事项是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1999年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判决该州一项合并原州司法部和州内政部的组织决定违反了德国基本法和州宪法。在判决中,北威州宪法法院认为重要性理论同样界定了组织性决定中保留给立法者进行排他性规范的范围,(19)NWVerfGH NJW 1999, 1243, (1245).并为重要性理论在组织性法律保留中的适用提出了三项具体标准:首先,在基本权利保留领域中,重要性通常被理解为“对基本权利的实现是重要的”。(20)BVerfGE 58, 257 (268).遵循这一思路,如果组织决定对于实现基本权利而言是重要的,则该组织决定应当被纳入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内。(21)NWVerfGH NJW 1999, 1243, (1245). vgl. Krebs in: Isensee/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3. Aufl. 2007, § 108 Verwaltungsorganisation, Rn. 85.其次,如果组织决定对于其他的宪法基本原则,特别是法治国家和分权原则的实现而言是重要的,则存在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必要。(22)NWVerfGH NJW 1999, 1243, (1245).最后,重要性理论可以被具体化为对于保障宪法性机构参与国家领导的重要性。(23)NWVerfGH NJW 1999, 1243, (1245).
该判决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德国公法学家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认为重要性理论在组织性法律保留中的适用在宪法上“既不必要也不合适”(24)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Organisationsgewalt und Gesetzesvorbehalt, NJW 1999, S. 1235.。因为这剥夺了行政权原初获得的决定组织领域内重要问题的职能,特别是考虑到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的结合,将会使一项由法律规制的组织决定只能由法律修改或废止,这无异于彻底剥夺了政府的组织权。即使是那些不重要的组织措施,也会排斥行政的组织权。(25)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Organisationsgewalt und Gesetzesvorbehalt, NJW 1999, S. 1235.他认为组织权的问题应当被置于政治讨论中,议会可以通过干预权进行监督,但并非一定要这样。(26)Vgl.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Organisationsgewalt und Gesetzesvorbehalt, NJW 1999, S. 1236.也有学者认为,只要重要性理论尚待澄清,那么它就只是一项在制度领域具有法律效果的论证概念,而不是可操作的法律原则。(27)Vgl. Christoph Ohler, Der institutionelle Vorbehalt des Gesetzes, AöR 131(2006), S. 345.
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主张在组织性法律保留领域适用重要性理论。因为重要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辅助性地规制行政组织,特别是涉及公民的职权。(28)Vgl. 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0.Aufl., 2020, §21 Rn. 66.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重要性理论存在的缺陷,“法律保留原则适用于组织权领域,但不能将其过于具体化,否则就陷入法律保留制度的历史泥潭中,很难得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29)[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3页。
上述围绕重要性理论所产生的诸多争议主要根源于对其确定性的过高期待。随着现代社会复杂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每一种国家权力都不得不面对日益繁杂、多变、综合的任务,横亘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等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与其说是一道清晰而又稳定的界线,毋宁说是一片模糊、交叉又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过渡带。面对当下日趋复杂的国家与社会,或许应当容忍理论为了增强自身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而保持必要的不确定性。重要性理论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或几个泾渭分明的静态标准,而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关于事项性质与规制密度的动态阶梯:某项事务越重要,对立法机关的要求就越高。从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宪法保留,到重要的事务需要立法者绝对保留,再到较重要的事务需要相对保留,直到不重要的事务无需法律保留,由行政部门调整。“这个阶梯结构不是固定的一阶又一阶,而是缓慢地滑动着。”(30)Hartmut Maurer/Christian 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0.Aufl., 2020, §6 Rn. 14.作为对比,传统的侵害保留说就是一种明确的标准:当国家权力的行使侵害公民的自由与财产时适用法律保留,反之则不适用,这是一种对性质的是非判断。重要性理论所做的判断则是对程度的判断:越重要的事项受到越严密的法律控制。重要性理论所推导出的阶梯意味着它不能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一个于个案中结合具体事实进行程度衡量的参照系。
在重要性理论这个参照系中,具体的衡量要素必须体现出作为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的法治国家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可以认为,对实现基本权利越重要的事项,越有必要保留给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决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性教育课程判决中指出,“一项措施是否重要,是否必须保留给议会决定,或者至少在议会明确授权的基础上行政才能够作出规范,首先应着眼于《德国基本法》。在此,基本权利保障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思考基础。”(31)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其次从人民民主原则出发,则当然地应当考虑对实现民主机制的重要性。政治上越重要的事项,特别是那些事关政治生活与国家、社会秩序的原则性决定,一般而言都满足重要性理论所要求的重要性。(32)Vgl. Böckenförde, Gesetz und gesetzgebende Gewalt, 2. Aufl., 1981, S. 388.因为这类事项通常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需要更强的民主正当性,也就需要通过更多的讨论、沟通和妥协才能够最终形成民意,“基本权利重要性”与“政治重要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33)Vgl. J.Staupe, Parlamentsvorbehalt und Delegationsbefugnis, 1986, S. 127.f.
那么,重要性理论在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具体化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领域内的“重要性”究竟指向哪个概念?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同时体现“基本权利重要性”与“政治重要性”的呢?
三、组织事项重要性的具体化
在组织法中,职权(34)我国组织法中常见的“职权”一词,在德国法上的对应概念为“Zuständigkeit”,通常译为“管辖权”,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资料也通常使用“管辖权”一词。是国家机构的核心构成要素,任何国家机构都必须具有特定的职权。传统上对职权的认识往往是基于其外部效力,即针对诸如公民等外在于国家组织体系的对象所产生的影响,故针对职权的讨论多与基本权利的实现相联系。但另一方面,职权也具有内部效力,即对于国家组织体系内部的其他国家机构的影响。因此,借由职权这一概念,国家机构的组织事项就有可能同时影响基本权利和民主机制的实现。对于组织性法律保留而言,组织事项的“基本权利重要性”与“政治重要性”就不再缺乏标准,而是可以被转化为组织事项与职权的关系,进而使重要性理论在组织法领域得以具体化。
(一)职权的双重效力
所谓“职权”是指“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针对特定事务(任务)的排他性主管权。”(35)[德]汉斯·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0页。一方面,职权意味着特定机构在特定事项上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自然人、法人等相对人必须服从于该机构在这些事项上的命令。简言之,职权就是国家统治权的具体化。(36)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56页。另一方面,职权意味着一种独立性,即特定机构独立地决定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排斥其他国家机构的干预。因此,职权的授予或收回就决定了该机关的存废。原则上,所有国家机构的职权分配应当既不重复也不遗漏地覆盖全部的国家任务,保证每个机构各司其职,形成“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的职权秩序。即使是上级行政机构,一般情况下也应当尊重职权秩序,不得随意代替下级行政机构行使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在“王维军、宋继承诉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江苏省人民政府不履行土地行政管理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决定案”中即认为:“江苏省国土厅虽系连云港市国土局、连云港市赣榆区国土资源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有依法监督其所属工作部门的职责,但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一般不宜逾越职权界限,代替相应工作部门对该工作部门职权范围内事项直接作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37)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647号行政裁定书。
因此,作为核心要素的职权就同时具备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效力。对外而言,职权影响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涉基本权利的实现。对内而言,职权在本质上体现着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着政治重要性,故需要民主机制的控制。当然,国家机构的一些行为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其所对应的职权也不具有外部效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机关内部的部门划分、业务流程规定、人员配置等管理职权。这些职权并不会直接指向行政相对人,因而不具有外部效力。尽管如此,由于这些职权必然涉及国家权力的分配,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重要性,也就必然要受到民主机制的控制。
此外,职权的政治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与公共任务、法律责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履行特定的国家职能,完成特定的国家任务,否则该国家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为了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任务,国家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职权,同时也必须对赋予其权力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任务、职权、责任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反过来说,明确、独立的职权是不同国家机构承担责任的前提。如果某一机构在特定事项上的决定为其他国家机构所干预,不能自主、独立地作出决定,那么该机构就不应当承担此决定所带来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出发,机构的职权也具有政治重要性,必须受到民主机制的控制。
(二)职权和重要性理论
职权同时具备基本权利重要性和政治重要性,对法治国家和民主机制的实现都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在组织法领域,判断组织事项的重要性就必须围绕着职权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一般而言,那些与职权联系越紧密的组织事项就越重要,对其的规制密度就越严格;那些与职权联系越松散的组织事项就越不重要,法律对其的规范就越宽松。以此为标准构筑起组织性法律保留的重要性阶梯,国家机构的组织事项就可以归入不同的重要性层级之中。
1.不同职权的重要性不同
在全部组织事项中,职权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应当受到最为严密的法律调整。国家机构的职权通常都由狭义的法律予以规定与调整,此即“职权法定原则”,该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机关独立行使法定职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干预;第二,未经法律许可,机关的法定权限不得变更与转移。(38)参见林锡尧:《行政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03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职权也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这成为划分法律保留与无须法律保留及宪法保留的核心标准。
首先,一些职权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具有外部效力,最典型的例子是组织管理职权。因此,那些诸如日常办公、档案管理等仅仅为了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职权,不具有外部效力,其重要性低。
其次,某些职权具有宪法上权力分工的重要意义,应当由宪法保留。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诸如国家主席、国务院、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其职权只能保留由宪法调整,而不能通过法律改变。同理,在创设诸如监察权这样的新的权力分支时,即使宪法尚未明确规定,但由于这类职权对行政权、检察权等既存的权力分支会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从根本上改变了现行宪法中国家权力的分配秩序,故也应当通过修宪而非制定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39)参见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3页。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这种创设新的法院类型的国家机构改革也属于宪法保留的范围。参见程雪阳:《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的合宪性制度通道》,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4期,第137 页。
最后,由于事务范围、地域范围的不同,不同的职权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机构管辖的事务范围越大,对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影响也就越大,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重要;机构管辖的地域范围越广,其作出的决定所影响的公民也就越多,其政治重要性就越大,因而也就越重要。
2.不同机构的组织事项的重要性不同
除职权外,组织事项通常包括机构的设立、变更、撤销、组成、工作机制、责任制度、内设机构、编制、内部组织程序以及必要的人员、物资的配备等。而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具有重要性程度不同的职权,这种重要性的差异也会传导至其他组织事项中,因而同一类组织事项在不同的机构中就会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以组织形式为例,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于机构职权的行使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会影响到该机构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尽管如此,不同机构的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仍存在较大差异。审判组织究竟采独任制还是合议制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会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这种组织事项往往被明确规定于程序法之中,原则上不允许变更;但是对于行政机关特别是各部委的内设机构而言,由于它们没有直接对外独立行使的职权,其决策过程受到所属部委的控制,法律责任也由所属部委承担,故其采何种组织形式的重要性较低。
3.同一机构的不同组织事项的重要性不同
在一个机构内,某一组织事项与职权的关联度越高,则越重要,反之则越不重要。典型的例子是对国家机构的运行保障。任何一个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人员和物质保障,这是行政组织科学化的实践要求。但这种结合需要根据任务的不同而进行灵活调整,且与职权的行使之间仅存在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联系。对于这类组织事项,要求实行法律保留既无意义,也无可能。但无须法律保留并不意味着无须受到民主机制的控制,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任免权与预算权的行使对其加以约束。
总而言之,重要性理论在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具体化的核心是职权。越重要的职权,法律保留的规制密度越高;与职权的关系越紧密的组织事项越重要,法律保留的规制密度越高。明确了以职权为核心的标准后,组织事项便可以被划入不同的重要性分类中,形成一个重要性阶梯结构,进而适用不同的规制密度,最终建构起我国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具体制度。
四、国务院的组织法律性保留
截止到2023年,国务院共设有26个组成部门、1个直属特设机构、14个直属机构、1个办事机构、7个直属事业单位和17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鉴于国务院的组织纷繁复杂,且同一类事项在不同职权的机构中显现出不同的重要性,故宜先从机构和事项两个角度,基于组织事项与职权之间的关系,将所有的组织事项类型化,然后再分析其重要性与相应的规制密度。
(一)国务院机构的类型化
国务院机构的类型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方面,国务院机构的内部层级可以提供类型化的依据。另一方面,不同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职权,这也是类型化的依据。
1.行政一体性的层级划分
从行政机构内部的层级划分来看,不同层级的机构虽有分工,但往往出于专业化以及效率原则的目的,在配置内部职权时更加强调一体性。这些机构多采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自上而下地贯彻命令。尽管内部机构林立,对外则是一个统一的法律单位和意志主体。对于强调一体性的行政机关而言,不同层级的机构行使着重要性不同的职权,层级越高,管辖的事务越综合,地域范围越大,决策的独立性越强,承担的责任越大;层级越低,管辖的事务越专业,地域范围越小,决策的独立性越弱,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减弱。
我国国务院的组织机构可以分为四个层级:(40)《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6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行政机构根据职能分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该条例第13条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在职能分解的基础上设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也可以只设立处级内设机构。”
一级组织通常是完整地行使某一个权力分支的机构。其职权最为综合、全面,不仅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范围大,影响程度深,同时还具有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宪法意义,一般直接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因此一级组织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民主机制的实现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本身是一级组织。
二级组织通常是在一级组织之下设立的机构,行使一级组织的某一项职权。相较于一级组织近乎无所不包的职权而言,其职权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民政部的职权实际上是对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职权的具体化。同时,二级组织受到一级组织的领导,并对其负责。另一部分二级组织是所属一级组织的内部机构,不存在具有对外效力的职权。一般而言,属于二级组织的行政机关具有权利能力,能够承担责任,并成为归责主体。因此,二级组织(特别是那些具有产生对外效力职权的外部机构)具有重要性。
三级和四级组织是二级组织的内设机构,分解其职权并具体实施。所有的三级和四级组织都仅仅是负责执行上级机构的意志,具体实施其决定,行使其部分职权,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因此,三级组织和四级组织的重要性较低。
2.外部机构和内部机构
以职权是否具有外部效力为标准,可以将国务院行政机构分为外部机构和内部机构两类。如前所述,能够产生外部效力,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职权重要性高,自然行使这类职权的外部机构也就具有更高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部机构不具有重要性。因为任何职权,无论其是否具有外部效力,都是其管辖范围内国家统治权的具体化。此外,这些内部机构的经费也全部由国家财政供给,其数量、规模也直接影响着公民的税收负担,故而需要受到民主机制的控制。因此,内部机构组织事项的重要性低于同级外部机构的组织事项的重要性。这同样适用于诸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与中共中央相应机构合署办公或由其承担职责的部门,也应该按照其行使的职权分类纳入组织性法律保留的框架内。
以国务院的二级组织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虽然同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但前者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性的,包括“负责组织重大问题的调研”“组织院属单位承担并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报送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信息,反映学术界动态,报送本院重要研究成果、对策性建议”等,(4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机构编制方案》(国办发〔1994〕97号),1994年11月4日发布。而后者的职权包括“制定、发布气象工作的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监督实施”“承担有关的行政复议工作”“审核全国大中型气象项目的立项和方案”等产生外部效力的职权,(42)参见《中国气象局职责》,载“中国气象局”网站2022年4月15日,https://www.cma.gov.cn/zfxxgk/gknr/jgyzn/bmgk/202205/t20220520_4843818.html。因而中国气象局的组织事项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组织事项更重要。
国务院机构中还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机构——审计署。审计署隶属于国务院,属于二级组织,且其行使的审计监督权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属于外部机构。但是审计机关的设立、职权和责任制度均规定于我国宪法当中。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审计监督权及审计署具有超越一般二级组织的重要性。究其原因在于,审计监督权的管辖范围是高度专业化又极为重要的经济事项,包括预算、决算等财政情况以及中央银行的收支情况等。审计监督权事关国家预算的执行和决算,其审计结果报告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预算批准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相比于其他的二级组织,审计署的重要程度更高。(43)关于审计权的独立性,参见王世涛:《审计权独立性的宪法规范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3年第2期,第111页。
(二)组织事项的类型化
除了机构的类型化外,对组织事项本身也有必要进行类型化分析。通常而言,一个机构从无到有,要经历三个过程:
首先是该机构的建制。即通过法律成立一个机构,并确定其法律地位、职权的范围、工作机制、责任制度。这一阶段的机构仅是抽象地存在于法律规范中,虽有明确的任务和职权,但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组织结构。
其次是该机构的建立。即通过内部组织程序、内设机构、职权在内部的分配、设定人员编制、细化工作机制和责任制度等具体事项完善机构的组织。此时的机构,尽管无法实际行使职权,但其行使职权的组织结构已经具备。
最后是该机构的配置。即通过预算和人事制度为该机构划拨经费、配置公务员、分配物资,使其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行使职权。
如果以经验科学的角度观察上述三个过程,每一阶段对于任何一个机构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从规范的视角出发,机构的配置对于职权的影响恰恰最小。设立一个机构当然暗含着人员、经费、物资的需求,但职权的规范性并不会因为上述需求未得到满足而有所损益。而在剩余的两个过程中,机构的建制无疑与职权的联系更加紧密,直接决定了该机构的权力能力。无论一个机构的内部如何组织、分工,都不会对该机构的职权与任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机构的建制比建立显得更为重要。
(三)国务院机构组织事项的重要性阶梯
从机构和事项两个角度对零散、庞杂的国务院机构的组织事项进行类型化之后,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一级组织、二级组织、三级组织、四级组织的重要性依次递减,三级组织和四级组织不重要;(2)审计署的重要性高;(3)外部机构比内部机构重要;(4)建制事项比建立事项重要;(5)配置事项不重要。
将上述两个角度的类型化复合成一个框架,则国务院所有的组织事项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得到分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法律保留的控制密度。
1.特别重要的组织事项
特别重要的组织事项数量较少,但是在宪法秩序中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事项在本质上是权力分工原则的具体化,将国家统治权分成行政权、监察权等若干部分,并建立起行使这些权力的机构。毫无疑问,这些权力会对基本权利的实现产生巨大影响,也都需要接受民主机制的严格控制以获得与其地位相符合的民主正当性。对于国务院而言,特别重要的组织事项是一级组织,即国务院本身的建制事项,对于这些事项,应当实行宪法保留。
2.重要的组织事项
重要的组织事项是国家组织法主要的调整对象。具体包括:一级组织的建立事项和二级外部机构、审计署的建制事项。该类事项应遵守绝对法律保留。
对于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级组织来说,其建立事项对于其职权的顺畅运行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务院的内部组织程序、内设机构、职权的内部分配、总编制数额以及对工作机制和责任制度的细化都属于重要的组织事项。
二级外部机构是指那些隶属于一级组织,能够独立行使职权并产生外部效力的机构。这些机构往往承担着一级组织的部分职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对外管理,并承担法律责任,其建制事项属于重要的组织事项。尽管审计监督权并不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职权,但其对于民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故该职权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因此,审计署的建制事项也属于重要的组织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89条第1款第3项赋予了国务院“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的权力,国务院的二级组织,特别是外部机构的任务和职责显然属于重要的组织事项,该项规定如何与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要求相协调,涉及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基于该原则的要求,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行使的国家立法权和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存在竞合的事项范围内,应当“先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再根据该法律来制定行政法规,将法律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44)王贵松:《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127页。而根据《宪法》第86条第3款和89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国务院二级组织的组织事项恰是处于竞合的事项范围之内,故必须先由法律进行规范,而后才能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加以具体化。如此解释便能使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要求与《宪法》第89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相协调,即国务院的二级外部机构的任务与职责由法律绝对保留,国务院依据第89条第1款第3项所制定的行政法规仅能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具体化;而国务院二级内部机构的任务和职责不属于重要的组织事项,法律可仅作准则性规定,然后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出具体规范(45)实践中,国务院各部委因规范模糊而导致的职权争议时有发生。典型例子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围绕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执法权限而产生的争议。参见程雪阳:《体系解释视角下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执法权限争议的解决》,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0期,第35-36页。有意见认为这种争议应当由国务院解决,并且法律不应该规定国务院二级部门的具体职权。但所争议的执法权限是二级外部机构的职权,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在规范上也由《土地管理法》第77条和第78条所调整,因此该争议毫无疑问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解释予以澄清,而不能推诿给国务院解决,这也凸显了法律保留原则督促立法机关积极作为的面向。。
3.较重要的组织事项
较重要的组织事项包括两类:二级内部机构的建制事项和二级外部机构、审计署的建立事项。这一类事项与职权(特别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职权)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不具备外部效力的二级内部机构,其建制事项在整个国务院机构内部具有权力分配的意义,其遵守相对法律保留即可,可以选择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调整,法律也可以授权行政法规等其他规范进行控制。
4.不重要的组织事项
不重要的组织事项是指对于职权没有规范意义上影响的组织事项。具体包括所有机构的配置事项、二级内部机构的建立事项以及三级、四级组织的组织事项,对此,国家机构可以自行规定,但组织法也可以就这类事项做一般性、原则性的调整。但不重要的组织事项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受到民主机制的控制。配置事项必须符合人大批准的预算以及《公务员法》中公务员的职级、任职条件等规定。

表1 国务院机构组织事项的法律保留阶梯
五、结语
法治国家原则与人民民主原则是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这既决定了重要性理论更适宜作为组织性法律保留的判断标准,也决定了以职权为核心对重要性理论开展具体化的思路。依据组织事项与职权的关系判断其重要性,形成组织性法律保留的阶梯结构,最终实现法律对国家机构组织事项的控制。除了国务院以外,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也同样应当遵守组织性法律保留原则,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要考虑这些机关的职权和组织结构方面的特点。无论是效率方面的考量还是专业性上的优势,都不能够成为国家机构组织事项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理由。
同时,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立法已经越来越难以就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给出确定的实体标准,这使得程序法与组织法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组织性法律保留督促着立法机关对国家机构的组织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理性保障国家机构以最恰当的组织形态履行职责,实现国家目标。因此,组织性法律保留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