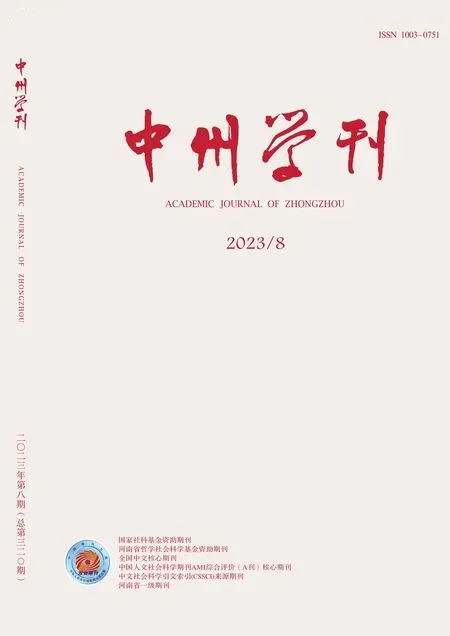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李芳民
长安是唐之都城,也是全国交通的中心与枢纽,由都城长安延展向四方的交通线,大致在长安的东郊、西郊形成两个重要的征行起点,即灞桥与渭城。“灞桥”位于长安之东,是出长安东行、南下与北上的饯行之地;“渭城”位于长安之西北,为唐人西行及西南行的祖帐之所。由于唐人离开长安以东行、南下与北上者居多,故因“灞桥”形成的“灞上折柳”“灞陵伤别”等具有符号特征的别离意象,在唐人诗歌创作中出现频率颇高。相较而言,西出长安的“渭城”意象则显得较为逊色。但是,如果从“渭城”作为诗歌意象的生成演变与经典化来看,其意义仍值得关注与重视。本文拟从“渭城”由一个地域空间到诗歌意象的演变及其在唐、宋的经典化过程展开讨论,追溯这一文学意象的生成与演变历史,并进而阐释其在唐代长安诗路文学意象建构中所具有的意义。
一、渭城:一个蕴含丰厚的地域空间
“渭城”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其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存在,要比其作为文学意象的历史久远得多。“渭城”乃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都之旧地,就使得这一地理名称及其所包含的地域空间,较之一般的地名,更富有历史文化蕴含。
“渭城”之名,与流经关中的渭河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因濒临渭水而得名。在中国历史上,由渭河等河流冲积所形成的关中平原,以山河形胜、物产丰饶而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①,因此它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几个重要王朝的定鼎之地。就其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而言,则是从秦开始的。不过,秦之都城,本名咸阳,自汉武以后,“渭城”之称始有取咸阳而代之之势。至唐代,“渭城”亦兼有唐都城长安之意。经过秦、汉、唐三代,“渭城”这一特定地理场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世事沧桑,不断地丰富着其文化含量,从而使得这一地域空间的内在蕴含愈来愈丰厚。

在秦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其都城也经历多次迁徙。前后所历,分别有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之“徙都汧”,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之卜居“汧渭之会”,秦宪公二年(公元前714)之徙居平阳,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之卜居雍,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之“居泾阳”,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之“城栎阳”[2],定都咸阳,则始于孝公之时。史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3]203。

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3]241。此后咸阳宫殿之营建,更是穷奢极欲。《三辅黄图》称: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
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4]6-7
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应是朝宫之营建,史载: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3]256
朝宫营建,因工程浩大,故先建前殿阿房宫。《三辅黄图》谓:“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4]14据史载,尽管阿房宫可能是在秦惠文王所建宫殿基础上的扩建,但因其豪奢宏丽,至始皇崩殂,犹未竣工。逮至二世即位,复继修之,终致秦之覆亡。
秦亡之原因,贾谊《过秦论》中以为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2237,而所谓“仁义不施”,亦即不恤民力、穷奢极欲,终致“残虐以促期”[3]292。“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5],杜牧之慨叹,代表了后世对秦覆亡之因的认识。
秦以数代之力所建的咸阳城,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但也因秦的暴政而成为天下怨愤之所集。秦末项羽一炬,咸阳之宫阙化为灰烬。咸阳从此不仅成为废都,同时亦成为后人吊古之场域。面对这个昔日既以宏伟壮丽著称,同时又是暴君骄奢淫逸象征的都城遗址,人们留下的是无尽的叹惋与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怀,正如许浑《咸阳城东楼》所称:“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或许缘于秦末都城咸阳的被毁以及人们的复杂情怀,汉人定都关中后,重建新的都城,咸阳之名也逐渐被“渭城”所取代。《汉书·地理志》“渭城”注云:“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为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莽曰京城。”[6]1546《括地志》亦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秦孝公以下并都此城。始皇铸金人十二于咸阳,即此也。”[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更为周详: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至汉代,咸阳之北原,又被选为西汉帝王的陵寝之地。西汉十一帝,除文、宣二帝葬于长安之东外,其余皆葬咸阳北原。自西而东分别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及景帝阳陵。汉帝陵在营建时,亦有徙豪富功臣家于帝陵之举。《关中记》记载:“诸陵……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陵县属太常,不隶郡也。”[9]119《汉书·地理志》亦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6]1642惠帝之安陵营建时,尝“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女啁陵也”[9]110。诸陵中,长、安、阳、平、茂五陵,影响尤大。五陵豪富的汇聚,也使此地风俗为之一变。班固尝谓:“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9]1642而五陵之子弟,多因富贵豪奢而倚势横行。其或探丸借客,作奸犯科;或斗鸡走马,豪侠相尚。由此,“五陵侠少”亦成为渭城特有的标志符号。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之都城,西汉时又因为诸帝陵寝所在而豪富聚集,渭城因此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至唐,因为都城长安与秦都咸阳(渭城)及汉都长安的位置相近,渭城与唐人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当唐代诗人流连往返于这一场域时,渭城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就为其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可供表现的主题选择,唐诗中的“渭城”意象,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的面相。但同时,随着经典作品的传播,“渭城”意象的意义指向逐步向定向化发展,而其经典化的历史亦由此而起步。
二、“渭城”咏唱:唐人的渭城诗与《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
“渭城”成为一个诗歌意象是比较晚的。就目前所见文献看,在唐代之前,仅有一首诗歌涉及“渭城”②。自唐代始,“渭城”在诗歌中才开始有了较多的表现。不过就数量而言,亦不算多。唐诗中涉及“渭城”者,约有20位诗人的诗作26首(两首重出,去其重则为24首)。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唐诗所涉“渭城”意象诗歌及作者表
从唐人关涉“渭城”意象的诗歌来看,其题材内容与主题较为广泛,大致有田猎、送别、酬赠、羁旅、音乐、怀归、怀古、胜地、写景等。这表明,唐人涉及“渭城”意象的诗歌所寄寓的情思是丰富多样的。这一方面与“渭城”这一地理空间原本文化蕴含的丰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诗人因所处情境的差异而引发的感受不同有关。就表现主题意旨的丰富性而言,则首推崔颢的《渭城少年行》。崔诗云:
洛阳三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长安道。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不见家。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桥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10]304
《渭城少年行》属乐府诗,《全唐诗》卷24、《乐府诗集》卷66即收此诗于杂曲歌辞下。但用此题创作者,仅崔颢一人一诗。《乐府诗集》卷66鲍照《结客少年场行》下之解题文字曰:“《后汉书》曰:‘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曰:‘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11]948此篇之后,则有《少年乐》《少年行》《汉宫少年行》《长乐少年行》《长安少年行》《邯郸少年行》等题之作。观此类作品,主题大略相近,因此很可能《结客少年场行》后诸题之作,其题目皆由《结客少年场行》衍生而来。其中的《少年行》多表现游侠少年的慷慨豪迈与放荡不羁,王维的《少年行三首》与李白的《少年行三首》可为代表。在“少年行”之前冠以地名,则以梁代何逊的《长安少年行》为最早,其后陈代沈炯有1首、晚唐李廓有10首。崔颢《渭城少年行》之题名,可能受何逊的影响。不过,与何、沈之作相较,崔诗之内容则要丰富得多。一是崔颢以《渭城少年行》为题,虽不取“长安”,但其所用之“渭城”的地域范围,是一个包含秦之咸阳与汉唐长安在内的大“渭城”,故诗中的景观,既有棠梨宫、葡萄馆,也有长安道、曲江边;既有渭桥与章台,也有下杜与金市。二是其以秦地行人春日思归切入,通过行人的眼光展开铺叙,描绘了渭城春日的优美景色、繁华景象以及五陵少年探丸走马、贵里豪家沉沉歌舞、帝城章台筝瑟娱客、青楼倡家春风卖笑等都市生活场景。三是诗中活动的人物,以五陵少年为主体,突出其斗鸡走马、鸣鞭挟弹、流连倡家、出入青楼的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可谓“写尽当年渭城豪侈冶游情景”(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语)。从主题来看,崔颢此作显然承袭了自《结客少年场行》以及《少年行》等乐府古题之本旨,但他将“渭城”作为五陵侠少的活动背景,并创制《渭城少年行》之乐府诗题。无论是就唐人乐府创作而言,还是从渭城意象进入唐诗歌咏之历史来看,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崔颢此诗虽获得“轻飏婉媚,如游丝袅絮”(邢昉《唐风定》)的褒评,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却不能不让步于王维的《渭城曲》。王之《渭城曲》,本题当作《送元二使安西》③,据题可知此乃送别之作,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中将其题作《赠别》,或即因其内容而简称之。正是王维此诗的出现,奠定了“渭城”在唐代西出阳关诗路赠别乃至整个古代诗歌赠别送行之作中的经典地位。
赠别送行,是唐人诗歌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严羽曾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2]而唐诗中的赠别送行名篇亦多不胜数,但论后世影响之深远,则又推王维之《送元二使安西》为首。从现存文献看,王维此作当时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当与其被诸管弦、广为传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传唱自盛唐始一直赓续不绝,于是“渭城”作为一个诗歌意象,也经由对《渭城曲》的不断传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诗歌创作,成为一个古代诗歌入乐传唱的经典。关于《渭城曲》的历代传唱情况,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一文已有详尽的勾稽与阐述[13]。这里仅在王文的基础上,就唐、宋两代有关《渭城曲》传唱活动中一些重要现象对诗歌意象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略作申说阐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王维诗配乐演唱后,《渭城曲》又或称作《阳关曲》,而二者实同曲之异名,因而以下凡论及后世诗文涉及《阳关曲》者,皆同《渭城曲》视之。
首先,王维此诗入乐谱曲后的传唱与社会影响值得注意。唐诗入乐而被演唱,在唐代较为寻常。《集异记》所载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故事,作为诗歌传唱之掌故,人所共知;诗人李贺,则因长于歌篇,所为“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14]。但是,像王维这首诗配乐之后受到不同阶层的喜爱,及至后世仍在不断地传唱,且引发丰富多样的传唱效应,则是空前绝后的。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此诗所配乐曲之精妙及名家演唱的艺术效果不无关系,而这两者也是紧密相连的。
王维此诗何时、何人配乐今已难以详考,唐人笔记小说中仅略有所及。成书于晚唐文宗大和年间的《大唐传载》曾称:“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15]891而大约同时的《明皇杂录》中亦有相似记录,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15]962二书皆谓王维此诗在开元中已被宫廷著名歌手演唱,只是《大唐传载》仅称《渭城曲》是鹤年最拿手的演唱歌曲,《明皇杂录》则谓龟年、鹤年兄弟不仅为当时备受玄宗顾遇的著名歌手,似乎还是《渭城曲》的制曲者。如此看来,王维此诗很可能在开元中即受到宫廷乐工的青睐与关注,配乐后即在宫中演唱。从“妙制《渭川》”来看,则很有可能《渭城曲》即为龟年、鹤年兄弟所作,或为其中之一④。很可能由于此诗配乐精美动人,又兼有宫廷著名乐工的演唱,故其自开元之后,一直是宫廷乐工的保留演唱曲。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15]794
其次,此诗的传唱构建并确立了一个长安西行赠别的诗歌意象经典。如前所说,王维此诗原题为《送元二使安西》,但是经由入乐配曲演唱,在后世的流传中,其原题则被曲名所取代,后世著录,亦多改此诗名为《渭城曲》或《阳关曲》。《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渭城曲》下即谓:“《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阳关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辞云。”[11]1139清人赵殿成注王维诗,于此诗下也注云:“成按:《诗人玉屑》以此诗为折腰体,谓中失粘而意不断也。唐人歌入乐府,以为送别之曲。至阳关句,反复歌之,谓之《阳关三叠》,亦谓之《渭城曲》。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讴者,善唱阳关无故人词。’又《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诗中辞云。’”[17]
显然,诗在配乐传唱过程中,“渭城”与“阳关”这两个地名作为歌曲的亮点而受到关注,正所谓歌曲之命名,“盖因诗中辞云”也。而就诗歌来说,也正是这两个地名,使此诗作为送别之作具有了独特的意味。这是因为“渭城”在这里不仅代表着京城长安,同时也代表着故乡,阳关则意味着遥远的边塞。在汉代,阳关是中原与西域的分界线。《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通……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6]3871在唐代,“阳关”也往往是塞外的标志性地名符号,出阳关则意味着道途的荒凉、征行的孤独与别离的忧愁。如岑参的《岁暮碛外寄元》:“西风传戍鼓,南望见前军。沙碛人愁月,山城犬吠云。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18]崔湜《折杨柳》云:“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年华妾自惜,杨柳为君攀。落絮缘衫袖,垂柳拂髻鬟。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10]61唐人写及西出阳关、远赴西域的别离之作甚多,但唯有王维此诗,成为表现西行别离之情的经典。王维此诗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渲染了渭城送别的特有氛围,而且情深意厚、含蓄蕴藉,将别离之际道不尽的深情寄于言外。诚如明人李东阳所说:“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19]
此外,诗中所描写的渭城朝雨、客舍柳色的环境氛围,又与诗人创造性地将唐人灞桥折柳的意象融入西行别离情境不无关系。宋人程大昌云:“汉世,凡东出函、潼,必自覇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覇陵伤别’也。王维之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盖援覇桥折柳事而致之渭城也。渭城者,咸阳县之东境也。唐世多事西域,故行役之极乎西境者,以出阳关为言也。既渡渭以及渭城,则夫西北向而趣玉门、阳关者,皆由此始。故维诗随地纪别而曰渭城、阳关,其实用覇桥折柳故事也。”[20]但也正由于王维此诗移“灞柳折别”故事于“渭城”,营造别离之氛围,唐代西行赠别经典的建构才得以确立,而“渭城”“阳关”也成为西行出塞之路的标志性景观意象。
最后,此诗在唐代配乐传唱过程中,因传唱附带产生的故事与人物也值得注意。比如《刘宾客嘉话录》中所记长安邑里鬻饼者,以及宫廷乐工米嘉荣、何戡等,在后来围绕此诗与乐曲的传播活动中,也都成为富有意味的传播符号,为后来诗人相关的创作增添了富有趣味的素材。
三、“骊歌”:赠别意象的经典化与《阳关图》之意味
由于《渭城曲》自盛唐以后百余年的传唱效应,入宋以后,其在宋人的文化生活中仍然有着持久的影响。一方面,《渭城曲》在宋代社会各阶层仍广为传唱;另一方面,王维的原始诗歌文本,作为赠别经典,同样备受文人的青睐。伴随着歌曲的广泛传唱,《渭城曲》及其诗歌文本,在宋人的社交生活、诗歌创作以及艺术活动等方面形成多样的传播面相与效应。而宋代文人以不同艺术形式对《渭城曲》进行的多种回应,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曲》及其诗歌文本的文化蕴含。《渭城曲》的传唱,不仅丰富着文人的日常生活,刺激着他们的创作兴趣,而且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思维活动,启发了他们对送别空间的想象与联想。正是由于宋代文人的相关艺术创作活动,《渭城曲》无论作为歌曲还是诗歌,其意趣也进一步深化。于是,经由唐、宋两代文人前后相继的艺术创作,《送元二使安西》最终被形塑为赠别诗的经典,《渭城曲》也因不断传唱而成为古代“骊歌”之绝唱。
《送元二使安西》对宋代文人的影响,首先还是缘于作为歌曲的《渭城曲》的传唱。有关《渭城曲》在宋代的传唱情况,宋代文人的诗、词、笔记等作品中,都有所涉及⑦。我们可以从宋人刘攽的故事感受《渭城曲》当时的社会影响与文人对此曲的赏爱。范公偁《过庭录》曾记刘攽轶事云:“刘原父知长安,妓有茶娇者,以色慧称。原父惑之,事传一时。原父被召造朝,茶远送之,原父为夜宴痛饮,有别诗曰:‘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至阙,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原父。原父适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原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酒病。’永叔戏之曰:‘原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21]刘攽离别长安时,所宠歌妓送别所唱即为《渭城曲》,而刘攽亦以“白玉佳人唱渭城”的赠别诗句,留下了宋代文人与《渭城曲》的一段颇有趣味的故事。
宋代文人不仅喜听《渭城曲》,而且能唱《渭城曲》。强至《陆君置酒为予唱〈阳关〉即席有作》即有句云:“故人幽怨几时尽,至今愁杀《阳关》声。陆君酒酣喜自唱,坐上客泪俄纵横。”⑧韩维《归许道中二首》其一亦有句曰:“京洛风尘久客情,暂由归路眼中明。最怜杨柳青青色,徐策征骖唱《渭城》。”⑨不仅如此,宋代文人对于“阳关三叠”的演唱方法亦甚有兴趣。苏轼曾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22]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平日对《渭城曲》的关注与喜爱。
不过,从诗歌中“渭城”意象的经典化过程来看,宋代文人在文学与艺术创作层面对于《渭城曲》主题流向与深化的贡献,更值得关注。而这可以从宋人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创作、绘画艺术及连带的唱和之作来考察。
从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来看,由于《渭城曲》的广泛传播,《渭城曲》及与之相关的“渭城”一词,也成为宋人诗歌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符号。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原本为赠别送行之作,但在配乐而以《渭城曲》的形式传播后,其音乐性已对赠别的主题造成一定程度的掩蔽。中唐时白居易所作三首与《渭城曲》相关的诗歌抒发的主要是诗人欣赏音乐时的愉悦与快慰之情,刘禹锡的《与歌者何戡》也重在表现他长期遭贬而重返京城后再闻《渭城》“天乐”的沧桑之感,所以,王兆鹏在分析《渭城曲》在唐五代的流传与传唱时说:“唐五代人熟知的是乐歌名曲《渭城曲》,而不是近体绝句诗《送元二使安西》。”[13]与唐人不同,宋人相关的诗歌创作则再次激活了原诗的别离之意。他们在诗歌中运用“渭城”或“阳关”入诗时,多将其作为抒写送别之情的标志意象,如以下几首诗⑩:
东风未晓放船行,卧唱《阳关》出渭城。老去与人浑惜别,不知何处可忘情。(晁冲之《送韩温父》)
正有寻梅约,今朝此见梅。小停剡溪棹,更尽渭城杯。人物良堪惜,山川会复来。前村风雪夜,归意莫生埃。(陈杰《江头闲行送去客》)
客子明朝早问程,尊前今夜若为情。使君亦恐伤离别,不使佳人唱《渭城》。(戴复古《李敷文酌别席上口占》)
还有一些诗人,则是以“渭城”作为具有符号性意象来烘托诗人的情感。如李复的《白沙驿在归州东江南岸》:
转侧下层巅,江流出断壖。寒云生古戍,野店引山泉。雨暗疏茅湿,堂危倒石悬。去程无限险,心落渭城边。
又如刘敞的《渭城》:
举世几人歌渭城,流传江浦是新声。柳色青青人送别,可怜今古不胜情。
词人的创作情况,也大抵如是。如叶梦得的《醉蓬莱》:
问东风何事,断送残红,便拼归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羁旅。一曲《阳关》,断云残蔼,做渭城朝雨。欲寄离愁,绿阴千啭,黄鹂空语。遥想湖边,浪摇空翠,弦管风高,乱花飞絮。曲水流觞,有山公行处。翠袖朱阑,故人应也,弄画船烟涌。会写相思,尊前为我,重翻新句。[23]
因此可以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不仅继承了王维原诗的主题意向,而且激活了该诗在《渭城曲》传唱过程中一度曾被音乐所掩蔽的赠别意涵,并确立了其抒写别情所具有的符号意象特征。
此外,宋代文人在诗词中运用“渭城”意象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浓度,不仅突出其抒写别情的意义指向,而且注入了浓厚的凄凉与悲伤的色彩,从而把王维原诗蕴藉含蓄的情感表现转化为浓墨重彩的深情抒发。如以下数作:
凭君莫唱《阳关曲》,自觉年来不能悲。(韩维《同邻几、原甫谒挺之》)
离愁自堆积,辄莫唱《阳关》。(郭祥正《螺川送别王公济朝奉还台》)
《阳关》一曲悲红袖,巫峡千波怨画桡。(黄庭坚《送曹黔南口号》)
一曲《阳关》双别泪,百壶清酒两邀头。(洪朋《代饯无为马使君口号》)
休唱《阳关》催别酒,春情离恨总悠悠。(江端本《梦中作》)
萧寺试来携手处,《阳关》已作断肠声。(孙觌《嘉会饮饯爱姬大恸而别》)
三迭凄凉渭城曲,数枝闲淡阆中花。(陆游《阆中作》)
如果说宋人的诗、词创作使王维诗歌中“渭城”意象的意义指向不断稳固化、情感的分量不断强化,那么宋代画家《阳关图》的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题画诗,则进一步深化了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拓展了“渭城”的意义空间。宋代诗、画艺术的交流与碰撞,使王维原诗中的“渭城”意象获得了新的发展。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李公麟的《阳关图》。
李公麟是北宋声名甚著的画家与诗人。《宋史》本传称:“(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其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24]《宣和画谱》中对李公麟的绘画艺术褒赞有加,谓其“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皁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善恶,与夫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妍丑,止以肥红瘦黑分之”[25]130。书中称其绘画大抵“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公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25]131,并记录当时御府所藏其107幅画之名称,《阳关图》亦在其中。所惜者,《阳关图》之真迹今已难觅,所画内容不能亲眼目睹。所幸者,有时人张舜民所作《京兆安汾叟赴临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画〈阳关图〉并诗以送行浮休居士为继其后》一诗存世,而据其诗之描述,公麟所绘之《阳关图》约略可得其仿佛。张诗云:

由张诗中的描述可知,李公麟的《阳关图》从主题、人物、空间场景等多个方面对王维原诗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与展衍,描绘了一幅比王维诗歌所写内容更为丰富的渭城送别图画。其中的画面、人物设计都对王维原诗的赠别主题作了生发与改造,表达了画家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独特思考。也可以说,作为画家的李公麟,借助王维诗歌中渭城赠别的曲蘖,利用《阳关图》这一画作,重新酿出了自己关于人生别离意义的“新酒”,从而也为王维诗中“渭城”意象增添了新的蕴含。其中之意,张舜民可谓深有所会,故在诗中揭示说:“李君此画何容易,画出鱼樵有深意。为道人间离别人,若个不因名与利。”《宣和画谱》也说:“公麟作《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闻其意。其他种种类此,惟览者得之。”[23]131王兆鹏对此有更细致的分析,详见其《〈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图画传播》一文,此不赘引。
如果单纯从送别场景也即“渭城”这一空间意象来看,李公麟的《阳关图》无疑是对王维诗歌的重大改造,大大丰富了王维诗中的“渭城”空间意涵。不过,李公麟《阳关图》中还有一个问题少有人注意到,即此画之画题与其内容的关系。佚名《复斋漫录》曾有这样的议论:
《送元二安西》绝句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伯时取以为画,谓之《阳关图》。予尝以为失。按《汉书》:“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馆在焉。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可也。东坡《题阳关图诗》:“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皆承其失耳。山谷题此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然则详味山谷诗意,谓之《渭城图》宜矣。[26]
从张舜民诗歌中对李公麟《阳关图》画作内容的描述看,画面所描绘的空间场景的确是“渭城”而非“阳关”,但李公麟为何不将其画作命名《渭城图》而题作《阳关图》呢?胡仔是这样解释的:
苕溪渔隐曰:“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旧本《兰畹集》载寇莱公《阳关引》,其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亦以此绝句填入。词云:‘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26]
他认为题作《阳关图》,是受到流行《阳关曲》的影响,而《阳关曲》之名,又源于诗中之语。不过这样解释,或许有点简单化了。其实,画题与画中场景“渭城”之间的矛盾,也许正是画家别有用心处,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使画作更具有耐人咀嚼的意味。人生何处无离别,何处离别不感伤,但“渭城”之离别,正在于它要西行阳关之外,这样,“阳关”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或许正是《阳关图》突出渭城别离之意的独特之处。所以,黄庭坚才说:“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27]苏轼也说:“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28]黄庭坚诗中所说的“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或许正是苏轼所说的“阳关意外声”。
自中唐以降,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赠别之作,历经唐、宋两代的接受与传播,逐渐成为送别诗的经典。在这一过程中,“渭城”与“阳关”始终是此诗最为抢眼的两个焦点。尤其是其中的“渭城”,作为西行出发的送别之地,经过众多诗人与艺术家的接受与再创造,逐渐发展成为别离的经典意象。而因“渭城”与“阳关”在王诗中所具有的呼应关系,人们也顺理成章由此展开了长安西行塞外的想象,“渭城”作为别离意象的特殊性也因此得以确立。近年来,唐人行旅与诗歌的关系备受关注,“唐诗之路”研究因而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渭城”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别离诗歌意象。
注释
①战国时苏秦说秦惠王即称:“秦四塞之国,披山带河,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汉初刘敬劝刘邦都关中,张良亦说刘邦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分别见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42、2043—2044页。②自汉以降至唐前,诗歌中写及“渭城”者,仅梁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其一这一首诗。诗云:“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篸。花舞依长簿,蛾飞爱绿潭。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5页。③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即作《送元二使安西》,并于题下注云:“《诗人玉屑》作《赠别》,《乐府诗集》作《渭城曲》。”见《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全唐诗》亦作《渭城曲》。按,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例略》称,其所见王维诗集“惟须溪评本为最善”,故“是编十四卷以前之诗,皆须溪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见《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可知王维此诗宋本原题应作《送元二使安西》。④不过,“制”之义甚广,既有制作、制造、裁制的意思,亦有“式样”之义。故“妙制渭川”,亦可理解为龟年、鹤年兄弟唱《渭城》,是天下唱此曲之楷式。据薛用弱《集异记》载王维“性娴音律,妙能琵琶”;其科举中第后又曾为太乐丞,故《送元二使安西》之入乐,亦不排除王维自制曲之可能。设如此,则《送元二使安西》之配乐传唱,应始自王维本人。⑤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51页。⑥《与歌者何戡》诗,《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系作年为刘禹锡大和二年初返长安时。⑦关于宋人唱《渭城》的情况,杨晓霭曾有讨论。据杨考,《全宋诗》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诗作近50首,《全宋词》出现的相关的词作130多阕。见杨晓霭《宋代声诗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75页。⑧强至《祠部集》卷三,清武英殿聚珍版藏书本。⑨韩维《南阳集》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⑩下所引晁冲之、陈杰、戴复古诗,分别见《晁具茨诗集》卷七,清海山仙馆丛书本;《自堂存稿》卷二,豫章丛本;《石屏诗集》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景明弘治刻本。李复《潏水集》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敞《公是集》卷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下引韩维、郭祥正、黄庭坚、洪鹏、江端本、孙觌、陆游诗句,分别见韩维《南阳集》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郭祥正《青山集》卷二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琳、李勇先、王荣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3页;清四库全书本;洪鹏《洪龟父集》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四十六,日本元和七年活字印本;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据王兆鹏《〈阳关图〉与〈送元二使安西〉的图画传播》一文,宋代有六位画家曾有《阳关图》之画作。分别是北宋的李公麟、谢蕴文、修师以及南宋的僧梵隆、刘松年和李嵩。该文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又,宋人方岳《深雪偶谈》又尝谓:“渭城朝雨裛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摩诘《送元二使安西》诗也。世传《阳关图》亦摩诘手,遂称二妙。”如是,则在宋人之前,王维亦曾有《阳关图》画作。张舜民《画墁集》卷一,清知不足斋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