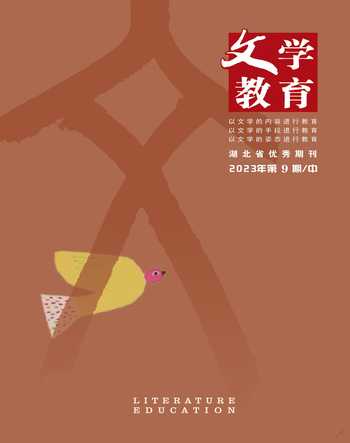反乌托邦思潮下的《沙丘》:科技与政治的危险性
王逸杰
内容摘要:弗兰克·赫伯特作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說“新浪潮时代”的巨匠,在科幻领域久负盛名。太空歌剧作为一种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科幻文学,既有想象中虚拟性的叙事架构,也聚焦现实社会的反乌托邦精神。在作品《沙丘》中,赫伯特通过对“科技乌托邦”与“政治乌托邦”的反对与批判,为科幻写作打开了新视域,在表达他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的同时,给予了每一位读者对乌托邦的思索与体悟。
关键词:《沙丘》 弗兰克·赫伯特 反乌托邦 叙事
美国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1920-1986)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巨匠之一,他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1892-1973)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不可动摇,他的作品《沙丘》(Dune)曾一举囊括“雨果奖最佳长篇奖”与“星云奖”[1]。在《沙丘》中,他将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巧妙地结合当代社会的人文因素,开拓性地塑造了“沙丘”世界。不同于传统的“硬科幻”创作,《沙丘》并不痴迷于科技元素的涉猎。相反,赫伯特在科幻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情感元素与人文情怀,构筑了史无前例的太空歌剧。同时,他通过运用多种叙事手段不断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最终揭开了《沙丘》中人为建构的乌托邦外衣,将其乌托邦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乌托邦的本质与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理想与道德规范实则并不相符,作品警醒每位读者反思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
一.反乌托邦思潮与反乌托邦文学的产生
“二元结构”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核心逻辑,将世界分为两部分的做法,既确定了表象世界,也建立了现实生活的理论模型[2]。“乌托邦”这一理念便应运而生。尽管其为世界提供了前进方向、绘制了未来愿景,描摹了秩序参考,但它的“专一性”和“权威性”为表象世界的运作埋下了隐患。随着基督教对“时间”这一概念的线性设定以及“进步”这一概念的产生,乌托邦开始走向现代化进程。然而,在经历了技术理性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破坏之后,人们对乌托邦的追求逐渐幻灭,反乌托邦思想开始萌芽。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人们理想化的美好世界,摧毁了所谓“技术生活”的愿景。战争使许多人流离失所,并无助地游荡于人性泯灭的现实之中。因此,西方社会的知识精英开始反思和批判乌托邦这一理念、以及科技的无限制发展和权利的膨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现实世界迈向乌托邦的步伐逐渐变缓。反乌托邦思潮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涵盖了哲学、艺术学、文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反乌托邦文学是乌托邦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科幻文学创作的新思潮[3]。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我们》(We)是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它们确定了反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要主题和总体基调。此后的反乌托邦文学主要批评整体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同一性,以维护人类的自然属性,并强调人与人之间个性和独特性的不同[4]。同时,反乌托邦文学对科学主义的发展持谨慎的态度,并用嘲讽的笔触展现对乌托邦理念和过去实践的批判[5]。
过去,社会历史片面的直线上升隐藏着普通人精神生活倒退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引发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人类天真地认为科学是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服务的工具,然而建造乌托邦式理想世界的执念却让科学技术与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削弱了人的精神本质[6]。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作品继承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理念,深刻反思科技发展可能对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并揭示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潜在危险。
二.反科技乌托邦:对科技至上的批判
赫伯特在《沙丘》中融入了对乌托邦理念的辛辣讽刺。科技向人类不同方面的全方位渗透,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却遭到了曲解与误用。在故事的开篇,作者便十分讽刺地交代了其独特的科幻背景设定,即人类在与AI机器人大战后损失惨重,失去了过往的地球家园,在艰难的胜利之后便宣布禁用人工智能,转而借助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具有极高的逻辑推理运算能力的“门泰特”(帝国术语,帝国等级制度的一个等级,也被称为人机)进行决策[7]。这恰恰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伦理观不谋而合,机器人在违背了“机器人三大原则”之后,反噬了人类自身,野蛮的技术增长非但没有将人类送向美好世界的彼岸,反而将人类置于近乎毁灭之中。
赫伯特成功地塑造了恒星帝国这一概念,并指出其是由以帕迪沙皇帝为代表的帝国政府、各个行星的统治家族联盟——兰兹拉德联合会与宇航工会三大势力共同统治[7]。生活在恒星帝国的中所有人都受到三大势力的监视,在可能的反叛与隐蔽的危机矛盾爆发之前便会受到外力干预得以解决。主人公保罗·厄崔迪则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看清了这一事实,认为应当捍卫恒星帝国中各族群的多样化发展,并最终带领弗雷曼人推翻了这三大势力的共同统治。以此,赫伯特讽刺了“沙丘”这一人工乌托邦社会对人性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弗兰克·赫伯特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追求高科技的发展的同时却被科技阉割掉了自由,科技的无限扩张反而阻碍了人类个性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进程。这违背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初心,背离了科学技术的价值,也在最终压制了人性的发展。在赫伯特的反乌托邦文学科幻作品中,他便虚构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宇宙化社会模式,进而描述科学技术在异化的状态下,成为消解人性的异化力量这一事实,人类最终变为单向度发展的人,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文中的哈克南人与走私徒便是其最生动的体现,他们在看到厄拉科斯星的主要产物——“香料”的独特价值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香料的开采与走私贩卖之中,枉顾了这种做法对环境的破坏与对人性的抹杀。在他们眼中,利润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必要时可以不惜环境与人性的代价。
弗兰克·赫伯特对科技乌托邦的批判意识也融入在个体人物的生命体验之中。小说中的杜菲·哈瓦特便是科学技术的推崇者,他盲目地笃信科学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与任何经过所谓“帝国预处理”的人物,相信岳医生的无辜,却未理解杰西卡夫人与雷托公爵之间的真挚爱情,片面地怀疑杰西卡夫人是杀害雷托公爵的凶手,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返[7]。在这个社会中,科学技术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真切情感被否定,个体最终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能力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反而转为了机器结构的特征。
三.反政治乌托邦: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反乌托邦文学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批判极权主义对个体的全面统治[8]。在极权统治者眼中,个体的利益微不足道,他们始终认为自己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符合社会发展的真理。因此,当个体意志置于极权政治下,很容易发生主体性的缺失。肉体监控下,每个人都是被设定成固有参数的提线木偶,而人作为被监督者,只能将真实的自我置于想象的虚幻空间。
独裁作为极权主义的重要统治手段,规训和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所以独裁一直都是反乌托邦文学的讨论焦点[9]。弗兰克·赫伯特在小说中构建了宏大的帝国体系,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人类惯有的权力思维,小说中的帝国设置等同于地球,不同的行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国家,此外,作者也建立了犹如中世纪的古老整体,即皇帝与贵族,并用爵位指代的方式暴露了各个势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使得整个故事背景犹如中世纪一般。
在这种统治方式之下,由于保罗的父亲雷托公爵成为了势力强大的诸侯,已经开始或可能在未来不久威胁帕迪沙皇帝在恒星帝国的統治地位,帕迪沙皇帝便让厄崔迪家族前往他的世仇哈克南家族的势力范围——厄拉科斯星球进行统治。由此不需要皇帝亲自动手,就可以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并解决掉这两股强大的势力,以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与领导权,借以规训恒星帝国中的各大家族,让他们永远忠于帝国的统治,不留二心。
文化领导则是极权主义的另一种统治体现。文化的断层和分化有文化本身质素的原因,也有社会分层和分化的因素[10]。在《沙丘》中,在主人公保罗与杰西卡夫人成功进入弗雷曼族群,并受到“香料”与“生命之水”的影响后,保罗与杰西卡也具备了预测未来与回溯历史的能力,并成为了弗雷曼人的统治者。“他一言不发,记忆里充满了看见的那些东西。他的生活中没有经验和具有预见性的梦幻能使他完全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时间的面纱被突然扯掉,露出了赤裸裸的面孔。”[7]他们分别以“先知”与“圣母”自居,赢得了弗雷曼人的拥护。在这之后,他们便成为了无往而不胜的代表,察言观色,拿捏人心,驾轻就熟,甚至运用预言能力开启掌控弗雷曼族群,以一种不平等的信息流开启了近乎“宗教”形式的统治领导。
四.赫伯特的反乌托邦叙事策略
反乌托邦的叙事主题决定了《沙丘》的反乌托邦叙事特征。真理永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当乌托邦的理念滑向绝对真理的边界,其背后的悖论与谬误便渐渐浮现[2]。赫伯特在他的作品中驾轻就熟地使用了后现代式的叙事策略,以一种非技术化的意境构思揭露乌托邦理念的空洞与荒诞。
1.悖论与反讽的运用
悖论和反讽是反乌托邦文学中的重要叙事方法,科幻作品常常出现悖论问题,赫伯特通过这些叙事技巧,巧妙地拓展了文本的张力,体现着作者思考的思维方式[11]。科幻文本中常常使用悖论问题展现作者的哲思,《沙丘》一书也不例外。
首先,“权力悖论”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它指的是当个体或组织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控制和影响其他人时,他们的权力反而会导致他们失去对他们所控制的人的掌控和信任,这可能导致他们的权力减弱或完全丧失。帕迪沙皇帝的计谋失算便因此而产生,作为恒星帝国的主宰者,他对权力的追求达到了巅峰。对各大家族的打压是他追寻足够权力的过程,却也是导致他失去信任、被保罗率领的弗雷曼军团推翻的根本原因。
其次,“暴力悖论”也是小说中一个显著主题,暴力常常是对抗暴政的最常见方式,但是暴力也常常导致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这一反效果,从而使自由、和平、稳定、发展更加难以实现。在小说的结尾,虽然保罗带领弗雷曼人成功推翻了帕迪沙皇帝与哈克南家族的统治,但是弗雷曼人却陷入了发动圣战的必然选择,这一趋势连保罗都无法挽回,追求自由的弗雷曼人看似获得了厄拉科斯星的统治,却被禁锢于发动圣战这一设定之中,失去了发展的自由。
除上述的两个悖论之外,反讽也是赫伯特常用的叙事技巧,在《沙丘》中,擅长利用环境优势的弗莱曼人虽然拥有在沙漠中生存与开采香料的先进科技,但却始终被恒星帝国视为原始而落后的代表,并不具备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姐妹会虽然以其控制和操纵他人的能力而闻名,但她们却只能将实现自身抱负的期望寄托于育种计划产生的“魁萨茨·哈德拉克”之上。
2.悬念与反转的设定
悬念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叙事手法,用于让读者保持关注并在叙事中创造紧张感。《沙丘》中的第一大悬念就是在厄崔迪家族和哈克南家族之间即将爆发的冲突。从故事的一开始,小说就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强大的派系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另一个悬念则围绕着星球厄拉科斯所含有的宝贵资源——“香料”展开。小说一直在强调了香料的重要性,使读者对其真正的本质和用途感到好奇。
反转是一种叙事技巧,其中预期的结果或情况被颠倒,从而在故事中创造出令人惊讶和常常发人深思的转折。《沙丘》中便蕴藏着多个反转,其一便是哈克南家族与厄崔迪家族之间权力的反转。厄崔迪家族在保罗的带领下成功从弱势的一方成为了新一代统治者。另一个例子便是书中女性角色地位的反转。姐妹会及其成员看似是依托恒星帝国的存在,但在故事的最后却实现了她们的最终目标,育种计划产生的“魁萨茨·哈德拉克”最终实现了姐妹会的抱负。
五.反乌托邦的意义:反思人类发展
在《沙丘》中,赫伯特不仅描绘了科幻的想象,还书写了自己对于人类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他在20世纪中叶开始思考文明演化的趋势,这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那个时期众多的鸿篇巨制。
虽然乌托邦理念为人类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但在实现这种执念的征途上,人类却屡屡陷入困境。高科技的滥用实际上导致了主体和客体的身份转换,科技不再为生产服务,而是消解利益本身。人类追求社会稳定的完美状态,也必然会产生社会的绝对统一性,而个体的差异性则被科技抹去。在极权统治下,人们进入了缺乏自由的监狱[6]。小说中的沙丘世界虽然是赫伯特的想象之物,但它基于人类本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具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指涉性。因此,小说不再是对现实问题的重复摹写,而是关涉对人类现实命运的思考。乌托邦思想在规避人类潜在的幻想和痛苦时,实际上扼杀了人类自我发展的未来。
赫伯特的《沙丘》是一部极具深度的太空歌剧,它不仅仅在文本中引导读者思考,更深入探讨了人类与世界本身的关系。通过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关注,赫伯特的作品提升了文学的价值,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对于完美世界的向往和对神秘事物的探索。然而,乌托邦理念的追求往往会导致对绝对理想的执念,以及对真实性危机的无视,这是值得警惕的。不同于传统的反乌托邦作家,赫伯特并未简单地否定乌托邦理念,而是站在未来潜在可能性的角度,对乌托邦思想进行批判和反思。
作为一部现实与幻想交融的虚构科幻作品,赫伯特的《沙丘》具有客观性和前瞻性,并将科技理性与文学想象完美结合,使得“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被消解。赫伯特通过悖论、反讽、悬念和反转等叙事策略,展现了文本的反乌托邦叙事内涵,并超越了现实,深刻透视了人类自我发展。此外,赫伯特试图通过科幻作品来隐喻现实文明的隐忧,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一个细致而丰富的未来期待。总之,赫伯特的《沙丘》不仅是一部令人陶醉的科幻作品,更是对乌托邦思想的深入反思,以及对未来的超真实透视。
参考文献
[1]王思涵.“黄金时代”美国科幻小说世界的建构.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0.
[2]王超.超现实的现实指向——阿西莫夫的反乌托邦运思与叙事架构.学术交流,2016(06):186-192.
[3]龙慧萍.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
[4]王一平.论反乌托邦文学的几个重大主题.求索,2012(01):201-203.
[5]Vieira, Fátima. “The Concept of Utopi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2010(3): 27.
[6]赵柔柔.反乌托邦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2019,39(01):47-54.
[7]弗兰克·赫伯特.沙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05.
[8]Jameson, Fredric. “Politics of Utopia.” New Left Review 2004(25): 35.
[9]刘丽霞,杨雷.反乌托邦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学术交流,2014(04):183-186.
[10]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11]Rorty, Richard. Contingence,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基金資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美国太空歌剧的反乌托邦叙事研究——以《沙丘》为例”(项目编号:202210287181Y)。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