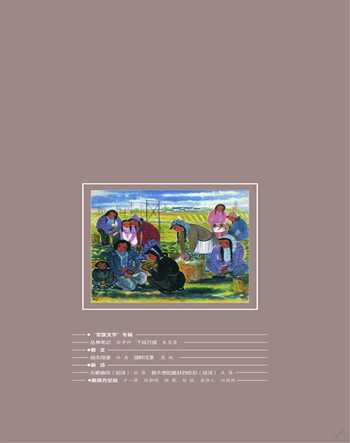南方意识与文学反哺
卢一萍?赵郭明
赵郭明:我发现,近几年你的写作背景正从辽阔的西域往西南、四川——更准确地说,是向你老家米仓山转移。这种转移与你工作调回四川,在成都生活有关吗?
卢一萍:应该无关。在新疆服役时,我也写过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牡丹灯记》;回川后,在成都我也写过以“世界屋脊”为背景的小说,如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名之地》。但我的写作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四川,一直都有西南或南方的叙事背景。
当然,它也只是背景。西南如此神秘、辽阔,更不用说整个中国的南方了,即使我的出生地南江县,我也很难走遍它的各个角落。
一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在信息闭锁的时代,只需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个立锥之地就够了。所以,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还是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样本”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他们都是在写自己的片瓦之所、立锥之地。
赵郭明:去年你在《青年作家》组织讨论“新南方写作”,一个聚会上,我就听说,你在写一部与“南方叙事”有关的长篇。这部作品进度与最初构想,到了哪一步,对你意味着什么?
卢一萍:这部长篇小说叫《少水鱼》,已经写完,正待出版。小说讲的,应该是个纯正的“南方故事”。有30多万字,计5章55节,写了一个家族在百年间的命运沉浮。是一部“亡魂书”,也是事关迁徙、革命与爱情主题的长篇小说。为完成这部作品,我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995年,我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就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但因当时功力不够,所以就没完成。一摞残稿,被我从北京背到乌鲁木齐,再背到帕米尔高原、疏勒,又背回了乌鲁木齐,最后一路颠沛,被我背到了成都。
其间,我好几次都想重写,却不知该如何下笔。但小说中的人物却一直在我心里活着,成长。不寫出来,就令人不安。回四川后,在老家比在新疆方便多了。巴中熟悉而陌生的“巴蜀”或“巴楚”文化迎面而来,给我带来一种神秘的冲击,给我完成这部小说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动力。
写完这部作品是一种“还愿”,在我心里“闹腾”了将近30年的那些人物,终于安静下来。
赵郭明:这是哪个年代的故事?
卢一萍:原来,我想把故事放在1900年到2000年的百年之中,但因太多的历史事件无法绕过,为了叙事的方便,我就把时间设定在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晚清。我后来发现,把时间放在这个拒绝工业革命的洗礼,只顾埋头走向衰落的王朝时期,反而更有意义一些。
赵郭明:怎么讲?
卢一萍:戴托·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问题,无论走向寓言的叙述或充满反思的厘定,都能根据克罗齐的界定,在“过去历史”的镜像中找到与我们有关的东西。
赵郭明:作品的型构,想必就很大了。
卢一萍:李氏家族好几代人,为创建自己的“新唐王国”,从大巴山南麓流徙到长江流域,直至在东海的一座荒岛上繁衍生息,再从类似虚幻缥缈之境的那个荒岛沿着长江远征,最后战败又回到了大巴山南麓——也就是我老家米仓山的丛林里。这个充满魔幻的故事很有轮回感,“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清帝逊位”“联省自治”“辛亥革命”等“前历史”,都有“重述”。我在“西南的南方”和“江南的南方”两个地理背景中,写人为了生存坚持抗争,写他们刻骨铭心的爱和迫于无奈的流徙。我用一个文本,对人在多灾多难的时代无法把控的命运,做出了自己的揭示和思考。
赵郭明:的确是个很有气象的“南方小说”。
卢一萍:以绵实的文字和语态,形成独特的阅读情境,在我看来这是“南方作家”的共性。具体到《少水鱼》的创作,由于它有百年时空和“两个南方”的空间感,我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写作策略,即将流徙故事和地理风光互融,把人物性格与命运抗争并置,让爱情之美与残酷现实呼应;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让人物一起来讲他们与“新唐王国”有关的经历和故事。但读者要从各自的阅读情境抵达小说终章,才会发现这些属于大众史学范畴的讲述,原来却是通过亡魂之口来呈现的。
坚持这个策略,一是可以解决小说的语言问题——因为毕竟不是乡土叙事;我想让语言充满神秘的诗意、南方的个性;但是如非以亡魂之口陈述,就容易与现实产生一种无法拉开距离的胶着感。二是生活中没人听过亡魂说话,也没人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原点,这就给我留下了保持叙事驱力的余地,也能为小说“去同质化”服务。
赵郭明:以你为例,我发现就认识论和经验分享来说,你的书写与其他“南方作家”,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大多数作家的小说场域,大部分建立在自己的南方本土,但你好像不是这样。
你的场域,从早期的《激情王国》,中期的《我的绝代佳人》,近期的《白山》《少水鱼》这四部长篇,还有中短篇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名叫月光的骏马》《无名之地》,相关场域一直都在你的南方本土之外,比如辽阔的西域、地标模糊的都城,乃至内陆亚洲的中心地带帕米尔高原——这样的视域。
那么,区别“南方”或“南方作家”的“南方意识”,这种从不确定到型构建模,与你的从军和求学经历有关吗?
卢一萍:“新南方”的场域问题,更多应该是文学意义上的,当然,它的确也有自己的地理区位所指。但在现在“世界文学”的“中国单元”这个背景下写作,我们再强调地域性可能已没多少实际意义,反而会显得有些狭隘。在南方写作的作家,可能来自北方;出生在南方的作家,也不排除他有北方经历;但有眼光的“南方作家”,一般都不会忽略繁复、温润、飞扬的南方意识彰显;这些南方意识,会让作家的文本具有区别于北方写作的明显风格;我想,这是生存、劳作、风俗、季节、风雨、历史和苦难共同发酵的结果。
我在西北或西域生活了23年,是个拥有“北方观念”,但又具有“南方意识”的复合型作家。我希望将“北方”“南方”集于一身,在创作中呈现北方的辽阔大气,同时又在情节和细节中,融入一些南方的深邃和细腻。
赵郭明:你的“南方意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式样。20世纪90年代,长篇《激情王国》的“南方意识”,是以诗意的洒播,伴随理性思考来呈现的。我记得《激情王国》,写一个朝廷的罪逆集团,根据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主义引领,从中原抵达西域,建立了一个诗意王朝,最后却毁于一句民谣的解构。这种一枚硬币的“两面”之境,从中我们能够发现“理想主义青年”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有作家本体——在历史镜像中的修复与重构。
卢一萍:是的,出于“修复与重构”的需要,2000年,我还写了直到20年以后才出版的《我的绝代佳人》。一个流浪的少年诗人,他一边沉迷南方的情欲,一边心怀失父之疼,在遗忘与怀念、挣扎和沉沦中,开始了他的自我确认之旅。
这个小说,个人色彩比较浓厚。你从比较文学的观察角度,提到了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个我无须否认,但是我想说,这是我写得最富“南方意识”的一部作品。
赵郭明:这个阶段,你的“南方意识”是饱满的,也是游弋的,小说主题,和存在与虚无的个人思考有关。直到2017年,随着长篇《白山》的出版和井喷式发表、出版的一批中短篇小说,你的“南方意识”与人物互洽,才指向了“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内陆亚洲的庞大背景。那么,从不确定的诗意弥散到内亚疆域的清晰印痕,这对你书写能力的提升和叙事可能的扩充,是否具有相应的指涉?
卢一萍:用“南方写作”来概括我的创作,也是不全面的。但有意思的是,长篇《激情王国》作为我20世纪90年代的习作,带有当时还不成熟的实验性。文本揭示了人类理想的脆弱与诗意进入俗常经验的危险,由一个接一个的破碎梦境拼贴而成。这是“南方意识”的“南方”——相对北方的他者,自古就有其破碎和梦魇元素,以及你提出的“诗意洒播”,和我这个当时在北方求学的南方文学青年产生的对冲。
这个小说培植了我的文学元气,开始发在《芙蓉》上,后来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这种幸运,给我带来莫大的鼓舞,它使我借助其驱力,接着又写了《我的绝代佳人》。《我的绝代佳人》这部长篇,仍由多个梦境拼贴而成,但文本的情爱和诗意表达虽然变化不大,相关的痛苦或苦难的主题确认,却已显露出了北方他者介入的粗粝感。
当时,我之所以总写梦境,是因我对现实还不具备理解和批判的能力。但日有所见、所思,夜有所梦、所现,梦境也是现实的一种,因此,这一时期的梦境书写,也不能说它全部就与现实生活无关。
到了写《白山》的时候,我已历尽沧桑,对人与世界有了认识和理解。我認为自己可以走出梦境,直接面对现实了。《白山》是个西北方向的“北方故事”,至少它的地理元素,是有中原农耕文明之外的内亚性的,但我却在这个“北方故事”中贯穿了我的“南方意识”。比如在作家本体意识的凸显上,无论幽默、荒诞、情爱和环境书写,这些都与我依赖的西南“立锥之地”,即南方的生活阅历有关。
赵郭明:20世纪90年代,你的“南方意识”是在苦难与传奇和反传奇的文本中激扬;本世纪以来,又在“南方意识”彰显的“历史和新历史”“批判和寓言”的互为指涉上着力,以几部长篇和你的中短篇小说人物塑造为例,能谈一下你的创作经验吗?
卢一萍:在我看来,我写的国主陈六儿、流浪的诗人、戍边的军人凌五斗和误入“一杆旗”——这个地方的农垦女兵刘月湘,他们的形象和命运,之所以能在“南方作家”文本中形成偏颇与极致、真诚和荒诞、粗粝与细腻的异质,我想经验上,可能真的也没有什么可谈。但我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我体验到了,理解到了,我写下了;在这三个层面,我如实写了我的人物,也不知算不算是经验。
以陈六儿、凌五斗、刘月湘为例,他们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活着或消失的人。只能在那种场域,那种语境出现。但这些人虽然活动在以帕米尔高原为背景的内亚区块,身上的匪气、敏感、执拗、多情或淳朴的底色,实际在我家乡——对一方儿女——甚至对我本人的哺育上,又不难看到他们和西南“南方意识”的理论自洽。
赵郭明:你的创作,在我看来,一是具有可贵的域外背景,二是形成了“南方意识”从游弋不定,到落地内亚区块的蓬勃茂盛。那么,基于作家伦理的哺育与反哺逻辑,你能指认“南方作家”对域外经典作家和地方知识可能形成的影响吗?
卢一萍:这个问题很好。依我拙见,稍微具备一定水准的作家——他们背后都有域外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影子。但在接受域外作家和作品影响,乃至他们对域外作家也能形成影响的确认上,不少人要么半途而废,回到了传统的庇护所,要么只写一些应景之作,干脆放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目前,只有北方作家莫言、阎连科等还在坚持文学的哺育与反哺伦理,仍在布迪厄描述的“专家城邦”里工作;南方作家只有阿来、韩少功、残雪等为数不多的前辈,还在一条几近荒凉的路上砥砺前行。
如在拥有“南方意识”和世界经典意识的作家中,非要选择一个识别的样本,我认为,阿来、韩少功和残雪的文本价值追求是成功的,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南方意识”和域外经典在影响他们,他们也在影响“域外”和“南方”。他们可与当下文学审美形成差异化的样本,无疑正是仍然走在远征路上的我,需要抵达的方向。
赵郭明:这次感觉还是聊出了一些东西。问一个用来结束这次聊天的问题,你接下来的写作方向是什么?
卢一萍:我积攒了很多素材,我有不少想要表达的主题。我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会一直看着前方的路,一直往前走。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