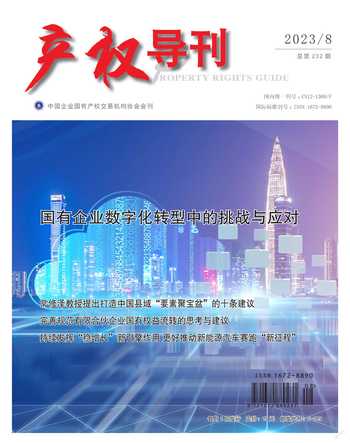刷新生活图景的数字经济
李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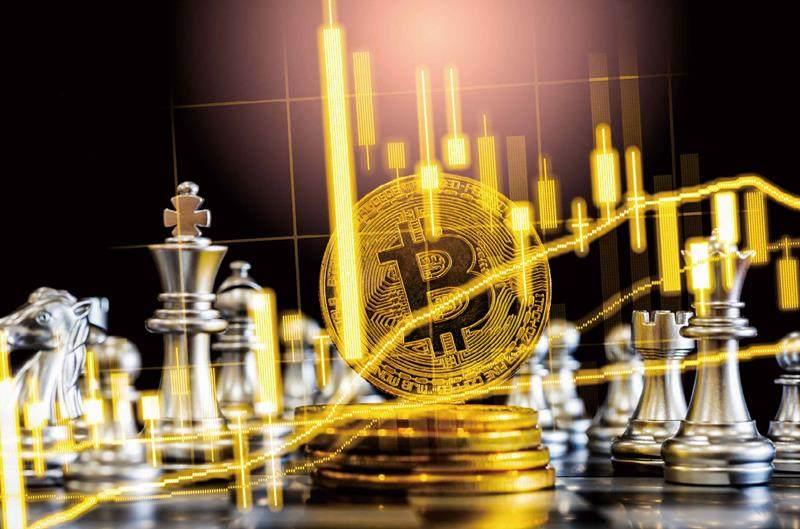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生活中,数字应用相当广泛。我们熟悉的是“十进制”自然数。但自从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发展以来,我们才发现,其背后有别于“十进制”的“二进制”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已经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在描述今天的时代时,要冠以“数字化”了。相比于“十进制”自然数的“显性”特征,那么,“二进制”则可以称为“隐性数”。今天,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显性数”与“隐性数”并存的数字化时代。“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作为最重要活动方式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数字经济”,我们历史地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
今天,我们把哪个节点算作数字经济的起点?第一台286计算机出现在一个用惯了自来水笔的作家书桌上的那个时刻?甚至谍战片里频繁出现的那台神秘的发报机的时候?抑或是尼·葛洛庞帝写出《数字化生存》的那一年?还是淘宝开市、京东面世……?这场纯粹技术领域里的变革,早早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数字化浪潮,党和国家高屋建瓴,未雨绸缪。至少从1999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中国证监会国际互联网站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就开始出台相关的法规,从各自职能的角度,逐步规范包括信息发布、技术规范、经营场所、内容管理、连锁经营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更是把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因此,本质上,数字经济与人类其他经济形态的活动没有区别—供需双方以及供需方之间所需的各种桥梁、为其实现而形成的配套要素等等。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传统形态的市场经济活动有相当部分已经靠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了,与此同时,还包括了数字化手段自身即用数字化手段实现的数字经济行为——它包括了与实体店分庭抗礼的电商、起步就依赖信息平台的产股权交易以及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的数据流通交易——而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将可能是市场经济在当前生产力背景下的最高形态。在其之下,则是数据流通交易,再往下,则是数据产业生态。可以想象,在不远的未来,譬如五年,我们就会生活在全覆盖的数据产业生态之中。这如果是选择的结果,也只能说是人类社会生活在发展规律之下选择我们(人类)的结果。
任何事物之间及其发展都不可能是割裂的。在数字经济中,经济实体当然不会缺席,也不可能缺席,但显然会日渐式微,越来越成为类似于供给基地或展示窗口。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必将成为助推实体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引擎。从现在技术趋势和发展思潮看,最终,电商类的“平台经济”只能是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比较初级甚至是“低端”的资源配置、商品交换的方式,它虽然不可或缺但也是外强中干。人们愈发依赖它,但却不会给它一个类似“以食为天”那么高的地位。今天,当人们穿透实物、实体,看到物流、支付、配置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更加便利地实现流转与管理功能之后,“初低端”的数字化经济形态就将不能满足部分人进而是整个社会的需求了。靠电商平台崛起的阿里巴巴前掌门人的马云已经在说“阿里过去那些赖以成功的方法可能已经不适用,应该迅速改掉”了。
我们知道,为了调节资源要素的公平配置,产股权交易悄然登场,如同一棵不被注意的小草。作为早期以柜台交易为雏形的一种经济方式,“产权交易资本市场随着国企改革推进而诞生,是中国独创的经济模式”(《新时代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企业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机构协会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23年3月第1版)。它可以说是中国本土诞生、养大的一个市场。它不是“中国化”来的,而是“中国式”的。而它从诞生之初就直接靠上了互联网——可能除了马云最初向往的网上黄页电话,它是中国最早依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行业之一。甚至比各级政府的官网还要早,更不要说更晚的微博了。制定交易规则、平台管理规则和项目多维标准处理流程、逐步减少人为干预,上线智能化审核和操作流程,推动交易全流程在线完成,建立高效电子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智能平台,逐步衍生成为数字经济的先行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品”消灭了“山一程水一程”的长途跋涉,通过比特进行传输。对于习惯于“实体经济”的大脑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当我们说“产品”时,人们首先可能需要你回答它的长宽高等物质形态。但“数字产品”却只有KB、MB、GB这样肉眼无法感知的计量单位。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要让人们相信的是:数字产品是真实存在的。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非常像我们早期用DOS时的状态。
中国早期的电脑初学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视电脑为畏途。在他们看来,把一个现实世界“翻译”成一个“虚拟”世界,或者一个“虚拟”世界“引渡”到现实世界,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可是如今,哪怕一个三岁的孩子,无需更多教育,却可能无师自通地伸出一根手指,自如地拖曳光标或者点击菜单,操纵多种智能电子产品。是这代人比那代人更聪明吗?其实未必。数字经济中的数据交易真的会比我们在农贸市场上买一只土鸡或者在超市里买一袋大米,再或者,比在淘宝上买一束鲜花更难以理解吗?数据交易的本质是场景化的数据合理合规应用。它们往往具有工具的性质,而不是如同一筒抽纸或者一杯酒那样的直接消耗品,但最终依然是“有买有卖”。不管是鸡、米、鲜花,还是数据产品,它们都是可交易“标的”。现在,它们一如既往地因各种需求而通过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媒介)进行跨时空的流转,完成了我们用惯了的流通、交易、收益分配诸环节。
数字经济有多少种呈现方式?电商、APP、支付、共享经济、数据交易、数字货币,这些经历数字化迭代后的不同产物,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不要误解,其实这不是全部,只是冰山一角,還有针对B端、C端的各类服务以及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为这类活动提供的算法服务、算力服务、数据服务。
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有一些行业必定会退出舞台——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死掉”的,而是从空间被逐步压缩开始,就像我们常说的那种“垂死挣扎”,其中,依赖特权或关系维系经营发展的那些“灰色行业”将会是首先被“解决”的。这类行业既破坏市场公平原则,又污染社会正义风气。如今,90后作为由互联网养大的第一代人,已经登上社会生活舞台。除了偏远的山区、农村、海岛,哪怕是四线小城,90后们也基本上和各种类型的“网游”相伴而生。网络就是他们的“江湖”。在他们面前,讲关系和圈子,就不如讲平台更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数字更客观,互联网更公平,数字经济也似乎对利用现实关系拉拉扯扯颇为不屑。在铺天盖地的自媒体的短视频上,成为网红与否,与up主可能存在的、隐藏着的那个特别的现实社会关系不构成直接关系。一个草根,藉由某种机缘也会实现10万+的效果,成为流量明星。董宇辉横空出世、“挖呀挖”的黄老师突然来到,他们的成功,更让90后们坚定地轻视“特权”和“关系”。即便人们不喜欢却很魔性的“炒作”之手,也开始被迫“尊重”互联网的规矩——重视网络的力量了。在网络世界这个公共空间上,所谓的“任性”和“野蛮”,都会被视为“脑残”和“进水”行为。“特权”当然还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但数字经济一定不想继续喂养他们了。终有一天,他们必定被逼进一个逼仄狭窄的空间,如一只老鼠被猫逼进墙角。他们甘心退出吗?似乎不会。这是人类社会一诞生就存在的一个“物种”,与人类如影随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数字经济浪潮中,他们也会变换姿势,持续学习更新并且跟上数字化步伐——还远远不止于此,他们自己也会“数字化”起来。至于具体方式,虽然打一个电话、批一个条子越来越没有了用武之地,但他们会以影响和干预各种规则为主,以偷梁换柱为辅,试图瞒天过海、暗渡陈仓。他们会比过去更提前开始了“运作”,把功夫下在了“源头”上——比如,产权交易,进入平台后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可以在交易行为在进入平台之前,从确权、评估等前期环节进行干预。但,今天的管理者已经“百炼成钢”,练就了“火眼金睛”,会反复发出“温馨提示”:绝不能忽视数字经济中“人性恶”的部分的变脸登场。有时候,有人会对银行APP的层层密码、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滑块感到繁琐,岂不知,电信诈骗、AI换脸等等从某些地方发出的危险信号,已经来到我们面前,正准备或者已经开始敲打我们的生活之门了。对此,“全覆盖零容忍无禁区”的枪口,自然对准了这个战场。而在實操层面,“严防死守”的态势已经形成——产权交易本身,就是一场对“暗箱操作”的“自我革新式”行动:阳光下规范交易,让“灰色地带”无处藏身。当然,仅有“自我革新”还不够,必须能够来一场“斩草锄根”或者“自断后路”式的“自我革命”。而这场“自我革命”的序幕则已经由区块链、智能AI、数字货币拉开了。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各种要素正在变成一个运动着的链条上的一环或者一个单元——这个链条通常被称为“供应链”,而担负市场配置功能的交易平台更想称之为“交易链”。不过,这一“大胆的想法”并没有推广开来。尽管与“供应链”相比,它的确把数字经济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方式描述出来,可能也正是因此,导致一些业内人士回避了这一称呼,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微利”害羞地称为“服务”那样。
如果认为数字经济改变的是“更快”的问题即单纯的效率问题,那就是低估了“数字化”的影响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一定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在“提质增效”的同时,正在逐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破市场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产生的“隔断”,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推向更加充分的状态,使之“满血”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进一步深化的社会分工、应用创新、市场扩容的新的发展格局中,严重影响公平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性、地方性的产业政策等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系列痼疾,被政府和市场共同“清算”,统一的市场格局呼之欲出、应运而生。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不管其在供应链链条的哪一环上,都同频共振、同步运转起来,整个社会的高度协同性越来越强。在不动声色中,数字化转型开始由“效率变革”转向了“价值变革”。
数字经济的发展支撑,来自于数字技术。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其他科技发明带给我们的幻想,比如电的发明,有了一拉开关就亮的电灯、一拨号码就听到远方声音的电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几乎成为一代人最高的生活向往。一度,人类是不是觉得已经到了知识的天边?
今天,数字技术的发展依然让人想到:我们会不会又一次站到了人类认知的“天花板”?我们还不能忘记的事例就是,当微博这种方式火遍全网的时候,一些政府部门迅速跟进,以规范文件的方式强调和要求基层单位把微博当做“问政”平台。那时,人们没有想到自媒体会出现,没有预料到官民平等的抖音、快手、小红书会出现。当我们享受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红利或者福利的时候,一定能清晰地知道:人类社会从来不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停下求变求新的脚步,它将不可置疑地按照螺旋上升的法则继续前行。新的需求总在无止境地催促和召唤人类向前、向前、再向前。
现在,我们必须坚定地明确的是,数字经济首先是一场思维革命,然后是思想革命,是到目前为止认识论和方法论最高级的实践范本。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更迅捷和更剧烈。本质上,我们依然是生活在供需的法则之中,商品经济的全部规律还主导着社会经济生活。数字经济首先改变的是各种模式、方法、渠道、手段。这些效率上的变革,正在酝酿着对生产力的新一轮的反作用,高调地向价值变革转变。从小到市井的生活方式、大到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理念,数字经济的影子已经无处不在。它甚至比任何一次激烈的暴动带来的变革和影响要深远得多、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再一次证明:科学技术革命具有更胜一筹的先进性。无论是社会管理者还是社会成员,都平等地向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大程度地“让渡”旧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相比揭竿而起的革命,不仅没有硝烟,更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有的生产力,以跨步攀爬台阶式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洗礼。但,科学技术革命也并不是“零成本”的。比如,一些实体店的凋敝、部分传统产业的门前冷落、低端劳动力的过剩……代价也不可小觑。但相比于宏大的、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这场革命为个体提供的便利和幸福、为整个社会提供的生产关系的优化等——或者说,全社会从这场深刻的变革中获得的幸福感,其代价与影响的性价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优良率最高的一次革命(包括工业革命)。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持续夯实的“数字底座”、不断丰富的数据资源、日臻完善的数据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正如曹兴信所说“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抢占数字时代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正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规律,穿过人类生活。人类从实践中获得了灵感,这些灵感又反过来令实践更生动和丰富。“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数字经济启示我们,我们还需要更高智慧、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坚定的信心,持续刷新我们的生活图景。
(作者为广东省交易控股集团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