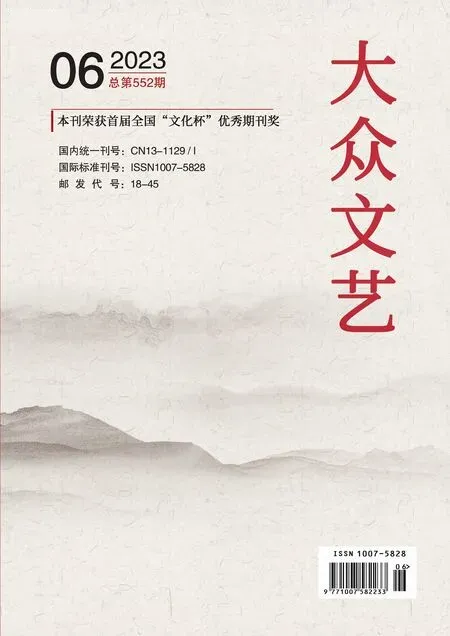空间理论视域下殷若昕电影的叙事空间建构
于 航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随着《我的姐姐》的上映,中国新锐女性导演殷若昕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之中,影片在获得高票房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我的姐姐》中深刻社会议题的讨论。自话剧科班出身的殷若昕对电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将镜头对准了社会现实,影片包含了原生家庭、伦理价值、人物困境等等话题。她把电影的第一帧、每一帧都当作自己的热爱,于是便有了《我的姐姐》和《再见,少年》的呈现。《我的姐姐》的故事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一则关于姐姐的网络热帖,此帖当年一经发出便引发热议,有人强烈指责姐姐违背道德、丧失天良,也有人感叹自己应该与贴主一样选择属于自己的道路。正是如此,影片《我的姐姐》讲述了主人公姐姐安然于父母意外去世后,在梦想和现实、自我与血缘之间困难抉择的故事,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另一部作品《再见,少年》则是一部关于青春与友情的史诗,故事以导演自身经历为灵感,讲述了两位少年从无限接近到逐渐远离的故事。当代国产电影的发展离不开电影人不断的全新尝试,也离不开雨后春笋下新锐导演的努力。导演殷若昕洞察当下社会议题,结合自己独特的电影见解与热爱,凭借两部影片在电影行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电影中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要依靠着影视的空间所存在。影片的空间是银幕体现的基本空间世界不能离开影片的叙事和主题,电影中的空间既是主题的载体,又是叙事的环境,既是影片的视觉风格,又是影片的造型风格,所以电影中的空间有很大的表现性和象征意义。[1]列斐伏尔认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导演殷若昕在两部影片的空间建构独具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人物命运书写物质空间;以构图、音乐和道具构建社会空间。本文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为依据,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层面出发,探究殷若昕导演电影的叙事空间建构策略。
一、人物命运书写物质空间
环境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电影叙事空间建构首先是对主人公的选择,然后运用现实空间进行人物心理空间的刻画,进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2]物质空间即电影中人物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殷若昕导演在两部电影叙事中构建了相对封闭的物质空间:一方面,剧中的主人公在生存空间上都存在着自身的困境;另一方面,两部电影中人物活动空间都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一)人物困境的表达
在电影创作中,塑造人物最常见的一种方法是让人物处于困境之中。给人物制造困境,是可以展现故事当中不同成长阶段的人物形象,也能够建构电影的叙事空间。导演殷若昕正是通过人物命运的书写来建构电影的物质空间。《我的姐姐》中,作为姐姐的安然始终陷入困境之中。她从小就受尽“男尊女卑”封建迷信的影响,在“重男轻女”观念下,她被迫地被父亲贴上了“残疾人”的标签。在父母眼里,姐姐好像从生下来就是“错误”的,但殊不知姐姐又承担了多少家庭的重担与责任。面对着父母意外去世,姐姐安然的生存环境令人同情,怀揣未来规划的她此时面临着抚养弟弟和追求梦想的双重选择。从血缘关系上来讲,长姐如母,姐姐抚养弟弟是天经地义,符合伦理道德;从现实生活来看,要想让一个姐姐放弃自己的梦想,接受一个并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几次面的弟弟,确实是一个难题。独立、尖锐且强势的姐姐安然在此刻陷入了困境。导演殷若昕在电影中不仅书写了姐姐安然的困境,而且运用安然姑妈的故事来放大当代女性的共同境遇。与之相同,姑妈安蓉蓉也是一名姐姐,而她是上一代为家庭操守而牺牲自己的传统女性代表。姑妈受到的传统观念更为强烈,原本价值恰恰与姐姐安然相悖,起初试图用“长姐如母”的观念使安然就范,可历经生活的洗礼之后,最终两位姐姐实现了心灵上的共鸣。姑妈生活困境的书写为电影生存空间表达提供了辅助作用,两代姐姐的对比将现实且深刻的社会议题予以呈现。舅舅武东风是一位不正经的长辈,他从小时时刻刻受到姐姐的照顾和保护,这样的生存环境导致他始终游离于家庭责任之外,可他却是最理解安然的人。弟弟安子恒是最无辜的人,父母的离世让他丧失了家庭的爱,正如他对姐姐安然所说的那句:“我只有你了。”弟弟安子恒面临的正是被姐姐抚养与送人寄养被动选择的困境。《再见,少年》中,好学生黎菲的生活环境较为优越,她属于衣食无忧、从小受到父母保护的一方,随着不断成长唯一面对的问题就是父亲的降职与对友情的认知问题。与之相反,坏学生张辰浩则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的生存空间与黎菲相反,家庭中有患病卧床不醒的母亲与酗酒赌钱无魂的父亲,而他渴望一个奇迹,试图通过让自己变好来使得母亲苏醒。两部影片剧中人物生存空间的设置使得观众了解剧中人物困境,从而回归对社会现实议题的思考。
(二)限制性活动空间的设置
殷若昕导演在表达电影物质空间进程中设置了限制性的人物活动空间。在殷若昕的两部影片中,“家”是最为典型的物质空间设置。《我的姐姐》中,姐姐安然的活动空间归置于父母“留下”的、且被他人所认为本该属于弟弟的学区房中,这一屋子堆满了各种“琐碎”。这本是属于姐姐自己的领地,是姐姐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而当弟弟与姐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屋子显得十分狭小和拥挤,两人极为紧凑居住地的空间予以呈现。弟弟对姐姐物质空间的介入,也潜移默化地让姐姐的生活状态发生了转变。姐姐安然在医院工作的区域也是受限制的,作为护士的她停留在护士台,平日的工作是护士的一些基本工作,只能在护士台与病房之间流转,这对于精通医术、本该成为医生的她不乏是一种约束。而这些限制却潜移默化地成了姐姐安然想要追求梦想、冲破束缚的动力。《再见,少年》中,男女主人公的活动区域主要被固定在了家、学校与铁路。好学生黎菲的家庭条件较为优越,家中布局精致、整齐,家庭可以活跃的空间范围较大。相反,坏学生张辰浩的家庭条件极为艰苦,他的家庭环境中,家具破旧、房屋拥挤且光线暗淡,整个屋子母亲的病床就接近占据了面积的三分之一,每次看到卧病不起的母亲,张辰浩似乎在屋内没有落脚的空间,不得不蜷缩在屋子内。两种家庭空间的对比,从侧面反衬出男女主人公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为接下来两人的渐行渐远埋下了伏笔。另外,学校被视为学生上课的地点,属于领地内的区域,而街道、铁路等都属于领地外的区域,属于社会空间。领地内的学生受到庇护,但若置身领地之外便会受到社会人员的影响,甚至是欺凌。张辰浩的活动空间正是如此,在学校内的时候,他极力想要去学习改变自己,试图创造一个从坏学生向好学生转变的奇迹。而当他身缘领地外的时候,就会有社会闲杂人员的出现将其限制,阻碍他追求真正意义的人生。殷若昕导演对于限制性活动空间的设置与现实生活相接轨,极具写实性并富有深刻的韵味。
正是因为殷若昕导演对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的设定,使得其影片人物极具写实性、现实性以及生动性,物质空间下电影叙事中的人物困境与命运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殷若昕电影中叙事空间建构的特色。
二、视觉元素构筑社会空间
电影的社会空间即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综合形象。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人在其中活动的物理场所,它的建构是编织这些活动的关系构式,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3]殷若昕导演在两部电影中用社会空间来诉说生活百态,将生活中人情世故融入电影中,极具现实感和代入感。在其电影中社会空间的表达主要体现为用构图表现社会关系、用音乐表现社会关系和用道具表现社会关系。
(一)用构图表现社会关系
电影的构图不同于其他艺术之处就在于电影的构图是动态的,而随时变化的构图能够表现电影剧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形式来讲,具有设计感的构图可以增添电影画面的美感,起到美化的作用;从内容来看,动态的构图变化蕴含着剧中人物社会关系的变化。《我的姐姐》中,姐姐安然小时因身着漂亮长裙被父亲打骂的片段之中,画面构图正是体现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片段先是展现安然和母亲单独的画面,两位女性居于画面的中间,虽处于主体地位,但她们被窗帘所包裹着,看不见真正的全貌,暗含着女性地位的缺失。当安然的父亲走入画面之后,画面中的构图有了动态变化,原本居于主体的女性从画面中间一分为二,母亲与安然居于画面偏左一侧,而父亲却独占画面右侧,父亲的谩骂与鞭打气势凌人,一度抢占到了画面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导演殷若昕用构图表现了当时安然与父母之间的人物关系,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盛行。《再见,少年》中黎菲与张辰浩在铁路上的构图也体现出了两人的社会关系。黎菲面带微笑行走在轨道之上,而张辰浩低头苦闷偏离道路之外,这里的构图暗示了好学生黎菲是走在正确轨道上的人,与之相反,张辰浩则是脱离轨道的人。两人获得了特殊意义上的友情,二者关系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此处的构图暗含着两人社会关系的渐离与疏远。
(二)用音乐表现社会关系
音乐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恰到好处的音乐不光可以渲染气氛,也可以表露剧中人物的社会关系。殷若昕导演在电影中对于音乐的把控,将剧中的社会空间完美塑造。《我的姐姐》中,姐姐安然在地铁站尝试将弟弟安子恒丢弃的片段,用音乐诉说姐弟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化。空旷的站点早已没有了姐姐的踪影,激烈鼓点下紧张音乐的背后只剩下弟弟安子恒口中疾呼的“姐姐”以及无助的哭声,又因在感情彻底爆发前发现姐姐背影,从而响起温情的音乐。姐姐内心的柔软与刻在骨子里的温情在此刻予以放大,血缘与亲情的背后是姐弟二人情感关系的升华。《再见,少年》中,两人在铁路上争执,提琴的音乐夹带着钢琴的忧伤,仿佛在倾诉着两人各自的心事,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隙,友情似乎已变得不再完整。张辰浩的社会空间具有不确定性,与好学生黎菲截然相反之处在于他结识诸多社会小混混。电影末端,混混大刘误杀务工女小艳艳的片段,音乐是不同寻常的,大刘望张辰浩包庇自己甚至想要让他替自己顶罪,此时的音乐带着特殊的曲调,甚至有些难听刺耳。交友不慎以及原生家庭带来的社会空间随着音乐的进程使张辰浩进一步迷失了自我。殷若昕导演两部电影的共同之处在于,她用音乐构筑起的社会空间对于影片的叙事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用道具表现社会关系
道具具有象征意义与隐喻功能,在殷若昕导演的电影中,道具的使用也表现出了剧中人物的社会关系。《我的姐姐》中,弟弟身旁的皮球道具的运用一语双关。一方面,皮球象征着弟弟本身,在自己物质空间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弟弟安子恒如同皮球一般,游离于姐姐与寄养家庭之间;另一方面,弟弟紧紧怀抱的皮球正是姐弟两人关系之间最后的稻草,弟弟始终不愿将其放下。皮球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姐弟之间的关系也像皮球一样渐近或远。同为姐姐的姑妈视俄罗斯套娃为珍物,出于保养的原因,姑妈每天都要擦拭它,因为那是她年轻时的梦想。可姑妈又何尝不是为了传统家庭而牺牲了自我。导演殷若昕用俄罗斯套娃进行隐喻,表现姑妈和姐姐安然的社会关系。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角色正如同俄罗斯套娃,套娃中一代传承着一代,一代又重复着上一代所做的事情,由此可见俄罗斯套娃生动再现了传统家庭中无数个鲜活的女性牺牲者,传达出当时传统社会家庭观念中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以此表达相应的社会关系:姐姐与姑妈之间是两代女性的代表,其背后隐藏的含义极具现实意义。《再见,少年》中,影片开始的石头也具有表现社会关系的隐喻作用。黎菲手中拿着的西西弗的石头暗指自己与张辰浩之间的友谊,看似柔软且又坚硬。西西弗被罚将一块重重的巨石往山顶上推,但由于其沉重的重量石头在不停地往山底跌落。石头象征着苦难,少年张辰浩正如同西西弗一样。家庭的苦难与生活的艰难让他成了一个不断推着石头上坡的人,但即使面前的困难再多,他也选择靠自己努力去克服一切。两人之间的友情虽然消弭于时间的进程,但又在各自的脑海中刻骨铭心,随着影片的进展不断影响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由此可见,殷若昕通过构图、音乐以及道具的成熟运用,成功建构出其电影独特的社会空间,在电影叙事进程中,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综合形象自然而然呈现。
导演殷若昕在《我的姐姐》和《再见,少年》两部作品中注入了对于电影空间的独特理解。殷若昕从电影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出发,塑造出电影的独特叙事空间,深刻揭露当下有关亲情、友情的社会议题,并引发讨论。其间不乏生存环境与生活困境的书写、多元化社会关系的表达,通过对自己两部电影的叙事空间建构,让观众在其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中,对社会、生活和现实有了更深入化的理解。
结语
导演殷若昕通过对电影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构建,利用导演塑造、别出心裁的空间建构的方式,表现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期间包括人物命运的书写、生活百态的诉说以及人文关怀的体现。殷若昕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书写、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表达以及隐喻的运用,对构建电影叙事空间的策略提出了个性化诠释,极具艺术特色及现实意义。殷若昕导演在电影作品中对于物质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够让观众更快融入影片故事真实的空间环境之中,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进行研究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感受殷若昕影片的空间环境,而是置身于种种困境之中,面临种种选择之时,能够正确考量自身与他者的社会关系并做出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