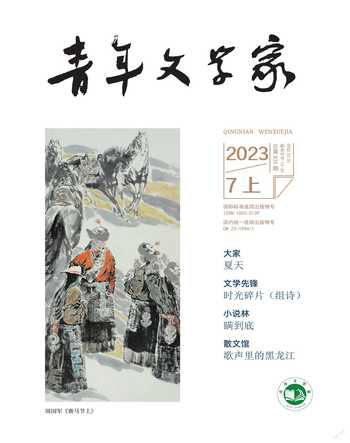瞒到底
麻静雯
江上的小船悄然驶过,枯黄的卢苇凹陷成一个记忆的窝,像有人来过。邱伯寻着船的方向沿岸边缓缓行走,他想象自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可是那细碎仓促的步履,始终追不上破浪前行的船,涟漪朝他冲过来,泛起的浪花,白不过邱伯的头发,只好缓缓退去。
邱伯睁开眼,原来是一场梦。他的右手被眼前的男人紧紧握着,男人的脸憋得通红,双眉拧成疙瘩,眼里泛着泪光,焦急而用力地喊道:“爸,爸,您醒了,您看看我……”
空气凝成紧张的一团。邱伯呆望着他,沉浸在不知是梦里还是现实的记忆中。那江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船驶远了,江面才恢复平静。邱伯停下来,就停在凹陷的卢苇旁边,那里的空间似乎要大一些,正准备坐下,身后熟悉的声音竟把他喊住了。
邱伯没有转过头去看,离开太久,一定会有人找过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托举着邱伯的手臂,轻声说:“您猜谁来看您了?”
是男人来了,邱伯知道。每逢周末,便有人来看望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六个年头。
邱伯笑,念叨:“赶快回去。”
从岸边往回走,踏上长长的台阶,靠江的漂亮房子是邱伯的居所。居所一边望江,一边望山,靠山的窗户外面,景色常年沉浸在深邃的清幽里。邱伯说,山上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山景看得久了,仿佛草木都已凝固,心跳也渐渐地沉寂下去,他才想到要去江边听一听風声。
“阿爸,下次出门让他们陪着,您一个人我不放心。”男人放下手里的果篮,接过邱伯的手臂仔细挽着,嘴里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如同很久以前,邱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儿子那般,显得细心又贴心。邱伯自然很满意。
那些身穿同样制服的人,让邱伯觉得无趣。他们总是在一旁忙忙碌碌,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吃穿用度不用邱伯自己操心,只要开口,就有人为他安排妥当。尽管如此,邱伯还是想往外走,他们便认为是否服务得不够好。
“您在江边看见什么有趣的事吗?”他们同情而又关怀地看着患了健忘症的邱伯,为他递去一杯温度刚好的茶水。
邱伯说:“江面上能看见鸟呢,比在房间里看见得多。”
窗外,空旷的天空里,只是些灰白迷蒙的云,云层缺处看得见半角蓝天,光芒欲藏还露。这些年,邱伯多半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仿佛多看几眼,太阳就能出来,也许再过几年他真的会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至少,邱伯此时清醒地记得,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工作,邱伯没有去过也去不了,忙碌的节奏使得儿子不能时刻陪伴,瞒着儿子安然无恙,一切才会叫人称心如意。
男人察觉出邱伯有心事,小心翼翼地关怀着,要替老板尽全力哄邱伯开心。有人则在一旁附和着:“您儿子真是孝顺,您老有福。”
邱伯对男人点点头,嘴角挤出一抹淡淡的笑,缓缓地喝完手中的茶水。虽然男人很努力,但一点儿也不像儿子,邱伯心里明白,这个男人只是在演戏。邱伯极力配合着,生怕男人看穿自己假装出来的健忘,只敢表现得愚钝些。
天空越来越暗,暗得能望到漆黑的尽头,窗外树影的模样也变得很奇怪。
当邱伯再次醒来,看见双眼含泪的男人站在跟前。邱伯右手冰凉,不管男人怎么捂都温暖不起来,身上插满管子,竟说不出话。呼吸机一刻也不能停,否则会令邱伯窒息。
过了一会儿,邱伯察觉到疼痛,他却逼迫自己朝男人挤出一个笑,极力用咽喉发出类似于“好”的声音。邱伯心想,这个男人一定会向儿子汇报自己的情况,他要尽量装得淡然一些。邱伯眼前的男人再也忍不住,心疼如刀绞,眼泪“唰”地一下掉了出来,沉重地砸在惨白的床单上。
邱伯感到身上一阵痛苦,于是,他紧闭双眼尽量不想被看出来,再次陷入糊糊涂涂的状态里去了。原来,邱伯已经不记得,眼前紧握他右手的可怜男人,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