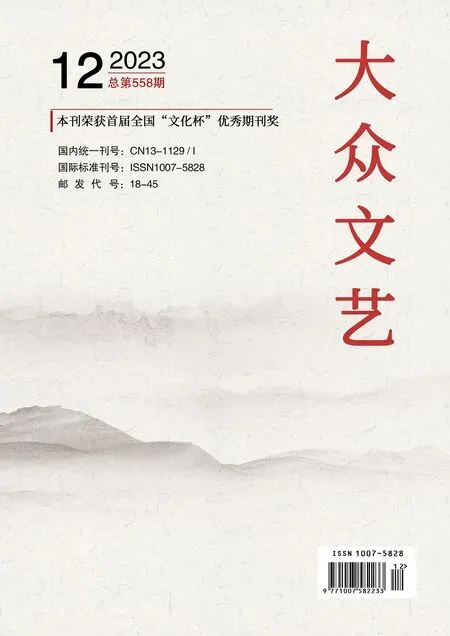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四声猿》中徐渭的生命美学思想观探究
张如添翼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四声猿》是明代才子徐渭所创作的四部短剧的合称,这部作品被王骥德称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①。其名自何而出学界一直颇有争议,较为可信的是取郦道元《三峡》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和杜甫《秋兴》中“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的悲苦之义,但《女状元》和《雌木兰》两部仅以内容来看皆为圆满结局,似乎与悲苦之义不符,是否偏离“猿啼四声而断肠”的主题呢?
在中国古代的审美历程中,“生命美学”的概念总是贯穿创作与欣赏的始终,《周易》中对“生”与“易”关系的讨论引发了华夏民族对于自然生命最为独特的体验与思考;王国维的“古雅”及“三境界说”累积了生命意志的历史厚度,促使人民寻求社会生命的解脱和价值;宗白华则在生生不息的生命运作过程中升华了“境界”的概念,指引大众寻找精神节奏与生命自觉的契合。生命美学的本质即以体验为核心,以生命为本源,以超越为指向。笔者认为,《四声猿》正契合了陈伯海先生对自然生命、自觉生命及自由生命三者关系的探讨[1],是徐渭自然生命体验的充分展现,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进行充分的自觉性批判与反思,所谓猿啼之悲苦并非故事之悲苦,而是所反映的社会之悲苦及生命之悲苦,故事之圆满亦是徐渭的自觉生命意识寻求自由生命的超越所致。
一、经由体验而形成的生命美学观
徐渭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与解缙、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其才华充溢书法、绘画、文学、戏剧、军事等多个领域,是青藤画派的鼻祖、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以豪迈放逸,狂傲不羁的艺术风格见长,但他本人的实际生活却不似艺术风格一般自由,而是出生在一个由盛转衰、乱象丛生的时代,其个人生活也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对自然生命里的悲欢离合有足够充分的体验。
徐渭生活在明代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重要时代,这一时代动荡不堪,内有严嵩等内阁首辅植党营私,外有“南倭北虏”,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徐渭虽满腹才华,有远大志向,但却坎坷波折,不被认可,加之其前半生始终在科举、婚姻、家庭等因素的重压下失意迷离,徐渭拥有了丰富且复杂的人生经历丰。现实生活的困苦性与其艺术风格的豪放性碰撞下产生强烈对比,由此导致徐渭被冠以“狂人”的名号,学术界对于其狂性人格的产生有两种观点:一是徐渭其由于连年打击,而真正患上了疯狂症。二是认为他是发真性于佯狂自纵,即以癫狂的病症为借口抒发自己的真实个性。笔者更赞同第二种,这从他人生前后的行为对比便可知,对于科举执拗追求的他晚年受张元忭邀请多次赴京任职自己所擅长之事,可都被委婉推辞,与友人先后多次游历山河,期间撰写了《会稽县志》《游五泄记》等一系列描写自然山水、边塞风光的优美诗文,他的文学、艺术也臻于一个新的境界,即基于“本体自然”的自由意识而形成的宣泄痛苦,为自由抗争的佯狂忘我境界。由此,徐渭并非病态、被动的,而是主动、积极地对自然生命以审美态度审视,以此达到了潘知常先生所认为的生命的理想状态,即作为生命救赎的审美式人生[2]。
早在狱中徐渭就自述其艺术创作并未因入狱而受阻,反而因艺术他过得十分自由,在《评字》中他写道“隆庆庚午元日,醉后呼管至,无他书,漫评古人,何足依据。”②审美活动是无限性的见证,是生命需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担着内驱力的职责,表现为精神自由及心灵解放的需要。正是徐渭将生命的体验视角沉浸于审美之中,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他摆脱了功利的束缚借助艺术克服了难挨的牢狱之灾与对科举的执拗,在更广泛的领域他也获得了潘知常先生所认为的人类本体活动的“大审美”,即在一切活动之中,“按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是人之为人而寻求真实的根本③。同时,徐渭对于自然生命的充分体验也完整的表现在了其戏剧作品中,《狂鼓史》虽明写祢衡在阴间重演辱骂曹操一事,但实际上是其借祢衡之狂对当朝佞臣严嵩等人进行强烈批判;《女状元》中写黄崇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无法获得认可,是对徐渭本人才华的多样展示及前半生怀才不遇的讽刺;《雌木兰》写边塞军旅正是其本人对边塞风光及戎幕生涯的追忆及向往。徐渭之狂是他丰富的自然生命体验与审美态度的撞击而产生的,正是对生命美学的审视他将一切困苦视为生命的艺术化体验,从而在作品与人生中同样达到了个性解放及追求自我价值的“狂”之境界。
二、《四声猿》中对生命本源的认识与探讨
《四声猿》除了蕴含着徐渭对生命体验的印记之外,更是徐渭对人生命本源认识的结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的生命本源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同潘知常先生的观点,认为需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个体是什么,二是个体怎么样。
徐渭对个体是什么的探讨充分体现在他的“本色论”戏曲美学思想当中。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首的文人以“彻远以代蔽,律古以格俗”④为目的力求学习古典,但古人的表达方式并非适合今人,拟古必然拘束真性情的自然抒写,并有可能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面对这种泯灭人性的大环境及复古派操持文柄的现状,徐渭的“本色论”反对文人以“宫廷化”的套路方式为南戏作规定为“南九宫”,支持保持南戏本身的声律特点及娱乐的通俗性,也反对将《诗经》等文学用语用于杂剧并使用骈语而追求对偶工整的现状,更加提倡以通俗、浅白、贴近人物和生活的“本色语”(即俚语、俗语、常用语等)书写,如《狂鼓史》中以生活化的俗语对曹操的咒骂,凶狠直接,一针见血:
大缸中去几粒芝麻罢,馋猫哭一会慈悲诈,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你如今还要哄谁人?就还魂改不过精油滑。⑤
又如《玉蝉师》中借蝼蚁为喻,通俗生动,直面认识并抒写人性的欲望:
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漏了黄河堑。⑥
通过这些妇孺皆可歌,大众皆可言的音律及文辞特点,徐渭拉近了戏剧与群众、艺术与生命的距离,既体现了戏曲的审美功能而打动人心,又充分做到了喜闻乐见并具有生活的烟火气,由此贴近到生命最本真的情感部分。在真情的投射下,戏剧角色冲破理学束缚,坦诚面对生命本真,以啼笑戏弄的方式传神的表达出不受约束、自由驰骋的个性特征,确立了生命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但仅有对“个体是什么”的探讨是不够的,潘先生认为以往美学研究更多的关注人的自我是什么,即表层现象之下的本质性问题,而很少关注价值论方面的存在性问题,即人的自我是怎么样的[3]。个体成为个体的原因,并非因其本质生而被规定为既有的路线,而是在自我存在的能动性探索下被确定的[4],明代的僵化风气正是对生命存在的压抑,面对个体是怎样问题的解答,徐渭在《四声猿》中大力批判社会现状的同时又倡导个体自我的觉醒。首先,批判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倡导男女平等思想的觉醒。一反以往作品中女性作为附庸地位的柔弱形象,徐渭作品中的“花木兰”和“女状元”两人一文一武,通过个人能力向上进发,塑造了心胸宽广,不受束缚,有真才实学女性形象,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有极强的超前性。
其次,批判封建官场的腐败,倡导真实性情的抒发。《狂鼓史渔阳三弄》中借咒骂曹操而直接表露对残暴的当代统治者的批判,语言激烈通俗,不着一丝遮掩;《雌木兰替父从军》中父亲年事已高,但仍被官府连下十二卷军书招致战场,借官府的不爱惜民力侧面反映了横征暴敛,压迫百姓的现状;《女状元辞凰得凤》中徐渭的期望也借考官对胡颜的评价而出:“这胡颜词气便也放达,可也忒出入。可取处只是不遮掩着他的真性情。比那等心儿里骄吝么却口儿里宽大的不同。”⑦这也是徐渭一身才华始终无法在死板的科举制考试中展露的真实现状,他期望虽然纸面的答题不足以满足僵化的要求,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真正的才气与性情才是个体生命的直接表达,唯此将视线聚焦于此,才能改变当今僵化的制度现状。
再次,批评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提倡对生命本身的信仰。《玉蝉师翠乡一梦》中玉通和尚虽闭关修行多年,但却一直自我欺骗,对本真欲望避而不见,因此只被人略施小计就破了戒,之后还一反高僧形象投胎报复,几十年的修行皆华而不实吹弹可破。玉统和尚所谈的信仰,只是人们对未知的无限性世界的一种自我设想与安慰,人们当然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应是盲目且自我欺骗的。生命美学提倡“为美学补神性”,这一信仰应该是审美的信仰,潘先生认为与审美活动有关的审美对象,使人们可以产生对无限性的追求与向往,在对无限性的见证之下,人们一步步向美靠近、向美追寻,由此美产生了[5]。有了审美的信仰人们便可见证美,之后便拥有了爱的能力,爱是人们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认识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能力,它引导人们在边缘处寻生。基于对个体存在是什么的认识,进一步追求怎么样才能达到那种生命的本真,才能像晚期徐渭一样与自己的执拗和解,追求山川河流旷达生活,唯有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从而获得爱的能力,才能在自我与社会中看到无限性的可能,个人追求无限性人的自我便开始觉醒,无数觉醒的个人总和才能促进社会的觉醒,这一切都来自最初对生命本源的认识与追求。
三、《四声猿》对生命超越性的追求
封孝伦先生认为人的个体生命是由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三者组合而成的三重生命理论系统[6]。在这一系统中,作为物质载体而现实存在的生物生命是极为脆弱和局限的,唯有通过激发精神生命的方式才能促进人类对生命的全面体悟,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解蔽,激发精神生命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审美这种人性自觉而为的生命活动,美是人类生命长河中所不断追求的一种精神价值。对于生命的超越是生命美学的最终指向,徐渭对于自然生命有充足的体验基础,见识到自然生命局限的一面后通过审美的方式在《四声猿》中进行辛辣的讽刺,在戏剧结构、音律、主题等创作观点的主张上又将抒发个性的主动权替生命拿回,生命的自然性变为自觉性,从而充分寻求社会生命的建立,而后通过不断地批判呼吁、反思改变,才能得到升华,从而进入自由生命,即超越有限束缚,进入无限精神境界的超越性阶段。
单从徐渭文章内容的角度来看,故事仿佛并没有那么超越,《狂鼓史》讲了进入地狱仍不忘生前曹操之仇恨,《玉蝉师》讲了高僧周转几世仍要报复,但实际核心内容都存在于结尾段:祢衡选择了主动原谅曹操,玉通和尚也被开悟成佛,这种角色思想上的反转与升华才是徐渭超越性思想的表现。这正如潘知常先生对美最高境界的界定,即在爱与信仰的共同作用下,对一切苦难的包涵与理解,这一境界,必然是无缘无故的,是用我们的生命之爱为指引的,在不断与苦难的和解中体会到真切的快乐与美好[7]。在作品内,过错被爱与信仰包容,因为这些苦难都是个体生命存在必然会遇到的本性问题,原谅他人即直面自我,直面自我即可超越生命。在作品外,徐渭将人生苦难用审美的手段处理与审视,以狂性保持着自由的尊严及人性的尊严,通过它们人类才能从自然的物质性中升华,以独有的精神性耸峙寰宇,获得对生命的不断超越。
生命美学十分强调这种以超越维度和终极关怀为视域,不止关注生命生物学意义上的吃饱穿暖,而是要把“忧世”的现实关怀提升到超越的维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离不开人们对死亡意识的认知。如玉通禅师主动进入轮回、祢衡寻求往生的慰藉一样,对死亡的认识与思考是所有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信仰维度对死亡的终极关怀也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存在方式,爱与信仰的权利是人类生命特有的自由选择与精神选择。潘先生认为通过爱与信仰,人们就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超越死亡,反之如第一世的玉通禅师一样,即使自然生命仍然存在,但只拘泥于此,便无法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死亡意识本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高级意识,只有深刻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并接受必然死亡的事实,人们才能将目标转向更多不会随生命逝去的,处于精神境界的生命追求。如祢衡即使身处地狱,但用爱包容一切,精神生命已经达到永恒,即达到一种“用爱来获得永恒”的“天人合一”的绝对高度,这一境界是同样也是生命对自我个性的完善与抒发,是生命回归的最终落脚点。
《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的最高成就,更是徐渭戏剧思想的集大成者,四剧主旨虽各有不同,但都紧紧围绕着生命的悲苦而作。徐渭前半生颠沛坎坷,对生命的体验无人能及,虽几经放弃,但都是靠着审美的态度度过了牢狱之灾,度过了怀才不遇,与其说是苦难循着徐渭的人生轨迹,不如说是徐渭选择了拥抱苦难、体味苦难,终是品味出了掌握生命、反抗命运、寻求“本色”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由内而发,从生命的骨子里由个性激发而出,使得徐渭对生命的认识由追寻者变成了掌控者,由此他达到了自由、狂傲的天人合一之境,学会用爱与信仰接受生命的多种形态,其身上绽放的生命美学之光一直持续到现在。
注释:
①王骥德著:《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②[明]徐文长著;施蛰存校点:《徐文长逸稿》,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第1055页.
③潘知常:“生命美学作为未来哲学”,南方文坛,2021(05),第49页.
④李淑毅等编.何大复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07),560页.
⑤(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04),1183页.
⑥(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04),1188页.
⑦(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04),1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