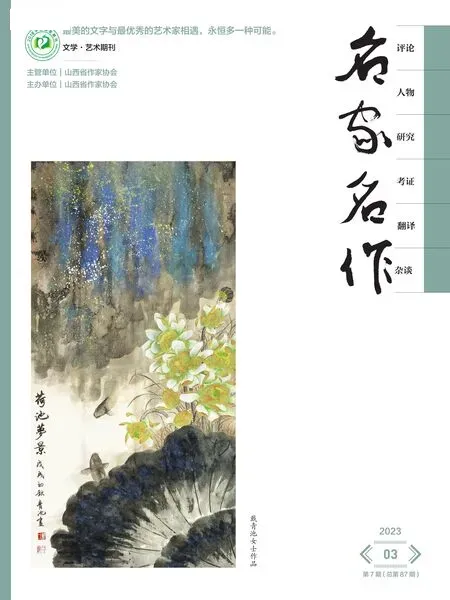二晏涉筝词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探究
唐巳田
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政治上“文人治国”,商品经济发达与市民阶层的扩大,推动了俗文化的兴盛,其审美趋向也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筝乐与词分别作为俗文化中音乐与文学的代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二晏(晏殊、晏几道父子)作为北宋文坛的代表词人,在筝乐艺术与文学方面成果显著,其涉筝词中的音乐美学思想一脉相承,却又各有千秋。
一、二晏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上,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
自安史之乱之后,频繁的战争与王朝更替使宋朝统治者认识到,相比外敌入侵,国家内部矛盾更值得被重视。而宋太祖本是草莽而非正统,经陈桥兵变后才得以黄袍加身,这使其更加重视中央集权统治的稳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评价:“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1]宋太祖由于其个人经历而心生畏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政治上体现为以避战仁慈为核心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也决定了北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同时,统治者也通过支持官员享乐来削弱文官的参政热情,以维护统治稳定。宋太祖言:“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2]同时也推动了宴饮之风的兴起,为二晏涉筝词的创作提供了政治前提。
(二)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扩大
北宋建国后,政局稳定,经济恢复,人口快速增长。至仁宗、真宗时期,城市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出现了开封等10 万户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城市中传统坊市格局被取缔,空间与时间的界限被打破,商业发展空间迅速扩大,繁荣的商品交易吸引了大量劳动力。随着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市民阶层的扩大与城市经济的昌盛,推动了文娱需求的增加,“瓦子勾栏”应运而生。“‘瓦子’亦称‘瓦市’,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3]瓦子勾栏形成于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宋代市民的重要娱乐场所,也是宋代市民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瓦子勾栏的滥觞为俗乐的繁盛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加之宋代统治者默许声色享受的政治导向,以筝乐为代表的市民音乐逐渐流行,“雅俗共赏”的艺术格局初步形成。
(三)文化上,市民审美与文化转型
宴饮之风日盛与娱乐场所的泛滥,使北宋社会形成了两种音乐文化发展脉络。一种是文化上移。文人们一方面碍于儒家礼乐观而提倡雅乐,另一方面又无法抛弃对民间音乐的喜爱,于是出现了“以雅化俗”的思想,这种对民间俗乐的雅化倾向在大晏涉筝词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另一种是文化下移。五代以来,大量宫廷乐伎流向民间,同时也带来了宫廷音乐审美。宫廷雅乐的表演形式与演奏技巧也在不断演变中影响了市民阶层的音乐审美趣味。这一时期,宫廷音乐受到民间俗乐的冲击,“雅俗共赏”成为北宋音乐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二、二晏涉筝词中的古筝艺术元素
关于二晏涉筝词的界定,本文以《全宋词》和《二晏词笺注》为主要参照文本,选取词中与筝相关意象及内容的词作,并对二晏涉筝词的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大晏共10 首,其中9 首收录于《珠玉词》中;小晏共12 首,均收录于《小山词》中。笔者将其中涉及“筝”的意象进行了归纳整理,占比较大的主要有“筝曲”“筝器”“筝人”三类。本文将从以上三个角度对二晏涉筝词中古筝艺术元素的审美体现分别进行阐述。
(一)筝曲
提到筝,就必然不可忽略筝曲。据统计,《全宋词》中直接提到的筝曲有27 首,其中能在二晏涉筝词中找到对应词句的有4 首,且均出自小晏之词,分别为《湘江曲》《乌夜啼》《水调》与《梁州》。
《湘江曲》又名《潇湘送神曲》,为唐传十三弦筝曲,相关涉筝词中以小晏《菩萨蛮》最为经典:“哀筝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4]该曲取材于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泪洒斑竹之传说,曲风悲凉哀婉。词中“声声写尽湘波绿”化虚为实,再结合视觉与听觉感受,将乐曲与弹奏者合二为一,感人至深。
《乌夜啼》又名《啼乌》,源自赛乌祈福的风俗。唐朝时乃鼓吹之曲,多用铃鼓而非弦乐,宋代以来才用于筝曲演奏。小晏有《蝶恋花》:“细看秦筝,正似人情短。一曲啼乌心绪乱,红颜暗与流年换。”[4]
《水调》泛指《水调歌头》,原为唐大曲,由《水调》摘遍而成,乃唐宋时民间流行筝曲。相关的小晏涉筝词有二,分别为《浣溪沙》:“脸红莲艳酒醒前,今年水调得人怜。”[4]与《蝶恋花》:“水调声长歌未了,掌中杯尽东池晓。”[4]
《梁州》亦名《凉州》,源自龟兹乐,初唐时由西凉传入,在宋代流传颇广。小晏《清平乐》中有:“钿筝曾醉西楼,朱弦玉指梁州。”[4]此外,小晏《小山词》中还有一首《梁州令》,也是在唐筝曲《梁州》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二)筝器
将古筝从乐器结构方面进行拆分,主要可分为三大部件,分别为筝体、筝弦和筝柱。由于在二晏涉筝词中对筝弦涉及较少,故本文将着重对筝体和筝柱展开论述。
筝体方面,二晏涉筝词中对于筝体的描摹多聚焦于筝体上镶嵌的各类装饰物,于是便出现了“宝筝”“钿筝”等对筝外表描写更个性化的称呼。例如大晏《殢人娇》:“空肠断、宝筝弦柱。”[4]又有小晏《清平乐》:“钿筝曾醉西楼,朱弦玉指梁州。”《木兰花》:“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4]钿筝,指在筝体表面镶嵌金银珠宝,起装饰作用。
筝柱方面,宋代筝柱也如筝体般多施以装饰。例如大晏词有《踏莎行》:“秦筝宝柱频移雁。”[4]“宝柱”即用宝石制作的筝柱;与之类似的还有小晏《菩萨蛮》:“玉柱斜飞雁。”[4]这里的“玉柱”指的是玉质的筝柱。此外,筝柱因其排列形似大雁,故也被称作“雁柱”,二晏词中也常以“雁”来指代筝或筝柱,大晏《殢人娇》中便有“楚竹惊鸾,秦筝起雁”[4]之句。
(三)筝人
在家中豢养乐伎为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好,在北宋宴饮之风的催化下,更是成为文人风流之象征。随着以筝乐为代表的俗乐的兴起,筝伎在乐伎中的角色更加突出,也更加受到文人的喜爱。以小晏为例,其家中共四位乐伎:小莲、小杏、小叶、小琼,其中小莲尤擅弹筝。小晏也曾在《木兰花》中表达过对小莲的倾心与喜爱:“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尽日东风吹柳絮 ”[4]。小莲去世后,小晏也为其作词悼念:“花易落,月难圆。只应花月似欢缘。秦筝算有心情在,试写离声入旧弦”[4]。
三、二晏涉筝词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比较
(一)音乐功能
前文提到北宋宴饮之风盛行,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二晏父子也是宴乐的爱好者。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描述大晏:“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与其父相比,小晏对于宴乐活动的参与更加深入,“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5]。其听乐场合多在酒宴歌席之上,现存涉筝词皆与宴乐活动相关。因此,在音乐功能方面,二晏的共同点便在于“娱宾遣兴”上,但二人关于“遣兴”却有不同的立场。
一方面,士大夫出身的大晏更侧重于“乐与政通”的政治功能。早在《史记·乐书》中就出现了对于音乐政治功能的描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以《拂霓裳》为例:“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4]大晏以筝词为载体,描绘了一幅幅歌舞升平、杯觥交错的画面,歌颂天下的太平景象,表达仁宗对国泰民安的赞誉之情。此外,祝寿也是大晏涉筝词中的重要内容,“玉楼清唱倚朱弦”在表达恭祝的同时肯定了仁宗对天运的继承,其词歌功颂德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长期游离于士人群体边缘的小晏更倾向于“期以自娱”的休闲功能。《浣溪沙》:“闲弄筝弦懒系裙,铅华消尽见天真。”[4]与其父相比,小晏的涉筝词将目光从政治转向了自身,情感更加细腻,“以休闲的人生诉求方式包含了对人生情性之道、人生意义与价值乃至宇宙天地的深入思考和体悟”[6]。
(二)筝乐审美
其一,关于大晏词的审美风格,近代学者宛敏灏评价“同叔词无强烈的彩色,无凄厉的音调,但出以清淡之笔,和婉之节,而声调自然,意境清新,形成一种闲雅的特殊风格”[7]。于涉筝词而言,大晏在“雅”的基础上增添了“俗”的色彩,主张“以雅化俗”的筝乐审美倾向。作为士大夫阶层,大晏合用清乐燕乐入词,其词大多是在以雅乐的规范为基础的音乐观念下创作的,涉筝词也不例外。10 首涉筝词中《踏莎行》《破阵子》《殢人娇》《拂霓裳》为《御定词谱》中注明以大晏为正体的十七调之四。这四调均为双调,也最能体现大晏“左宫右徵”的音乐特色。而这样的调式变化在传统礼乐观中被视为“以徵乱宫”,大晏能将二者在词中予以结合,实为顺应宋代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实践。但由于大晏并未完全摆脱传统雅正观念的束缚,“以雅化俗”实为“避俗求雅”,使其涉筝词创作更加具有矛盾性。
其二,北宋后期的小晏亲身实践了“弃雅入俗”的筝乐审美观。小晏与士大夫出身的父亲不同,一生远离官场,混迹于市井之中。在宋代文坛以平心静欲、中正平和为追求的主流审美下,小晏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大量以乐传情之词,《小山词》中更是有许多他与乐伎的情感记录。以《鹧鸪天》为例:
手捻香笺忆小莲,欲将遗恨倩谁传。归来独卧逍遥夜,梦里相逢酩酊天。
花易落,月难圆,只应花月似欢缘。秦筝算有心情在,试写离声入旧弦。[4]
该词为小晏从沈宅听乐后回到家中所作。词中借秦筝抒发对小莲的深切思念,发出“只应花月似欢缘”的感慨,动人心肠。纵观小晏所有涉筝词,其核心都在于一个“情”字,专注于个人情爱抒发的创作,已完全偏离了主流审美,“弃雅入俗”成为小晏涉筝词创作的核心审美思想。
(三)“理”与“痴”
大晏在涉筝词中描绘了宴会盛景,却常掺入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其在创作中仍然遵循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音乐美学标准,叶嘉莹先生评价大晏为“理性之诗人的代表”,“理”也成为大晏涉筝词的重要美学特征。以《拂霓裳》为例:
乐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惜清欢。又何妨、沈醉玉尊前。[4]
词的前半段描写宴席上鼓乐齐鸣的繁华景象,后半段转为对人生聚散无常、时光易逝的思考,秉承了“富贵不能淫”的儒家思想理念,透露出理性的光辉,而大晏的理性创作也为宋代文学理性色彩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庭坚在为《小山词》作序时评价小晏有“四痴”: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4]
由此可以看出,小晏的“四痴”实为诚挚忠厚,境遇不佳仍心怀赤心。与其父相比,小晏涉筝词少了理性思辨的色彩,而在情感表达上更加质朴,筝乐与情感联系更加紧密。在小晏的认知里,乐器是比歌声、文字更具感染力的情感载体,更以“幺弦写意”指出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蝶恋花》有云:“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4]心爱之人杳无音信,只好借秦筝抒发哀伤。乐音低沉使听者肝肠寸断,即使移尽筝柱也难排离恨。也正是因为小晏的“痴”,才使其涉筝词感情纯挚,我们才得以感知那份纯真的美好。
北宋初期的涉筝词大多承袭花间词调,二晏父子的涉筝词却让人耳目一新。父子二人在“雅”与“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大晏试图将雅俗结合,在不违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对“雅俗共融”做出大胆尝试;小晏相较其父的以理节情,在“雅俗之辩”的问题上更加大胆,打破了“乐与政通”的思想枷锁,专注自我而不为外界所扰,呈现出“痴”的音乐美学特征。小晏的音乐思想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宋代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二晏涉筝词中反映的音乐美学思想,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有着一种超前的自由,为宋代文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