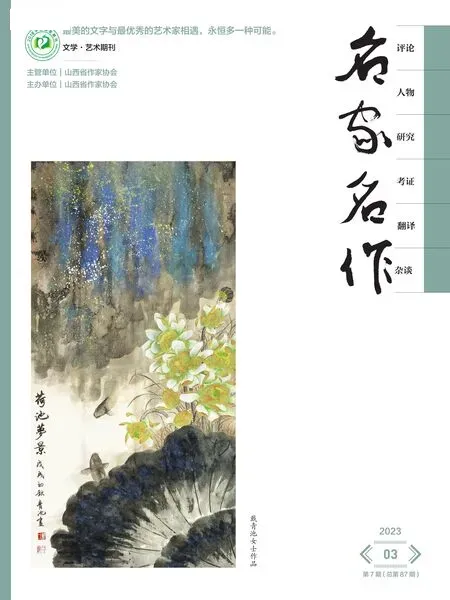论《史记》的“悲夫”之叹
张 云
《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其在客观叙述背后蕴含着太史公的炽热情感与理想追求。后人对《史记》抒情性的分析,或基于记述的内容,或基于描述的手法,或基于表达的句式……本文从抒情的词汇入手,以《史记》中的十三处“悲夫”为切入点,分类叙述太史公的时势变化之叹、荣辱成败之叹、名实相左之叹、世态炎凉之叹。
一、《史记》中的十三处“悲夫”之叹
刘德煊在《〈史记〉的抒情特征》中言:“司马迁喜用‘悲夫’一词来表现某种丰富而深沉的感情。这样的喟叹,沉郁、寂寞的心情宛然如现,表现出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后对世态人情的深刻认识。”[1]详究其实,全书共有十三处“悲夫”之词,分别是《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楚元王世家》《绛侯周勃世家》《六国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从正文位置分布来看,“悲夫”一词主要分布于论赞部分的“太史公曰”,共计九处,其余四处,两处出自他人之言,一是“褚先生曰”,一是“光禄徐自为曰”;两处出自列传本人之言,一是李斯之言,一是司马相如之文。
全书十三处“悲夫”之词,不仅分布的篇目、位置不同,其所表达的情感内蕴也不同。《〈史记〉导读十讲》中提到,《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内容主要包括时势之变、兴亡之变、成败之变和穷达之变[2]四大方面。通过十三处“悲夫”之词,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太史公对时势变化、荣辱成败、名实向左、人情冷暖的悲叹之情。其中,尤以荣辱成败之叹为甚。
二、太史公“悲夫”之叹的情感表达
《史记》中的“悲夫”之叹寄托了司马迁真实而浓烈的情感。在这些表述中,司马迁针对朝代更迭时势变化,王侯将相荣辱成败、名实相左、人情冷暖等做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或赞叹,或惋惜,或悲伤,或崇敬之情感表达跃然纸上。正如李巍在《论〈史记〉抒情性及其得失》中论述道:“司马迁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在对事件即人物悲惨遭遇的真实描写中,又借传中人物在此悲惨遭遇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3]
(一)时势变化之叹
秦国集六世之功而一统天下,但是后人仅以秦国二世而亡、《秦记》文辞疏略而看轻秦国、讥笑秦国,这种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的认知,让太史公不由生出对时势变迁的“感叹”之情。
《六国年表》记载了秦国“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4],一展天下时势之变。纵观《六国年表》,秦国于“襄公始封为诸侯”,历经文公“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闲”,穆公修政“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此后,秦孝公变法强秦,成效宏大。至秦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功业非凡。
《六国年表》内容多参照《秦记》而作。但因《秦记》文词疏略,秦国二世而亡,汉初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可见汉初对秦国的讥笑看轻态度。当世对于前世之功业视而不见,反因文辞看轻讥笑,太史公故有此叹。
(二)荣辱成败之叹
《史记》中,对于个人荣辱成败之叹尤为突出。王侯将相均有涉及,他们或篡位得权,或忍辱负重,或起于微末,终能成就非凡之功业、名扬于天下,但或因自身失德,或因同僚进谗,主上猜忌,终以悲剧收场,故太史公有此“悲夫”之叹。
1.《楚元王世家》中的“悲夫”之叹,叹楚灵王操行不得而众叛亲离、客死在外
楚灵王杀其侄以自立,会盟诸侯而骄纵无礼。对外穷兵黩武,征战陈、蔡、徐等国,在内穷奢极欲,建章华台以供己享乐。太史公论其“操行之不得”,由此而来。
楚灵王荣耀之时,“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5]。及其一朝行乐在外,宫中变乱,天下离心,独傍偟山野,无人收容、饥饿难起。观此荣辱之变,故有悲叹。为进一步凸显楚灵王的荣辱之变,强调操行对于荣辱的重要性,太史公通过观起之子与申无宇之子一正一反的描述,强化了“悲夫”之叹。从反面来看,因楚灵王“杀蔡大夫观起”,观起之子劝吴伐楚,会合各方力量,让楚灵王众叛亲离、客死在外;从正面来看,楚灵王傍徨山野之时,申无宇之子申亥为报答其父“再犯王命”而灵王“弗诛”之恩,往山中寻求灵王,奉之归家。
2.《绛侯周勃世家》中的“悲夫”之叹,明叹周勃父子性格使然,实悲所遇非人
周勃与周亚夫出身皆因赫赫军功获殊荣。周勃起于布衣,随高祖起兵,在楚汉之争中屡立战功,此后兵讨韩王信、陈豨、卢绾,诛杀吕氏,拥立文帝,位及丞相。周亚夫起于文帝时细柳营治军之严,景帝之初,封为车骑将军,此后平定七国之乱、位迁丞相。太史公赞其“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穰苴曷有加焉”,足见认可。从二人性格来看,周勃质朴刚强,周亚夫耿直刚毅。周勃与儒生相交不能尊重,身在绛县适逢守尉巡视,畏惧被诛而“令家人持兵以见”,因此被人诬告谋反而下狱;周亚夫因直言谏废太子,阻匈奴王封侯等事渐被景帝疏离,此后因其子盗买官器而被诬谋反入狱。所不同的是,周勃用千金贿吏,以公主为证,薄太后开脱得以生还;周亚夫在狱中“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李景星言:“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6]太史公在描述二人悲剧结局中,无限同情二人的悲惨遭遇,同时也表达了对君上、同僚和谗吏的愤怒与抗议。
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用“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来悲叹二人的命运其实是“似贬而实褒”。表面看来二人性格确实会导致先荣后辱的悲剧命运,但细究起来,无论是周勃被人“上书告勃欲反”,还是周亚夫下狱“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7],足见同僚佞言、君上猜忌、下吏侵迫让两位军功卓著、耿直刚强之人不得善终。所谓“削平吴楚大功成,一旦生疑触怒霆”,这才是太史公真正的悲叹所在。
3.《伍子胥列传》中的“悲夫”之叹,赞伍子胥隐忍成事,叹其所遇非人
伍子胥“弃小义”逃亡吴国,最终攻入楚国“雪大耻”,因其隐忍终能成事。在《伍子胥列传》中,楚平王以伍奢为人质,“诈召二子”欲一并除之。伍尚赴死,伍子胥逃往吴国,后伍子胥父兄皆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往吴国之后,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 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终报父兄之仇。此后,伍子胥助吴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
西汉韩诗学的创始人韩婴说:“伍子胥前功多,后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阖闾,后遇夫差也。”[8]夫差继阖闾成为吴王之后,伍子胥多次劝谏不被采纳。此后,太宰伯嚭多次进谗,称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最终夫差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了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自杀前让门客将其双目挂于城门之上以观越国灭吴,反因此触怒夫差,被浮尸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被越国所灭。在《伍子胥列传》中,太史公论赞四句话中三句反问,一句感叹,从语气里即可见其感情的激动。从周勃、周亚夫父子,到伍奢、伍子胥父子,其悲惨结局皆因“所遇非人”。谗臣的进言、君主的猜忌,导致他们凄凉的收场,太史公在论赞中对此寄予了丰富的情感和无限的慨叹。
(三)名实相左之叹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有言:“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9]太史公对孙膑、吴起、伯夷、叔齐、陈豨之叹,或因其名实不一、言行不一,或因高义未扬,或因名过其实。由此,他人之名、他人之言,未必真如其实,更应客观、辩证地看待。
1.《孙子吴起列传》中的“悲夫”之叹,叹孙膑与吴起名实不一、言行不一
孙膑能料敌于先击杀庞涓,却未料庞涓之计而被刑,所谓名实不一之处。孙膑在齐,两次因势利而围魏救赵、救韩,通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计杀庞涓,可谓“筹策庞涓明矣”;但反观孙膑初入魏国,未能预料庞涓刑而隐之之心,而致腿断面黥,太史公称之“不能蚤救患于被刑”。两者对比,即为名实不一之处。
吴起杀妻贪将、母死不归,也能与卒同苦、尽得士心,在魏言德,在楚刻暴,所谓言行不一。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10]吴起虽然于家少德,但却能尽得士卒之心,成就功业,此为一处不一;吴起在魏之时,魏武侯言山河之固是“魏国之宝”,吴起谏言“在德不在险”;反观其在楚之时,则“刻暴少恩”,此为另一处不一。
综上所述,人之名实未必一致,人之言行也未必一致,所以太史公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对孙膑、吴起才有此一悲。
2.《伯夷列传》中的“悲夫”之叹,叹君子高义未必能名扬于世
《伯夷列传》中,太史公言:“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11]伯夷、叔齐让一国之位被世人称赞,因“得夫子而名益彰”;但是许由让天下之位而少有记载,故太史公有“名堙灭而不称”之悲。由此可见,君子高义未必能名扬于后世,能名扬于世者是因有人彰名或者能够“附青云之士”而上。所以,扬名于天下者未必最为有名,高义之士也未必能够扬名天下,故有一悲。
3.《韩信卢绾列传》中的“悲夫”之叹,叹陈豨名过其实招致祸患
太史公悲叹陈豨“名过其实”而致祸患。陈豨仰慕信陵君之名,有招揽宾客、礼贤下士之心,回乡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且能够“待宾客布衣交”。因此遭周昌疑心,陈豨“惧祸及身”,最终走上反叛道路。刘邦观陈豨排兵布阵评价其“无能”,察常山守尉不随其反评价其“力不足”,陈豨最终被樊哙军卒所杀,可谓名过其实之祸。
(四)人情冷暖之叹
主父偃、汲郑均是先得其势,后失其势。在得势之时“诸公皆誉”“宾客十倍”,而一旦失势则“争言其恶”“门可罗雀”。前后之别,太史公引翟公言“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深刻而形象地描绘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悲。
1.主父偃“悲夫”之叹,叹其得势“诸公皆誉”失势“争言其恶”
《平津侯主父列传》中,主父偃未得志时尝尽人间冷暖,当其得汉武帝信任拔擢之时“诸公皆誉之”。后因举发齐王“淫佚行僻”导致齐王自杀,汉武帝下令杀之,则“士争言其恶”。众人前后态度之变,凸显世态之炎凉,太史公故有此悲。
2.《汲郑列传》中的“悲夫”之叹,叹汲、郑二人得势“宾客十倍”,失势“门可罗雀”
《汲郑列传》中引用下邽翟公做廷尉时宾客盈门,中道被废以致门可罗雀,后复职为廷尉,宾客又要登门,于是翟公在门前写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2]太史公以此来比汲、郑二人“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的境遇,对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势利关系,对世态炎凉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讽。
三、余者“悲夫”之叹的情感异同
《史记》中还有四处“悲夫”之叹,并非出自太史公之口,而是由他人所言或所记人物自身之言。其中,褚先生对“功臣侯者”成败的补述、李斯一生荣辱及其下狱后的悲叹,此二处与太史公荣辱成败之叹甚为吻合。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的“悲夫”叹众人目光不够长远,只言害而不见利;光禄徐自为之叹,则表达了对酷吏的痛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褚先生对《史记》所载“功臣侯者”的“成败长短”加以补述,对其“不谦让,骄蹇争权,喜扬声誉,知进不知退争”终至失身灭国的荣辱之变备加感慨,也与太史公著书宗旨和主旨观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李斯列传》中,李斯被囚于囹圄之中,仰天长叹,“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13]回顾其一生,起于上蔡闾巷布衣,至盛之时位居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14]后因畏祸与赵高合流,导致“沙丘之变”,为自保而上书曲意逢迎,在与赵高争势中落败下狱。后被赵高诬为谋反,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观其一生荣辱成败与太史公所叹甚为契合。
《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相如所撰《难蜀父老》围绕大臣和蜀中对通西南夷的非议和畏难之情,通过“鹪明已翔乎寥廓”但“罗者犹视乎薮泽”之喻,暗示众人没有意识到开拓疆域,交好夷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是盯着西南边疆开发的劳民伤财,故有“悲夫”之叹。
《酷吏列传》对十名酷吏作了描述,其中对王温舒捕郡中豪门奸诈“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之事,言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复言其为人谄谀,对待有权势者“有奸如山”也不过问,对待无权势者,虽是贵戚也必然侵辱。天子凡认为王温舒有治事的才能,予以升迁。待王温舒因罪而被灭族,光禄徐自为有“悲夫”之叹,感慨“古有三族”,而对王温舒的罪行诛其五族也不为过,表达了对酷吏的痛恨。
在司马迁《史记》中,拥有着丰富的语气词,除“悲夫”之外,尚有“嗟乎”“呜呼”“宜乎”“惜哉”等诸多词语,明确表达出了太史公写史之中的各种情感。这些词语为《史记》的抒情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太史公的著述宗旨和主旨观念提供了有力的印证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