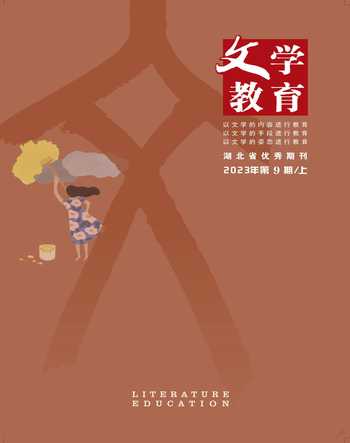陆文夫《美食家》中高小庭形象的反讽性
孙佳媛
内容摘要:《美食家》中高小庭是主人公,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反讽意义。高小庭作为故事人物,其情感结构形成和言语语境误置造成局部反讽效果;作者采用高小庭视角讲述故事,描绘其革命行动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裂隙,展现叙述人观点和作者观点的相悖,造成整体性戏剧反讽。这一形象与作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在他身上陆文夫提出自己对于革命历史和消费文化的理解,旨在完成其“干预人的灵魂”的文学理想。
关键词:陆文夫 《美食家》 高小庭 反讽 情感反讽 行动反讽 戏剧反讽
陆文夫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创作生涯,其间几经浮沉,1983年以《美食家》再度轰动文坛。《美食家》围绕资本家朱自冶“好吃”与革命者高小庭“反吃”历时四十年余年的斗争展开讲述,作品以“美食家”为标题,表面上指涉好吃的朱自冶是主人公,其背后的苏州美食文化是描写中心,但文本故事由高小庭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高叙述中所含的个人情感以及讲述自己与朱斗争的种种行动构成反讽,高小庭才是故事真正的主人公。
反讽一词最初指古希腊戏剧角色中故意自贬佯装无知的行为方式,后来在不断发展中引申为一种文学的整体修辞方法和思维情感的表达方式。故事借高小庭的视角讲述,但高小庭所讲的故事与历史事实和读者真实看法之间有裂隙进而形成张力,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反讽可以看做‘表面意思和实际所指之间的矛盾对立,它将实际意思掩藏在表象之下,使人无法锚定说话人的立场,由此产生某种模棱两可的疏离感。”[1]高小庭形象的经历与作者陆文夫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高形象的反讽性体现着陆文夫关于革命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一.无缘无故生爱憎——情感反讽
故事围绕朱自冶好吃与高小庭反吃四十年的斗争展开,“吃”在文本中既代表着一种基础的生存,也代表着充裕的物质享受。人们在几千年传统中把习惯于将吃看作不道德的浪费,如故事开头“吃喝小引”中就提到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孩子互相谩骂时也骂“不要脸,馋痨坯”。作者对“吃”这一题材的选取别具匠心,他在《美食家》后记中写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首先解决‘吃人的问题(鲁迅),那‘吃饭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是因为诸多并非偶然的历史因素,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的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吃人打主意”。
高小庭对朱自冶有一种似乎本能的厌恶、藐视与憎恨,将反对他视为己任,在开篇“吃喝小引”中就将自己的态度展露无遗,“碰到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冶以后,见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2]。高是穷学生时与朱的交往使他产生屈辱感,寄人篱下的高小庭在母亲的压力下从小走街串巷替朱跑腿买小吃,看到朱与一群朋友每天享受饕餮盛宴,来自贫民阶层强烈的反差让他同情街上吃不饱饭的叫花子并将自己视作他们中的一类,此种情感促使高走上革命的道路试图消灭剥削,拯救苏州。高小庭对朱自冶的恨来自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恨,他自觉代表一个阶级憎恨朱和他背后的另一个阶级,却忽略朱的个体性。
但讽刺的是,客观来看,朱在现实中不但没有剥削高小庭,反而经常帮助他:给他家免房租,给他挣跑腿费,也尊重高的妈妈。高小庭内心一度也认为他温暖仗义。高小庭对朱自冶的恨来自一个建构的模式,必须借助一个“神话”或者一个“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把朱自冶看成万恶的资本家群体,是他导致了社会的苦难和穷人的痛苦)。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情感结构”往往以一种稳定而又明确的结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最微妙、最难以捉摸的部分。它包含了一个时期内某些还没有找到外部对应物的共同经验,是对复杂社会经验的直接反映。[3]“我”对朱自冶的恨就来自特殊时代被灌输的此种“情感结构”。据此,“我”对朱自冶的情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分裂:既有基于自身个体情感的情谊与感激,也有基于时代情感结构的憎恶。陆文夫设置高小庭的视角展现这种情感的分裂构成情感反讽。
言为心声,高小庭在这样的情感结构下讲述故事的言语构成言语反讽。布鲁克斯曾言“反讽就是承受语境的压力”[4],高小庭的视角下的言语都带有他本人鲜明的情感倾向,语言与语境错位获得反讽效果。高小庭希望通过革命打倒朱自冶这样的蛀虫却没想到解放之后他过得更滋潤,“当我深夜被朱自冶的铃声吵醒之后,心中便升起一股烦恼,这苏州怎么还是他们的天堂?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时候,那寄生虫也会乘汤下面,养的更肥”,“我”在解放之后仍然沿用革命话语的一套逻辑显得滑稽可笑。高小庭因为心中不忿还去怂恿给朱自冶拉车的黄包车夫辞职,[2](p18)“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决不是给人家当牛做马的”“从古到今的车子,除掉火车与汽车之外,都是牛马拉的”,[2](p19)“我”在本分老实的阿二面前用革命话语搅弄是非,却害阿二丢了工作饿肚子。
作者有意将“我”的一套革命话语放置在明显不合时宜的语境中,这种语境误置能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语境压力造成言语变形进而产生言语字面义之外的潜台词,形成深刻的反讽,话语在新的语境下与原意疏离,进而对一切神圣的价值和权威进行嘲弄消解。
高小庭的这种情感倾向与读者基于故事事实认为的高对朱的应有态度形成反差,作者借高小庭的言语表述来塑造高小庭自身的形象。在他对朱的鄙弃中展现一个幼稚、极端且矛盾的革命者的心态,背后隐含的是作者真正的情感。作者对朱自冶自然是有批判调侃的,但也同样将高小庭置于审视和批判态度之下,这场关于“吃”的斗争中双方都不是胜利者。
二.郑重其事闹革命——行动反讽
作者设置高小庭视角不仅在人物叙述言语上造成局部反讽感受,更通过这一视点下的行动形成一种整体化的戏剧反讽效果。高小庭在故事中的许多行动带有荒谬性,他对于自己的革命行为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自我陶醉。高小庭本是带着消灭朱自冶一类人,解放苏州的雄心壮志奔赴战场投身革命的,“当时的心情有点像荆轲辞别高渐离。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净你身上的污垢”,不曾想“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枪炮声已经沉寂”[2](p13),只能灰溜溜无功而返;本来“再也不能让朱自冶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继续下去”,谁知道“取缔妓女,禁大烟,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2](p16)朱仍旧十分神气。
作者让高小庭带着一种严肃、宏大叙事的语调叙述自己的“革命行动”,每次轰轰烈烈地开场却惨淡收场,造成戏剧反讽的强烈效果。戏剧反讽效果来自于剧中人物對真相地不了解和观众读者对真相的了解之间的冲突,这种反讽对人物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是却能够对读者产生巨大的效应。高小庭自以为是的革命行为在读者眼中是幼稚、滑稽且缺乏意义的,他对于自己行为的无知看法的在全知事实的读者这里造成巨大的反讽效果。
韦恩·布斯为揭示戏剧性反讽的审美机制提出“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概念。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作者创造出来讲述故事的人,“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是价值观念和感情倾向与作者都不一致的叙述者,当作者采用不可靠的叙述者来组织故事时,读者就会对其讲述的故事和发表的议论产生质疑,戏剧性反讽就出现了。[5]高小庭就是陆文夫在作品中设置的“不可靠叙述者”,作者通过高小庭自己的言行展示其荒谬性和可笑处,进而反面呈现出作者的观点。
“这些带有荒谬性的生活题材、说话者有意加之的机智的夸饰都促使读者去注意言外之意。在荒诞之外探究隐含的深层次意蕴是读者和作者产生对话的有效途径。”[6]在名菜馆“我”大显身手努力改革,拆去霓虹灯,改造店堂款式和服务方式,让名菜变成家常菜,大众都消费得起。起初大家欢欣鼓舞,后来发菜品觉质量下降对“我”怨声载道,本是为着大众的改革却客观上造成了菜品味道的下降甚至对苏州饮食文化的破坏。“我”还在改革过程中培养助推了包坤年这样的投机分子,使他成为文革中检举诬陷“我”的凶手。这场荒诞改革最后以丁大头“我只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2] (p43)的结论结束,“我”的革新活动获得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讽刺效果,这一切的荒诞性来源于“我”作为革命者的不切实际和自我感动,透露着作者对幼稚的革命者的剖析与省察。
作品的反讽故事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剧中人高小庭看到的表象,另一个是读者体味到的事实。正是通过表象同事实二者之间的对立张力,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几经浮沉的陆文夫对于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在革命者与被革命者的关系这一点上陆文夫做出类似鲁迅对与五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深刻揭示,启蒙者有时自以为高高在上作出巨大贡献,实际不过是苍蝇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没有任何意义。“我”自以为“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结果历史却顾不得理睬我”。
三.思维同构作反省——总体反讽
高小庭是作者重点塑造的形象,它寄寓着陆文夫对革命者的反思,高小庭身上有陆文夫的影子:陆文夫本人也是1948年投身解放区,前期文艺思想亲近主流叙事,后来在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中几经沉浮,1978年平反回苏州后发表《献身》再度一炮而红。1983年发表的《美食家》充分体现陆文夫后期较为成熟的观点,高小庭这一形象身上寄寓着作者对于革命和文化的看法。
故事大部分以高小庭的视角展开叙事,他对于朱自冶的言说不具有有效性。而陆文夫正是在高小庭这种无效的言说中塑造高自身的形象并对之展开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作者作为曾经的革命者的自我省察。从革命时期走来的高小庭在建设时期仍然沿用不合时宜的革命改造方法,使他明明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苏州菜品改革行为变成了毁坏大众苏州美食文化的恶劣行径。“高小庭的革命理想是在对抽象的大众想象中建构完成的,大众的苦难、大众的力量、大众的抗争、大众的翻身等等构成一个完整的革命图式,其核心就是消弭了个体与个性差别的‘大众之神。”[7]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个体的舌头感觉千差万别、爱好各有不同,他们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事与愿违的改革结果体现着教条主义革命者在现实面前只能碰一鼻子灰。
在高小庭看似幽默轻松的叙述下,其实包含着作者对自己严苛的审视。陆文夫在复归文坛后没有简单从控诉或者反思中解脱自己,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对于灾难历史的控诉斥责,而蕴含着他作为主体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对于那一场运动和那一段历史进行批判,更是对卷入运动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反省,试图“干预人的灵魂”。
作者对于文化在新的时期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的警醒也在高小庭的叙述中体现。改革开放带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城市文化在与消费欲望对立统一中如何继续发展?高小庭的改革惨淡落幕后,朱自冶却因为“好吃”成为美食家,受人尊重和追捧,而投机分子包坤年抓住机会成立美食协会,这正体现了新时期某些文化现象。在作品结尾部分通过高小庭讲述他参与的盛宴与民宴,将新时期文化的走向消费还是民间两种路向呈现给读者。狂热的年代曾将高与朱一同展览,一同丢掷在居委会示众,打乱原来权力结构,但在新时期朱自冶、包坤年之类的人物再次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朱因为好吃成为专家,包因为组织活动和投机的能力成为副会长,在结局我收到了两份请帖,一份是学会主办的盛宴,一份是黄包车夫阿二儿女的婚宴,一个是奢华无比,体现着着新的权力在生成和交易,包想让“我”给朱在单位挂职,而“我”在这场类似“鸿门宴”的宴会中落荒而逃;另一个是热闹自然,亲切欢腾,但是以“我”抢夺外孙要吃的巧克力结尾,似乎预示着代表着下一代的“外孙”们将目光投向西方的“巧克力”,在民宴中也包藏着危机,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警醒。
八十年代初,阶级话语尚未消散,改革大潮再度兴起,《美食家》选取“吃”这一角度对革命话语、城市文化、消费欲望等问题进行思考,在“好吃”与“反吃”的历史斗争中建构政治革命话语与欲望消费话语的对立,并对两者均展开批判:既有对以往革命文化的冷静反思,也有对今日蒸蒸日上的消费文化的关注警惕。陆文夫试图在这两者之外开辟新的空间,为苏州文化发展寻得新的机会。如李徽昭所认为的:“《美食家》既有当代中国的政治反思,也有对饮食等日常生活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费与城市及时代的间性思考。在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间,《美食家》建构了欲望与消费的新观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锢的欲望与消费,从而成为时代变革的内在动力。”[8]
在总体叙事艺术上,陆文夫通过选取高小庭这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完成视点反讽,并通过当事人追忆回顾过去加强这一影响,从而达到一种总体性反讽的叙事效果,使得叙述人高小庭的一切情感/言语和行动/动作都带上了讽刺的丰富内涵。高小庭的思维结构的变化与作者具有内在统一性,由此揭示陆文夫本人对于对于革命历史的反思和当下文化的警醒的观点。由此,陆文夫《美食家》中高小庭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对高小庭形象进行反讽性解读能联结文本、作者与读者,达成新的阐释。
参考文献
[1]李思.论小说中反讽的伦理意义[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2).
[2]陆文夫.美食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谢菁.论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D].湘潭大学,2013.
[4]布鲁克斯.反讽———-种结构原则[J].“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
[5]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姜丽媛.《美食家》的荒诞性探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28(02).
[7]翟永明.舌尖上的世俗与革命——陆文夫《美食家》中的大众形象分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11).
[8]李徽昭.《美食家》:食以载“道”,或文化间性[J].小说评论,2022(03).
——由《苏州杂志》解读陆文夫的三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