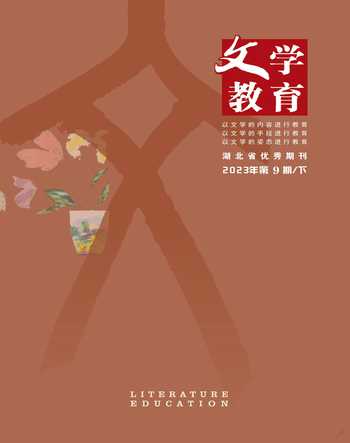福柯的语言与文学考古
陈思宇
内容摘要:为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于何时出现,法国哲学家、“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撰写专著《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并提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认识型规则。福柯在《词与物》中考察了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两次认识型断裂,而他的这一发现主要归功于其语言、文学考古。一度十分迷恋文学的福柯在深入探索西方各历史阶段的“语言”及“语言与文学之关系”的基础上,思考“知识”、“权力”、“主体化”间的联系并阐释各历史时期的认识型,由此得出作为某种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人之死亡、以人为中心的学科死亡的“人之死”结论。
关键词:福柯 《词与物》 语言 文学 认识型
20世纪60年代期间,语言与文学在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语言与文学主题不仅是福柯研究的参考对象,也是其话语分析的优先类别与研究對象。在福柯看来,“文学是一种话语空间”,是“话语操作和实践”[1]。福柯还将文学看作一种“外部的思想”,认为认识型使话语成为可能,而文学则可以帮助理解话语与不同认识型之间的连系。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于1966年出版之前,福柯对“话语”和“认知”的关注就已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年)与《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两部书中充分体现。
福柯不仅在写作中讲求修辞,注重行文风格,更擅于借助文学作品阐明自己的哲学思考。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曾通过分析“愚人船”这一文学主题,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不仅具有诗性特征,且与理性拥有平等地位、具有神圣的启示意义,而古典时代的“疯癫”则被理性征服,成为被驱逐的对象。福柯《词与物》的诞生灵感则来自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个文学文本,某部中国百科全书令人惊奇的分类让福柯看到了思想的界限,并让他进一步思索“相似性”的历史。
福柯的分析常常关注经验、客观领域或认知系统的构成及转变规则,企图揭示自古典时期以来,这些构成和转变如何成为可能,厘清作为我们思考出发点的“现代性”得以定义的条件。如果说《疯癫与文明》探寻的是“异”的历史,《词与物》考察的则是“一个文化能以何种方式以大规模和笼统的形式来设定作为其界限的差异”[2]的历史,是一个文化“借以能体验物之邻近的方式,它(文化)借以确立物与物相似关系图表以及物借以必须被考察的秩序的方式”[3]。在《词与物》庞大的人文考古系统中,福柯特别关注了语言、文学之考古,并经由对各历史阶段的“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分析,阐释各历史时期的认识型,发现西方文化认识型两大断裂(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最终得出“人之死”的结论。
一.语言的产生、消失、返回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世上原本只有“亚当语”这一种语言。上帝赋予人的原初语言是物“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通天塔之后,这一透明性被抹去,作为语言存在初始理由的相似性也被抹去了。如今,仅有留存下来的希伯来语以残片的形式保留了原初语言中的命名标记——存在物的固定属性。所有其他的语言不再与自己命名的物相似,语言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启示之所,是真理在其中被宣明、被陈述的空间的一部分。通过对不同国家语言书写方式的考察,福柯指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类推[4]关系,而语言的象征[5]功能不在词本身,要在语言的存在中,在其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中,在语言的空间和宇宙场所和形象的交叉中探寻。
16世纪末以前,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到“创建者”的作用,引导对文本的注释和解释、符号组织、使人类认识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相似性还“确定了认识形式(因为认识只能遵循相似性的路径)”[6],从而保证内容的丰富性,但正如培根抨击演绎法无法创造新的知识一样,这一时期的认识型具有“过剩”、“贫乏”的特征。再现和重复成了该阶段生活、认知领域的关键词,语言也只是“世界的镜子”。而相似性需要记号的标记,16世纪把诠释学和符号学重叠在相似性的形式之中,“探寻意义,就是阐明相似性;探索符号的规律,就是发现相似的事物”[7]。这一切“知识”都在认知对象外部包裹了一层纱。作为相似性与记号之重大分布的组成部分,语言要素的相似性法则被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以16世纪法国语法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为代表的学者寻找的是将词构建在一起的词之属性。
到了17世纪初,以相似性为特征的认识型开始变化。相似性成了谬误的原因。笛卡尔和培根的批判使古典思想排除了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相似性中的大杂烩”需要依据同一、差异、尺度和秩序而得到分析,阐释被分析取代。依据骑士文本寻找相似性的唐吉诃德最终没能证明自己,相似性与符号的古老联系解除了。物成为自己之所是,相似性消除,词不再标记物,语言符号对于它们所表象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虚构。语言中断了自己与物的古老关系,仅在成为文学时才重现其独立主权,相似性进入了一个对它而言“非理性和想象的时代”[8]。堂吉诃德的历险隐喻着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而语言从此拥有了全新的力量——史诗未实现的虚构成了“语言的表象力量”,词将自身的符号属性复归于自身。
福柯指出古典认识的唯名论特征。17、18世纪,语言是表象直接、自发的展开。表象在语言上获得了自己的原始符号,切割重组自己的共同特征并建立“同一或归属关系”,认识事物只能经由语言。然而,在《词与物》的开篇,福柯就已经借助对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宫娥》的分析,勾勒出了古典时期同一与差异之表象理论的认识型,让我们看到了“古典表象之表象”,也让我们理解作为表象与存在物间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语言”的消失。《宫娥》画面场景里的“真实中心”国王夫妇建构了全部表象情境,但两人所占据的真实的权力之点却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画面外的无,一个主体缺席的空隙”[9]。如同画中镜子里的国王与皇后,语言在古典时代的存在,至高无上,又不引人注目。至高无上是因为语言表现思想,能在身体外精确复制思想的副本,或者说古典时代的语言就是思想本身,然而“语言只有表象这一个处所”[10],语言只在表象中起作用,展现在挖掘自身而对自身进行的复制中,初始文本被渐渐抹去,词的基础被抹去,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言语符号中展开而成了话语。换言之,当表象理论作为秩序普遍基础消失,表象变成自我表象,语言的存在就也被排除了,剩下的只有语言在表象中的功能了——语言作为话语的本性和功效。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语言开始的地方不是表达,而是话语。普通语法,就是研究与同时性相关联的语词秩序,普通语法就是负责表现这一秩序。所以普通语法的适合对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语言,而是作为连续语词符号的话语。
自19世纪起,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认识型”开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对语法结构展开的独立分析使语言获得了自有的存在,语言开始关注自身,并获得其独特实在性,展开其独有的历史、客观性和法则,词之序不再是表象物之序,语言本身因而成为研究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词与物间产生分离。福柯进而列举了语言归于纯粹的对象地位而获得的三种方式的补偿:成为科学知识话语的中介;语言研究对“先天知识”的批判价值;文学的出现。语言随着文学的出现、注解的返回和语文学的构建以多样形式重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尼采和马拉美则将思想带回到语言本身。尼采不停追问“谁在讲话”,在思考“语言究竟是什么?”的同时,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尼采在语言的内在性中杀死了人。
二.新近的文学与人的消解
在《词与物》第八章中,福柯指出“文学”这个词是19世纪初“新近的”。在他看来,虽然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文学的诞生和传播从未停止,但那时对文学的辨读方式是根据已有的文学概念展开的。这类通过语言能指、所指的二元性被产生、分析的文学,依照的仍然是古典时代、尤其是17世纪以表象理论作为秩序的知识构型。在福柯看来,《堂吉诃德》之所以称得上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也正是因为它不断地用同一、差异去丈量符号和相似性。福柯从语言学和叙事学角度揭示了《堂吉诃德》在新旧文本间实现的重构与解构,说明《堂吉诃德》展现出的是以“同”及“模仿”为依据的“表象世界”。至18世纪,萨德侯爵的《朱斯蒂娜》和《朱丽叶》结束了由《堂吉诃德》开启的古典时代,支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那个表象世界也被颠倒了。萨德作品中喷涌的欲望直接摧毁了古典的修辞格,欲望被放回到表象之中,欲望、自由看似打破了严密的秩序,但欲望依旧依据表象之序得以表达和完成,“话语的秩序发现了自己最后的界限和规律”[11]。
19世纪,人们愈发关注文学把语言从语法带回到“说”的赤裸力量,文学在那里与词“原始且专断的存在”相遇。从海德格尔眼中最纯粹的诗人荷尔德林,到发现了词语“无能能力”状态的马拉美,再到维护癫狂体验的法国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文学以“反话语”的方式确立了自主存在,将自己与其他任何语言分离,从古典时代语言的再现和指称功能,回溯到自16世纪以来就被遗忘的这一原始存在。自马拉美以来,文学作为批评的专有对象,愈发不停地接近语言的真正存在,并由此激发了不再以批评为形式,而是评论为形式的第二语言。而马拉美试图以言语活动本身来取代从事言语实践时间的主体——“人”,这不仅预示着人在其从事的写作活动中的退场,更让福柯看到了“人之死”的征兆。
文学让语言的返回成为可能,更冲破了语言。在安托南·阿尔托、雷蒙·鲁塞尔的著作中,暴力、死亡的体验是先于语言的,在癫狂中体现。文学与超现实主义、与弗兰兹·卡夫卡、乔治·巴塔耶和莫里斯·布朗肖呈现出的死亡体验、不可思之思的体验、重复体验相连。文学总是“最接近语言,又最远离语言”[12]。文学作为语言实验,穿越于语言中获得体验,而在语言被不断结构化与形式化的过程中,“人”也被逐渐消隐了。
在《词与物》的最后,福柯指出:哲学的终结与有限性的思想、人在知识中的出现是同一件事。在哲学外反对哲学时,语言问题在文学中被提出。这一变化通过话语被表现出来。福柯将“人”与话语联系在一起,“因为整个現代认识型是与大写的话语及其单调的统治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语言向客观性方面的逐渐转变相联系的,是与语言多种多样的重新出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当语言注定散布时,人就被构建起来了,所以,当语言重新聚合时,人难道不会被驱散吗”[13]?
在古典时期,“人”是知识的主体,并不包括在知识之中。伴随着近代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人”由此成为知识的对象,“人”这个概念也得以出现。人的诞生是“认识型”变化的结果,伴随着认识型的再次变化,“主体的死亡”和“人”的消失也将发生。福柯认为,到了当代,人文科学被精神分析学、结构人类学、语言学所代替,人文科学并不导向“人”以及人的真理、本性、诞生、命运,而是关注系统、结构、组合、形式等(语言学分析的是结构,精神分析的对象是无意识,具有自由和存在的人消失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动摇了,主体不再是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人”并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认识主体和可知客体,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及产物。从一种考古学的观点来看,“现代认识型需要超出表象的知识中心,主体(人)被建构起来;‘人在语言的断片中建构了自己,也会随着语言、认识型的变化而走向消亡,被新的认识型所取代”[14]。综上可见,福柯所关注的“人”是人文学科意义上的“人”,而“人”的消解意味着关于人的学说、观念及学科的消解与死亡。
通观福柯一生的重要著述及其对知识、思想、权力展开研究的逻辑和谱系,我们看到福柯注重将考古学、历史、话语三者并置,将哲学作为诊断活动,形成其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借助对各历史阶段的“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福柯在《词与物》中阐明了人将随着以“人”作为研究中心的现代认识型一同消解的观点。他细密庞杂的论证也引发了对不同历史时期“语言”,“话语”和“文学”对“人”之影响的关注,为我们打开了重新审视语言、文学、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之门。
参考文献
[1]张中.文学的边界:福柯的文学“凝视”及其转折[J].法国研究,2011(4):1-11.
[2][3][6][7][8][10][11][12][13]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10, 10,31,32,51,82,216,389,391.
[4]福柯在《词与物》第二章区分了四种相似性,分别是“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其中,“类推”处理的是微妙关系的相似性,指从一个点拓展到无数关系.
[5]此处的“象征”取以类推方式表现其他物(符号)之意。
[9]张一兵.青年福柯与毕加索谁看走眼了?[N].中华读书报,2013/04/03:13.
[14]黄华.“人之死”何以成为可能——试论福柯的话语/主体理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5):105-108.
基金:本文受法国政府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及2022年法国驻华大使馆第二届人文与社会科学基金;河海大学2023年中央高校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社科基地项目(项目编号:B230207030);河海大学2023年国际合作交流引导资金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B23017051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