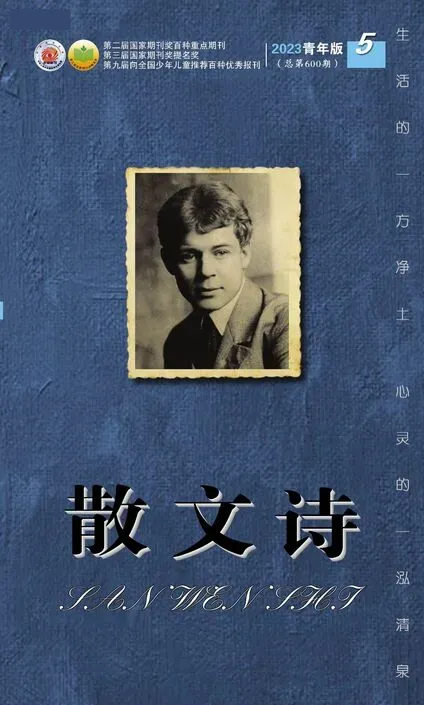舍尔舍涅维奇诗选
汪剑钊 译
瓦季姆•舍尔舍涅维奇(1893-1942),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之一。出生于一个法学教授家庭。7 岁时,父母离异,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自1907 年起,生活于莫斯科。在波利万诺夫中学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大学,起初在数学系,后转到历史-语文系。1911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春雪消融》。第二部诗集《Carmina》出版于1913 年,引起了诗坛前辈马尔科夫、古米廖夫的关注。这一时期,舍尔舍涅维奇的创作受到巴尔蒙特、勃洛克的很大影响,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特征。此后,他开始接近自我未来派的诗人,参与组织“诗歌顶楼”的活动,使用各种化名发表带有未来主义风格的作品,翻译意大利未来主义诗人马利涅蒂的关于未来主义的论述,撰写了《没有面具的未来主义》《最后说几句》等文章,但与立体未来主义、“离心机”等成员在创作观念上并不一致,遂导致了最后的分裂。十月革命以后,舍尔舍涅维奇与马利延戈夫、叶赛宁等一起推崇意象派风格的写作,写有《2×2=5》《我与谁握手》等理论文章,提出废除语法界限的极端主张,认为“形象就是目的本身”,“形象就是题材和内容”,宣称“诗歌一条主要的和出色的规律在于‘没有任何规律’”,在当时颇有影响,并于1919 年当选为全俄诗人协会主席。20年代,出版有诗集《马就是马》《快乐合作社》《如此结果》等。30 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戏剧翻译工作。1942 年,在巴尔瑙尔去世。他的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版,直到2000 年由学术项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诗与长诗》的诗集,堪称迄今最完备的一本诗歌汇编。
节奏的风景
大楼——
由钢铁和水泥建成的
大草垛。
雾——
往盛满香水的
杯子
倒进一点水。裁缝丈量过的街道的
弯折和断裂
是再次来自远方的
大雷雨助祭——惊雷。
广场的掌心——小溪的脉管。
在砖砌的司芬克斯肚子里
是我眼睛的帽饰,
我眼睛的双耳木桶。
铅笔狗有很多次
想挣脱锁链。
字母牙齿用唾液墨水书写纸的大腿。
大窗外有排水沟的皮护膝,
小窗后面有几普特重的凶狠。
齿缝之间的单词就像听话的羊拐子。
而摩天大楼上第7 层的骠骑兵
在入口将马刺碰得叮当响。
1919.8
爱的磨盘
一根沉重而陈旧的木棍,
捶打和磨研灰色的种子,
我们在脏炉膛里被火焰烘烤,
为了得到白面包填饱肚子。
脏抹布撕成碎片扔进水槽,
晃动摇杆作消遣
——又会怎样?
像一张雪白的纸片
从灵巧机器腹部爬了出来。
于是,我需要经历命运之牙,
在扎人的荨麻中脱下鞋子,
为的是重新看见洗白的自己,
让自己在你面前
显得非常温柔。
1923.7.6
城市狩猎
您惊恐地奔跑,丢失了面纱,
你们身后是一串尖叫和野蛮的吼喊,
人群沿着黑暗的大街四处奔走,
他们的叹息在您的肩膀上滑动。
狐梗狗和猎獾狗扑到脚下,
您向后仰起,抻直水笔,
从狂热的爱抚中解脱了出来,
仿佛终于不再受六月蚊虫的
叮咬。
您对某人低语:
“不需要!留着吧!”
您那白色的衣裙染上了污点,
但在您身后,歇斯底里地发誓并奔走着
人群、大楼,还有商店。
路灯与货亭挪移了原地,
一切都在您身后奔跑,大笑或尖叫,
唯有恶魔,看到这些场景,
从容地跟在您身后,撞击着
骨架。
1913.5.23
节奏的形象性
而今,这历史染血的活塞,
还在上帝之手的下面晃动,
如果你的嗓音如此衰弱,再一次
充满忧伤的皱纹,与我何干?!
俄罗斯骑着革命的扫把,穿过子夜,
去参加臆想的巫婆狂欢聚会!
哦,如果借助不可思议的欺辱
可以彻底抵消你的忧伤!
你的嗓音重新颤抖着古老的悲恸,
你的眼神重新拱曲,我的病女人!
我又一次描画前所未有的幸福蓝图,
希望入住你那无人栖居的心脏。
要知道,不是天神在焙烧人间的闲适!
诗行比烧灼的伤口更加滚烫!
与我何干?世界被熏呛得生疼,
如果你的眼睛在哭泣,我又爱莫能助!
但愿把烂疮的嘴巴张得更大一些,
能够用歌声将黑色命运向四处传播,
并且,就这样抓起衣领,
强行为你拽来不可言说的幸福!
1918.3
春雨
越过天空的一个个梯级,
穿越乌云,步履快捷,
你飘然而至,犹如一场春雨,
刷洗灵魂之中最后的积雪……
但是,狂躁的你并不知道,
那被犁铧翻耕到疲惫不堪的草地,
在白色覆盖物的遮蔽下,
忧愁和痛苦的残痕正在消融。
伴随着春天的絮语,
积雪逐渐在沉睡中融化,
但是,正如受到辱骂的旗帜,
大地的寂静保持沉默。
只有黑暗的沉默含着责备,
注视着你的眼睛:
你为何要用意外的耻辱
来欺凌这一份羞怯?
1911
来自最古老的世代
我迷信地珍藏的秘言,
来自最古老的世代:
“爱情不知道什么后悔,
谁若是悔恨,谁就不曾爱过。”
爱情,你比刽子手更残忍,
比生活更凶狠一百倍。
这些夜晚,北风更加凛冽,
超过了乌鸦翅膀的挥动。
在每一个初吻之上,
就有最后祭悼的安息香。
所以,尽管我们如此嫉妒,
却忍受着侮辱的愤怒。
你事先握紧了手枪,
热恋者,要明白自己的位置,
欲望那甜蜜的火焰,
有时与仇恨非常相似。
爱情!你的斗篷飘扬在世界上空,
可你的斗篷总有灾难的边饰。
你恐怖的眼睛闪烁犹如蓝宝石,
但其中更明显的是红宝石的印迹。
你不能阻止一切的诱惑,
我最后的爱情,
你可以扼杀,但不能欺骗
夜莺动人的创作。
1933-1935
孤独
我在郊外的小酒馆伤心,
美酒也不能愉悦灵魂,
银色的暴风雪扎入
已被狂风吹损的窗户。
马哈烟在幽暗的屋子里
缭绕着瓦蓝色的浓雾——
嗨!看呀,你从风雪之舞中
闪现,我的白雪公主!
从草地,从茂密的森林中,
从远方珍珠似的田野,
你显现,张开一对银色翅膀,
蓝色的雪地天鹅。
向我展示没有月光的道路,
尽管只是刹那间从迷雾中现身,
请用一只悲伤而冷酷的手
抚触一下我红肿的眼睛!
莫非必须我独自承担
这一痛苦而残酷的命运?
或者我必须独自一人躺进
被死亡沐香的雪松小屋?
空无一人!我独自在郊外,
痛饮苦涩的红酒,
还有凛冽的银色的暴风雪,
玩弄着破损的窗户。
没有什么词语比诗语更简洁
没有什么词语比诗语更简洁,
这是诗歌为何能够永恒的原因!
除了无忧之爱的权利,
没有什么其他罪恶更加神圣。
唉,时间中的一切瞬息即逝:
譬如生铁指挥官的脚步,
胜利的耻辱,暴力的恐惧——
只是心的梦呓已流淌无数世纪!
这就是为何透过艰苦的战斗,
我还能记得被腐烂包围的场景:
——任凭天空因为天堂而蔚蓝,
但蓝得更纯粹的是恋人的眼睛!
任凭血液鲜红——爱情更加鲜艳,
著名的紫红,刽子手的屠刀,
与它并列在一起,也会显得苍白,
甚至岁月因此得以赓续的夜晚!
哪怕烈性炸药发出的轰鸣,
哪怕叛乱的火焰
在到处燃烧——
初次表白一声胆怯的叹息
也可以压倒整个世界的喧嚣。
这就是为何爱情会绵延整个世纪,
尽管爱的生命只是夜的灰烬,
一个人念叨的爱之话语
却比诗歌的语言更加简洁!
1930
告别
你善变,就像女人,
那么,就挖苦吧,诟骂吧,幸灾乐祸吧,
哦,我有着取之不竭资源的
贫穷的祖国。
你与日俱增地好起来,
如此咸涩,又如此冷酷,
我们喝着美妙的饮品,
说着献给红脸颊岁月的祝辞。
你已永远忘掉,
祖国,你已彻底遗忘,
那些纷乱的岁月,
那时你对我多么眷爱!
哦,是你吗?或者我已不是?
但离别之后非常明显,
你的歌声不再响起,
我的沉默是如此苦涩。
请一定接受这最后的告别,
赶快,笑着接受,不要脸红,
你要将这一盒骨灰
放进最好博物馆的大厅。
要知道,一切并非彻底死去,
留存于你不自由的
兄弟式灵魂,
我是你忠诚的恋人,
真挚而又愚蠢的恋人。
193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