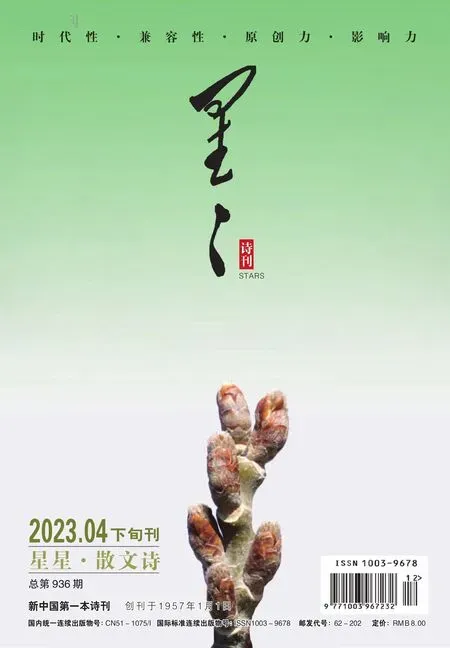走,听火车去(组章)
金小杰(山东)
摆 渡
七年了,每天都在出发。习惯了上课铃声分毫不差地响起,习惯了作业本上的圈圈画画,习惯了把同一条路反反复复地走成千上万遍。我,一尾破败不堪的小船,始终找不到桨,掌不了舵,被涨落回旋的流水推搡、裹挟。
教室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尾小船,船舷崭新,帆布洁白。一条条河流在教室里交汇,每一张课桌都是一处小小的码头。与其说船选择了河流,不如说河流在等一条合适的船。有人扬帆,在疾风劲吹的河面上远行,从此再无音讯。有人砍断桅杆,解开绳索,投奔一条河的风平浪静,长成岸边的蒲苇、芦笛,北风一吹,就扬出一生的苍白。还有人以手为桨,劈开浪花,奔向巍峨的雪山,或扬帆蔚蓝的大海。
七月,河流会变成锁链,凝成船锚,毕业的孩子们各奔东西,教室里只剩下找不到桨的我,在等另一批船。再或者,我根本没有船,只是一个渡口,把一只只船,用目光送得很远很远。
路 途
两点一线,从春天走到冬天。最先开的,不是迎春,是七里山阳坡的槐花,雪一样,把树枝压弯。每次上班,都是入山,和几条熟悉的河打打招呼,穿过大片大片的农田。路窄,桃花会在春天探出栅栏,央求每一个路人带走几片粉色的娇艳。
没有红绿灯,也不会堵车,偶尔会有大群的山羊,云朵一样,慢悠悠地在路上闲逛。果园里的雀儿被晨光惊飞,半透明的翅尖染上阳光的碎屑。比我更早的,只有初秋的露水,隆冬的寒霜,还有几次深秋的浓雾。我没有种豆南山下,也不必带月荷锄归,二十里外的小村,只有十一个孩子和站在坡上的风车,在生长,在旋转。
工作单位挪了几次,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学校更小,孩子更少。阳光透彻,一抬头,就可以望得见南山。浇花的间隙,会和孩子们谈论螳螂琥珀色的眼睛,谈论梧桐树叶这大自然的调色板,谈论头顶的太阳和围观的风。
两点一线,我终究和众人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十一个孩子,十一棵瘦弱的小豆苗,他们长成了我的南山,长出了暧暧远人村,也生出了依依墟里烟。
火 车
往北三里,有铁轨穿破平原。这坚硬的铁,像一根鱼骨,横亘在每个人的喉咙,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有很多人,会在时刻表上选一个班次,一个远方,候鸟般地飞走。
留下的,大多羽翼未丰,当然,我是个例外。上课,孩子们诵着“少小离家老大回”,窗外有叶子动了感情,颤了三颤,拖着日晒雨淋虫蛀的伤口,扑倒在树下。班里六岁的男孩,会在火车呼啸的瞬间,停顿,而后若无其事地诵着“乡音无改鬓毛衰”。他的妈妈打包起炊烟,打包起熟悉的平原,手里握着半张结婚证,推着他体弱多病的姐姐,变成了铁轨上最慢的半挂式火车,缓慢地出站。“妈妈过年就回家。”孩子不知情地说着。我看向窗外,不能否定,也不敢肯定。树叶大把大把地落,没有一片是秋天的答案。
此刻,我们都是听火车的人。阳光清脆响亮,山川明朗。或许,下一列火车,就会带着他的姐姐和妈妈,回家。
留 守
都走了,整个学校只剩下四个班级,五十多个孩子。当然,还有很多空教室,几年前孩子们诵读的回响,依旧隐隐传来。
这所建在小坡上的学校,树很多,鸟也很多。站在操场,可以望得见火车,一闪而过。还有风车,不急不缓地转着,像是校门口那排槐树,不知不觉地抽出密密匝匝的枝丫,遮笼住门前的小路,把天空的蔚蓝推得很远。偶尔,还有几只白底黑花的野猫,躺在闲置的乒乓球台上,晒着肚皮。操场上的落叶积了一层又一层,北风把它们推过去,又扫过来。满园的石榴熟了,同事们的年龄大了,树越长越高,人越长越矮,只有一群群长尾巴的喜鹊,在枝头跳来蹦去,啄得石榴籽落了一地。
办公室里,我是最年轻的那个,年轻得和他们的娃娃同龄。早晨开门,洒水,扫地,掏出纸质的备课本备课。不用敲击键盘,翻书,如敲木鱼,是每天的早课。村里断电,老教师们就会扯起绳子,敲醒比我年纪还大的铁铃铛。
门前的树叶黄了几次,铃铛响了几次,敲着敲着,打铃的人也退休走了。低头,那根绳子递交在我的手里。学校,更大更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