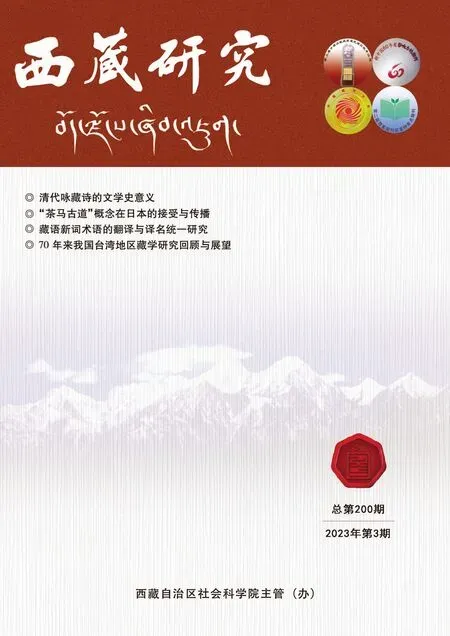“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构下青藏高原东部传统盐业的实践*
李何春 姚力尧
人类的生存、繁衍,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人类学、民族学、环境史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重点关注的对象。学界围绕如何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讨论,并从“环境决定论”逐渐转向“环境可能论”,再到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表明,人类在长达一万年以上的时间里,主要靠采集和狩猎活动获取生存资料。这个阶段,人类大多以适应环境为主,自然环境对人类实践能力的限制程度较强;但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改造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转变为主动实践。不过,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却出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分改造,或是从自然界中过度攫取物质资料,难免造成生态破坏,从而引发泥石流、沙尘暴等自然灾害。此外,汽车尾气的排放、森林资源的枯竭,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已引发全人类担忧。例如,有学者提到:“生态危机使人类直面自身如何生存的问题,为了突破生态困境,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不断地重新思考。”(1)李安君:《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吉首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46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到“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为我们探讨今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如何适应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生存技艺:青藏高原东部的传统晒盐业
青藏高原具有地广人稀、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等特点,并对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就西藏自治区全境而言,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面积达122.84万平方千米,截至2021年底人口只有366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2.1人。因此,学界曾产生“青藏高原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论调。后来,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们世代繁衍至今,不仅寻求了最佳的生存策略,还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例如,学者指出:“数千年前,在当地藏族民众与环境的交流与互动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尊重自然和自然法则,形成了自己的‘朴素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机制。”(Thousands of years ago,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Tibet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people living in this area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and lifestyle.In this they paid great respect to Nature and her laws,formed their “plain culture” and a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4)Luorong Zhandui,Fan Yibin.“A study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from Tibetans in Kailash Sacred Landscape(KSL)”,China Tibetology,No 1,March 2011,p.64.另一学者指出,藏族民众凭借其传统游牧文化,在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适应、磨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运行的‘文化生态共同体’”。(5)皇甫睿:《藏北高原的“清道夫”——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西藏牛粪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87页。显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在从事每一项实践活动中通常需要形成一套适应环境的机制,这充分显示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而言,最重要的生态资源包括草场、中药材(如虫草、贝母、黄连等)、菌类(如松茸)等;生存资料也必不可少,主要包括牛、羊、马等畜类;除此之外,盐是青藏高原较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仅人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盐,发达的畜牧业每年也要消耗大量食盐。然而,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盐业资源分布并不广泛,仅有藏北的湖盐和藏东的井盐;由于藏北路途遥远、荒无人烟,藏东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想要获取食盐非常困难。
西藏东部的盐井,分布在昌都市芒康县境内,位于滇藏交界处。国道214线正好穿过盐井,该地区交通便利,是西藏入滇的门户。此处距离云南德钦县城仅110公里。澜沧江谷底的岩缝中,天然的盐泉冒出地表,为当地民众提供源源不断的卤水资源,并至少在明代已懂得利用风力和光照进行汲卤晒盐。在澜沧江河谷,藏族和纳西族采用“架木为田”的方式,在两岸的山坡和台地上修筑晒盐平台,通过汲卤、背卤(或挑卤)、晒卤、收盐四个环节,获取食盐,通常称之为“藏盐”。据调查,盐井实为“纳西民族乡”(这里是西藏地区唯一的纳西族聚居区),辖上盐井、下盐井(又称纳西村)、加达、觉龙4个行政村;其中上盐井、下盐井和加达3个行政村的村民,长期以晒盐营生。加达村坐落在澜沧江的西岸,拥有2400多块盐田;上盐井村坐落在澜沧江的东岸,并靠北端,拥有700多块盐田;下盐井村,同处澜沧江的东岸,位于上盐井村的南面,拥有近500块盐田。历史上,盐井长期被当地的寺庙和土司控制,盐税由二者收取。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时期收回盐权后实行官办,积极推动当地的盐业发展,实现盐务机关征收盐税。民国时期,川边社会混乱,盐井亦被地方僧权和俗权控制。1950年3月,盐井解放。此后,盐业由当地县政府组织生产,并于1959年开始征收盐税,1980年实行免征盐税。1985年,芒康县撤销人民公社,盐田分给农户。目前,盐业由盐户自行组织生产和销售。
澜沧江上游的青海省囊谦县境内的8个盐场(6)包括达改、拉藏、娘(牛)日洼、白扎、乃格、然木、尕羊和多伦多8个盐场。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境内的甲桑卡盐田,同样采用传统的晒盐方式。上述9个盐场,采用“垒石为畦”的方式,提(引)卤晒盐。囊谦县的8个盐场,主要分布在香达镇、白扎乡、娘拉、着晓和尕羊等乡镇。从调查来看,囊谦8个盐场中盐畦数最少的为然木盐场,数量仅为84块,最多的为白扎盐场,数量在700块左右,其他盐场盐畦数为100—500块,8个盐场一共有3000多块盐田。
20世纪20年代末,学界开始注意到青藏高原东部存在着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制盐技术——晒盐法。考古学界认为青藏高原东部的囊谦传统晒盐工艺,是在“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创造、完善了这一独特且经济、适用的盐业生产工艺,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7)王玥、陈亮:《玉树州囊谦县盐场与盐业文化的调查研究》,《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第100页。因此,今天存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传统制盐工艺充分显示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研究传统晒盐工艺的“活化石”。
二、 盐民的“自然化实践”:传统晒盐工艺的策略
孙九霞等人提出“人的自然化实践”(8)孙九霞、王钰宁、庞兆玲:《基于生活实践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西藏夏乌村案例》,《地理科学》2022年第5期,第756页。概念,这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笔者认为“人的自然化实践”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同自然界产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不断适应自然环境的策略选择。青藏高原东部囊谦县和芒康县两地的盐民,采用传统晒盐技术获取食盐的过程,主要包含以下三种策略。
(一)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策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核心是二者相互依存,特别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要防止过度开发,以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那么,青藏高原东部的盐民是如何合理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的呢?
第一,在整个传统晒盐工艺流程中,除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外,修筑上述两个地区盐田(9)青海省囊谦县境内称之为“盐畦”。所需材料均取自所处的生态环境。芒康县用木料架成木楼,木楼上方修建平台,成为盐田的基础。盐田底部先用木料平铺,再用沙石铺垫,最后再铺一层特殊的红泥。储卤池,则利用江边的石头和鹅卵石修筑而成。运送卤水的卤水桶、树皮桶、盐田拍、刮盐板、盐框、盐箕、扫帚等,均利用盐井周围的木料、竹子、草等植物根茎制作而成。囊谦县各盐场的情况和芒康县盐井有相同之处。例如,修筑盐畦所用的石料、鹅卵石、泥土,均取自盐场周围的环境。木拍、盐锤、耙子等工具,多为木制。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芒康县的盐田修建在木楼之上,大小基本相同,形状较为规则;而囊谦县各盐场的盐畦,则直接修建在台地上,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但二者均尽可能使用自然环境中的材料是较为普遍的。
第二,利用地势从高到低“引卤”。这种现象在芒康县的盐井并不明显,其原因是盐泉出口低于江面,所修建的盐田多高于盐泉。但囊谦县的8个盐场中,仅有白扎和娘日洼两个盐场的卤水井和盐畦同处一个水平线,需要人工挑运卤水,其他6个盐场选择将盐畦修建在低于盐泉的平地上。通过引流的方式,即可让卤水自然流到盐场,省去了运卤环节,不仅节省了劳动力,简便的引流工程对环境的破坏力也极小。
(二)预防人地冲突策略
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任何一个生存群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能遇到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冲突矛盾逐渐明显。无论是芒康县盐井,还是囊谦的8个盐场,盐民从事晒盐业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处理晒盐用地、住房用地和农作物种植用地之间的关系,以下分别对上述两个县的情况进行讨论。
芒康县的盐井地处澜沧江河谷,东岸地势险峻,并不利于修筑盐田,盐民只得将盐田修筑在陡峭的悬崖之上。若将盐田修筑到相对平坦的土地上,则会造成食盐生产和农业种植用地之间的冲突。这在澜沧江西岸的加达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加达村地处澜沧江西岸,该处形成了约4平方公里的台地。这块台地显然成为晒盐、农业种植和修建房屋最佳之地。然而,加达村的盐户,并未将盐田修建在台地上,而是修建在靠近江面的坡地上。为了充分利用土地,本村所修筑的卤水井,甚至已延伸至江内。盐民的住所也分布在一条溪流两侧的坡地上。显然,村民充分认识到人地存在的冲突,从而有意避开晒盐、居住和农业用地的矛盾。
囊谦县的8个盐场,由于所处海拔保持在3000—4000米,农业种植极为稀少。此时,盐民主要处理晒盐、畜牧业和住房等用地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囊谦县境内多数为草甸,地势平缓,因此上述用地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很突显。人地关系的处理,主要表现在村庄距离大型盐场较近,便于从事晒盐业,但需要保证拥有足够的土地用于修筑盐畦。而那些小型盐场,需要合理布局盐工住所和晒盐用地,并用围栏将盐畦封闭起来,避免牲畜进入盐场破坏盐畦。
(三)食盐分级销售策略
青藏高原东部的各个盐场,采用传统晒盐方式获得的盐巴,相比较于“煎煮法”和“真空法”两种制盐方式,其杂质较多,盐质稍逊。其主要原因是,盐田底部多数铺垫鹅卵石或红土,晒盐过程中容易造成盐结晶体和杂质混杂在一起。因人畜对食盐的消费等级不同,收盐时技术娴熟的盐工主要负责刮盐,并将收获的盐巴分为不同等级。据民国时期崔克信的调查,芒康县盐井收盐时,按照次序,将含有不同杂质的盐分为不同等级。
扫一次扫时复分三次,计第一次,□当盐水干约七成时,用擦斯板将盐面轻刮一遍,稍□再将浮面花盐刮入盐袋中,袋置于盐田及水塘间堤上,浸出盐水,即注入塘中,不致损失,第二次扫时,在盐干后,先用扫帚轻扫一遍,再用擦斯板将盐刮起,倒入袋中,第三次再将余盐扫净,以砂泥湿□,故多掺入盐中,第一次刮取之盐质最纯,属桃花盐,第二次次之,称二道盐,第三次最劣,称三道盐。(10)崔克信:《盐井县之地质及盐产调查》,《西康经济季刊》1944年第8期,第182页。
将食盐分为不同等级,主要考虑的是人畜的不同需求,以及盐质对销售价格的影响。囊谦县的8个盐场,普遍将盐分为两个等级,分类标准依然按照收盐时的工序,上层为一道盐,下层为二道盐;前者为一等盐,供藏族民众食用,后者为二等盐,用于喂养牦牛、山羊、绵羊等牲畜。若二道盐的盐质不佳,则直接判定为三等盐。在芒康县的盐井,一、二道盐对应着一等盐和二等盐,可供当地的百姓食用,三道盐(即“三等盐”)喂养牲畜。由于盐井江东岸和西岸的土壤不同,东岸可生产白盐,西岸则生产红盐。白盐和红盐的价格也有区别,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白盐各等级价格分别为一等盐100—120元/百斤,二等盐70—80元/百斤,三等盐40—50元/百斤;红盐的价格为一等盐100元/百斤,二等盐60—70元/百斤,三等盐35—45元/百斤。(11)李何春:《动力与桎梏: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何国强主编:《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页。近几年随着市场变化以及晒盐户的减少,每一等级的食盐均上浮5—10元/百斤。囊谦县各盐场所产之盐,价格要比芒康县略低。一等盐的价格为80元/百斤,二等盐价格在30—50元/百斤。
芒康县和囊谦县两个盐区,针对消费群体不同,将食盐分为不同等级,有利于分类销售所生产的食盐,能够较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并在短时期内销售完毕。这也是盐民的一种生产策略。
三、生存有“道”:传统盐业实践中的原则
青藏高原东部的人们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懂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稳定而可持续的生计模式。传统晒盐业在青藏高原已延续了800多年,且经久不衰。这反映了盐民在从事晒盐业的过程中,遵循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修建盐神:感恩自然界赐予的尊重原则
据调查,在囊谦县的8个盐场中,可以直接观察到达改、娘日洼和尕羊3个盐场修建了盐神。以娘日洼为例,在盐畦的西面高出盐畦五六米的地方,建有一座塔状的盐神(见图1左侧图片),藏语称为“乐拖”。盐神总共分三层,底座由石头砌成,呈正方形,边长为2.1米,高出地面0.4米。在底座上,又用石头砌成墩状的正方体,边长为1.9米,高为0.9米。最高部分为塔尖,内部用木料捆绑成圆柱体状,外面用经幡包裹,高约2.2米,整个盐神高3.5米左右。达改盐场的盐神,则全部用水泥浇筑而成(见图1右侧图片)。

图1:囊谦县盐神的外观手绘图
除上述3个盐场外,多伦多盐场未修建盐神,但盐泉出口上方自然形成的土堆上挂满了经幡,如同供奉了盐神。盐神的供奉,在当地盐民看来,有两方面功能:一是感恩自然界的赐予,能为盐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卤水资源;二是保佑整个盐场能够顺利开展晒盐活动。白扎盐场,虽未修建盐神,但笔者在调查期间,从盐民口中得知该盐场曾受到高僧放置宝瓶的庇护。据了解,“噶玛巴一世杜松虔巴(1110—1193年)于75岁时在类乌齐创建尕玛巴寺,每次他路过白扎都要为社稷施放宝瓶,乞求平安”。(12)坚赞才旦、王霞:《百味之首在澜沧江源头——青海囊谦泉盐产销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0页。这一信息来源于一位叫丁达的老盐工,他出生在白扎盐场;1972年9月,丁达开始在白扎盐场工作,他讲述了盐工在平整白扎盐畦的过程中发现了放置在井底的宝瓶。
一天中午,盐工在挖井时突然从井中发现一个宝瓶,质地为粗陶,外部镶嵌宝石,发现后交给一位叫江章金的汉族干部(盐场经理)。因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江接过来端详了一阵,认为是封建迷信物就砸了。事后我向一位耄耋老翁请教,方知宝瓶是噶玛巴活佛的法器,内装各色吉祥物,放置宝瓶是祈求如意清静,一般在盐场东面神山放一个宝瓶,再在盐场卤井中放一个宝瓶,东西对应,故只需继续挖掘,还会挖出宝瓶来。果不其然,翌日又从卤水井中挖出几个宝瓶。(13)笔者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坚赞才旦教授一同调查获得的资料。调查对象:丁达;调查地点:囊谦县城;调查时间:2017年8月17日。
丁达还对两位调查者说道:“每一世噶玛巴活佛经过白扎盐场的时候,都要在井底放置一个宝瓶,祈求当地平安。”这也验证了井中挖出多个宝瓶一事。
(二)依势而建:顺应自然的最小化改造原则
西藏芒康县和青海囊谦县两地境内均采用传统晒盐方式,以构筑晒盐的基础(“平台”之意)而言,前者采用的是“架木为田”,后者采用的是“垒石为畦”。
在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泉自澜沧江河谷的两侧山体中自然冒出地表。当地的藏族和纳西族依照盐泉四周的地势,修筑盐田,汲卤晒盐。但是,澜沧江峡谷沟壑纵深、地势险要,两岸多为地势陡峭的坡地,并无平坦的土地可供晒盐。于是人们在陡壁上架起木楼,楼顶上再修筑盐田,即“盐田之式,土人于大江两岸层层架木,界以叮畦,俨若内地水田”。(14)段鹏瑞撰:《巴塘盐井乡土志》,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宣统二年(1910年),第13页。盐楼整体上是两位一体的建筑样式,木料支撑的结构统称为“盐楼”,地势陡峭的盐楼下方常建有储卤池或盐仓,以此达到空间的合理利用。(15)李何春:《动力与桎梏: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何国强主编:《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第40页。据调查,这样的盐楼在盐井一共三四百座,盐田一共3500多块。
囊谦境内的8个盐场,人们同样利用当地平缓的地形修建晒盐的基础设施。早期盐业生产者,依盐场所处地势,在台地或坡地上垒石为“畦”,引卤晒盐。通过调查发现,解放以前修建的盐畦,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此类形状的盐畦,主要特点是对地势改造不大,盐畦较为分散,且面积较小。目前所见的大多数盐畦,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修建的。报道人回忆称,这类盐畦修筑的时间大概在农业学大寨期间。(16)丁达,原娘日洼盐场的经理,访谈时间:2018年4月24日,访谈地点:囊谦县城。此后修建的盐畦,对大量坡地进行改造,一般先平整土地,再修筑盐畦;因此盐畦呈水平状,样式规范,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每块盐畦之间彼此相连。在晒盐季节放眼望去,整个盐场似一片雪地,十分壮观。8个盐场修筑的盐畦,外观上虽有一定差异,但修筑方式基本相同。多数盐畦建在空旷的坪地上,通常以石料为基础,修筑类似南方地区的水田,底部铺设鹅卵石,呈方块形状,称之为“盐畦”。
(三)以“能”代薪:绿色能源的利用与保护自然原则
无论是芒康县盐井,还是囊谦境内的8个盐场采用的传统晒盐技术,均与采用“煎煮法”制盐截然不同。“煎煮法”制盐,需要燃烧柴薪或煤炭提供“热能”,使铁锅中的卤水沸腾后蒸发、结晶,获得食盐;“晒盐法”则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使盐田(或“盐畦”)中的卤水蒸发,获取食盐。
从海拔来看,西藏芒康县的盐井处在2200—2600米之间,两侧的高山海拔均超过3300米。囊谦县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多数盐场所处海拔在3600米以上,其中白扎、然木、尕羊3处盐场的海拔均超过4000米。按照青藏高原东部森林资源呈垂直气候分布的特征,海拔在2500—3000米,多数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较低。以盐井来说,澜沧江河谷两侧高山上的植物多以荆棘为主,仅在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山峻岭,分布有一定森林资源。但这些林场,通常远离盐区,柴薪运输十分困难。囊谦县的多数地区则海拔在3000米以上,为草甸或高山草场,极少部分地区分布有森林,并不能提供燃料。
通过分析盐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可以看到利用燃料熬制盐巴的生产工艺需要大量柴薪,这种制盐技术往往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引发自然灾害。例如,李源较早注意到盐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云南盐业生产历史时期,木柴是熬盐的唯一燃料。由于长期乱砍滥伐,不事培育,各井场周围百里之内,童山秃岭,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每届雨季往往诱发洪灾、泥石流和滑坡等灾害。”(17)李源:《云南盐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井矿盐》1990年第6期,第43页。
囊谦本无丰富的森林资源,亦无煤炭、天然气等燃料,因此只能另寻他法。尽管囊谦的生态环境不能与盐井相提并论,但二者采用相同的晒盐技术,表明各盐场所处的自然条件略有相同。据金飞所述,盐井“既无煤矿,又乏柴薪,蛮民摊晒之法,构木为架,平面以柴花密铺如台,上涂以泥,中间微凹,注水寸许,全仗风日。”(18)金飞:《盐井县考》,《边政》1931年第8期,第2页。清末,有文献指出盐井曾“拟改用煎熬之法,一经提炼,色味俱佳”,但又继续提到“惟关外向无煤矿,全用山柴,成本几增二十余倍,只可暂仍其旧”。(19)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写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6页。可见盐井也曾推广煎煮法,但生态环境客观上不支持采用此法。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需要不断克服困难并寻找最佳的生存策略。尽管盐井和囊谦两地缺乏燃料,不具备熬盐的条件,但当地的太阳能和风能可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为当地民众从事晒盐业提供了良好条件。据分析,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青藏高原东部澜沧江河谷风力大,日照强,“晒盐法”是海拔、气候、光照时长、风力等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据研究,芒康县的盐井处于“S”形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南北方向吹来的风于此段峡谷交汇,在曲折凹形的地势下形成强劲的风势。峡谷形成了风洞效应,满江满坡都是风,带走了盐场的水汽,阳光灿烂的日子蒸发作用特别强。(20)李何春:《动力与桎梏:澜沧江峡谷的盐与税》,何国强主编:《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系列二,第28页。盐井属于干热河谷气候,按照金飞的描述是“常年多南风,昼夜不息,房舍遇有罅隙,风力无时无处不到,触之令人头晕气塞。”(21)段鹏瑞撰:《巴塘盐井乡土志》,第4页。由于光照直射盐田表面,因此中午地表温度可达28—30℃,而澜沧江流经盐井,水的吸热和放热过程提高了当地的气温。因此,日照强、风力大、气温高,对卤水的自然蒸发十分有利。
囊谦地区,虽然年平均气温低,但极端最高气温可达29℃,盐畦受阳光直射,温度更高。据调查,囊谦的8个盐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盐场多数处在河谷或上坡斜面,以至四面吹来的风力到达盐场之后,风力集中、加大。囊谦地区晒盐原理和盐井相似,有利于盐畦的水分蒸发。
风力和太阳能的利用,是藏东传统晒盐技术适应自然环境较为明显的特征。风力和太阳能,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属于绿色能源,还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因此,为了克服气候和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囊谦还是盐井,晒盐都是季节性的生产形式。囊谦以每年的3—8月为晒盐季节,这时正是囊谦气温最高、雨(雪)水较少、干燥的好气候。而在盐井,产盐季节为10月至次年的3月。这是因为盐井海拔比囊谦低,冬天并未全部积雪。干燥的气候,成为晒盐的好条件。
上述盐场有效利用了风能和太阳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小,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能源的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东部采用传统晒盐法获得的食盐成本不高、价格低廉,因此在滇藏之间销售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有人曾拿滇西北喇井熬制的盐巴和西藏芒康县晒制的沙盐进行价格上的对比,得出“喇盐距墩(德钦)十余站,道远费钜,砂(沙)盐地近价廉,无论如何核减万难抵制。”(22)吴强、李培林、和丽琨编著:《民国云南盐业档案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442页。这也是传统晒盐业的一大优势。
青藏高原东部的两个盐区,在传统的晒盐实践中,通过不断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利用一切自然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将传统晒盐工艺传承了近800年,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命共同体”。传统晒盐工艺是青藏高原东部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民族地区的畜牧业和旅游业发展,以及盐民的经济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最重要的是,传统的晒盐生计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并为“三江源”(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积极努力。总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是一句空话,是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反思,并需以实际行动不断践行,才能真正建构起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