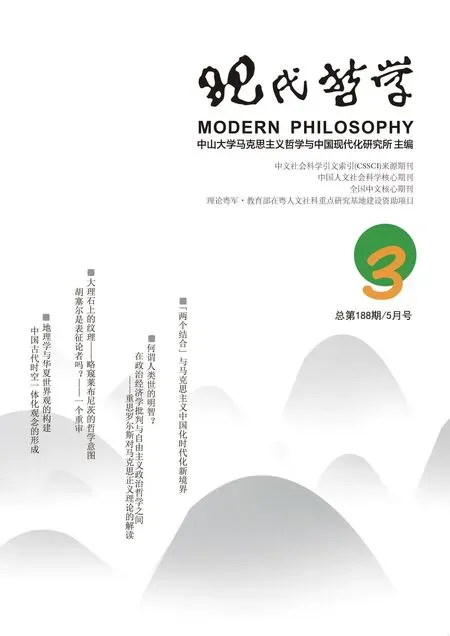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
刘晓峰
本文旨在讨论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过程,试图从对这一过程的讨论中,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如何产生和发展,并建构起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体系化过程,是一个将大自然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变化一体化的过程。而中国古代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则是将时间和空间一体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互相联系的。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看,时空一体化,是结合天文、人文为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上经·贲》,《周易本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4页。中国古代世界的时空观,是一个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独特世界,在这个世界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性,是天文与人文的结合,是科学的客观观察和瑰丽的人文想象的结合,这一文化理性推导出来的合天地人神于一体的世界图式是中国古代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框架,其影响及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祭祀、仪礼、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意义重大而悠远。仅以国家祭祀体系讲,到清朝结束为止,整个中国古代的祭祀仪礼的编排,就一直是依循这一图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巨大文明的精神底盘,这一世界图式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依旧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作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一份精神遗产,这部分文化传统也需要我们努力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清理这一传统的形成过程,描述清楚其基本结构,认识其主要特征,并在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一、时空一体化:中国古代时空观的核心特征
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角度考察,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体系。这个体系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被时间化,从而结构成一个时空一体化的时空观体系,如图1所展示的五行与时空的对应关系。在这里,东方同时代表春天;南方同时代表夏天;西方同时代表秋天;北方同时代表冬天;中央同时代表季夏。在这个体系中,时间和空间互相咬合,构成一个融天地于一体的时空一体化世界图式。这是一个由东与春、南与夏、西与秋、北与冬、中与季夏组成的基本时空图式。这个图式与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等配合,就是古代中国世界最基本的时空体系。
这一时空体系很早就出现了。《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明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0页。这里东与春、南与夏、中与季夏、西与秋、北与冬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对应关系。正如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所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时。”(3)[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页。四季与四方的对应关系,是建立在天地之间的,是“中”与“六合”结构成世界的整体模式的一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对应关系的史料。如《管子·轻重己》中已经有了春始天子东祭,秋季天子西祭,冬至天子北祭,因为“夏”者明也。天子所处为夏,所以夏至天子不出祭。又因为天子执中而治,中为黄,所以天子“服黄而静处”。这里面四方与四季明显存在对应关系。这一图式后来出现在《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礼记·月令》、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等一系列文献中,使这种对应关系更有了体系化的展现。
传世文献中,《礼记·月令》是有关时空一体化观念最典型的文本之一。《月令》以月系事,依循自然时序变化编写而成。它融自然、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于一身,囊括农事、礼乐、政教、兵刑等多方面内容为一体,是研究中国古代时空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有关《月令》的叙事的逻辑线索,蔡邕《月令章句》有非常好的阐释: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言佐然后列昆虫之列。物有形可见,然后音声可闻,故陈音。有音然后淸浊可听,故言钟律音声可以彰,故陈酸羶之属也。群品以著,五行为用。于人然后宗而祀之,故陈五祀。此以上者,圣人记事之次也。东风以下者,效初气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后人君承天时行庶政,故言帝者居处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节,所明钦若昊天,然后奉天时也。(4)[清]阮元校刻:《月令第六》,《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清嘉庆刊本)卷14,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30页。“法象莫大乎天地”,阮元校刻(清嘉庆刊本)为“奠”,实际应为“莫”,故用“莫”。阮元校刻(清嘉庆刊本)原文中无标点,本文引文加标点,下同。
这里蔡邕所讲的“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引自《周易·系辞下》,“奉天”以“建春”者,就是依天地、日月运行而确定四时起始。《礼记·月令》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层面组合的天、地、人、神的世界结构。这是一个独特的、由内在的逻辑线索编排起来的时空世界。这个线索的核心就是时空一体化的内在秩序。“天地有上下之形,阴阳有生成之理,日月有运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5)同上,第2927页。,《礼记·月令》所言日之所在,天干所系、帝与佐、虫、音、律、味、祀与祭之用脏,均为这一秩序的具体化。即便是人间的君王,也要为这一秩序所支配。按规定,王要按月份居住于明堂的不同居室。这里说的明堂,是按照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建造的特殊建筑空间。按照《周书》的记载,其建制是“明堂方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左为左介,右为右介”(6)[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玲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50页。前句标明“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533引《周书明堂》”。。按照《礼记·月令》的规定,王不仅要按照月份变化移动住所,而且王的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也都要依照时序而变化。时间与空间的一体化已经从季节与空间的对应,发展到人王与月份与空间的对应。在这里,天、地、人已经完全一体化。
内含于《礼记·月令》中的这套时空一体化的思想观念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它是汉以后古代中国的基本世界图式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古代人的祭祀、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举例说,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套时空观依旧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可以说,时空一体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最有符号化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春峰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化思维方式,曾专门撰写《“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7)金春峰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思维方式。(参见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26-159页。);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也对中国古代的时空混同的神话宇宙观进行研究(8)参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8页。。本文就是在上述先行研究基础上,围绕时空一体化观念是如何产生、什么因素推动古代中国人将时空一体化的思想发展起来等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事物产生必有其契机,事物发展变化必有其动力。那么,时空一体化观念产生的契机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以下从北斗七星的发现、季风的影响、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发展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二、北斗七星的发现
北斗七星勺柄指向规律性的发现,是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形成非常重要的契机。在中国古代世界,如《史记·天官书》所云,北斗七星以中央临治四方,地位崇高,拥有很多重要功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9)[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天官书第五》,《史记》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1页。北斗七星在中国古代的星空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偶然。肉眼观察下,北斗七星在夜空旋转一匝的时间,正与一个自然年相同。《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10)黄怀信撰:《环流第五》,《鹖冠子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0-71页。《淮南子·天文训》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11)[汉]刘安编、何宁撰:《天文训》,《淮南子集释》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8页。这两段话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北斗在十二辰之间的周年运行过程,特别是注意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方向与季节变化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正是这种同步关系极大激发了古人的想象力,北斗七星也被赋予各种特殊含义。《尚书纬》释“七政”云:“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为七政。”(12)《尚书纬》,[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3页;[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4页。《史记·律书》则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徳,即从斯之谓也。”(13)[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律书第三》,《史记》卷25,第1253页。
我们头顶的北斗七星,在地球同纬度都看得到,不同民族间有一些想象是相似的,例如中国古人想象“斗为帝车”、在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神话里北斗是主神恩利尔的战车、在北欧神话里有北斗是天神奥丁战车的说法、丹麦人称北斗为“查理之车”;有一些想象则不相同,比如英国人、爱尔兰人认为北斗是一架犁,德国人、匈牙利人认为它是一辆手推车,芬兰认为它是捕鲑鱼的网,还有人将斗勺部分视为船帆。在古希腊,北斗七星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斗柄是熊尾巴。北美洲易洛魁人认为,北斗七星的前四颗星是熊,斗柄三颗星是三个追熊的猎人,这三个猎人分工明确,或执弓箭,或执锅,或执烧柴。在其他民族那里,我们找不到将这七颗星与周年时间的复杂联系,也找不到给北斗七星赋予如此复杂的文化含义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民族对于星空进行想象的文化基础不同。
那么,古代中国人对于星空进行想象的文化基础是怎样的?《淮南子·天文训》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又云“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14)[汉]刘安编、何宁撰:《天文训》,《淮南子集释》卷3,第207页。。这二绳、四钩、四维作为维系天地之间的图式,广泛见于秦汉式盘、“博局纹”铜镜以及日晷等出土文物,可知这是古代人长期共有的时空知识。下面我们围绕对北斗七星的认识过程,回溯一下这一整套知识体系的形成脉络。
先说“帝张四维”。有关“四维”,古籍中只有《淮南子》记载了“四维”的具体名字,即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羊之维和蹄通之维。认真看一下这些称谓,会发现它们跟古代人对太阳的认识有非常深的关系。“常羊”和“背羊”的“羊”通“阳”。“报德”与“背羊”是呼应的。古代人观察太阳,是取早晨、正午和黄昏三个时间点。报德之维这条线产生于将一年的太阳运行轨迹平面化后一年冬至日升之点。而“背羊”之维这条线产生于将一年的太阳运行轨迹平面化后夏至日落之点。冬至为日照时间最短之日,冬至后日升点、日落点不断变长,一直到夏至这个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时间点,这是一个阳线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大地化生万物、生长万物的过程,故称“报德”(15)《月令》“东风解冻”高诱注云:“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发于南方,自阴复阳,故曰报德之维。”。到夏至日,太阳从东南升起,开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故称“常羊(阳)”,而背阳之维得名于从夏至这个日照时间最长的点开始,日落点会一天天不断变短。所以报德、常羊、背羊这三称呼可以说都得名于太阳的变化。西北比较特殊,“蹄通之维”的得名应该跟古代“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的神话有关。按照神话的叙述,因为共工撞断了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实际上是一个与中国广域地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有关的神话。天倾西北,西北多高山、有昆仑,“蹄通”说的就是西北地势之高,交通之不便,只有动物才能走得过去。所以四维中西北一维说的是大地,其他三维说的都是太阳周年的变化。《淮南子》中四维的称谓和太阳变化之间的关联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演进过程中,四隅的方位确定最早应该是出于对太阳的观测,出于观测太阳的东升西落。所以我们的四隅称谓是以东西为轴,称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传统的汉语词汇体系中却很少有北东、南东、南西、北西的说法。“四正”“四隅”构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八卦方位,加上中央一点合而为九,这就是九宫,是中国古代时空观中将大地这个巨大空间划分为九州这一空间想象的起点。
再说“运之以斗”。中国古人对于北斗七星时空指向性意识应当出现在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确认东南西北“四正”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这“四隅”以后,“运之以斗”与太阳周年运动有重要关联。这一点从“开阳”“摇光”这两颗位置重要的星辰如何称谓中就能看到痕迹。当古人想象的天盘上出现汇集于中央的四正、四隅八条线后,才可能发现和确认星空中北斗七星周年的变化规律。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这两颗被称为“开阳”和“摇光”的星斗之间的连线,即确定北斗七星勺柄指向的连线。这是一条按照季节变化与从中央向四维、四隅辐射的“线”相互重合的“线”。斗柄这条线一年的旋转过程是和四季的变化一一对应的。在这种对应关系中,一个着重点是“开阳”和“摇光”两颗星之间的连线和东北报德之维与西南背羊之维的重合。“开阳”和“摇光”两颗星之间的连线和东北报德之维重合之时,就是一年大地回春的起点;和西南背羊之维重合之时,就是一年万物入秋的开始。“开阳”和“摇光”两颗星之间的连线所指方位的变化,就这样获得标志季节变化的功能。这是中国古代先民在北斗七星和时间体系之间建立关联的起点,也是古人把北斗七星想象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根本依据(16)我们从汉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星与星之间画上这样连线的星图,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图像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古代星图中二十八星宿也经常用连线方式表示。笔者认为,“开阳”和“摇光”两颗星之间的这条连线,很可能就是最初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星与星之间连线的开始,是这条线开启了星间连线并赋予连线各种想象的先河。。
阿伦特曾经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论及望远镜的发明,认为发明望远镜看似是最不起眼的事件,但却在根本意义上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观,因为望远镜的发明第一次让人类拥有了地球之外的视角,通过望远镜,人类才得以从遥远的宇宙视角来看待自身。(17)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实际上,和望远镜出现同样重要的还有显微镜的发明。望远镜将人类的视域推向更远的领域,显微镜将人类的视域深入到微观的领域。在这样的工具出现之前,肉眼是人类观察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手段。在远古时代,我们先民发现的北斗七星和时间体系之间的上述关联,是那个时代肉眼可见范围内能准确确认的科学知识,是一年又一年都经得起实际检验的知识。对北斗七星斗柄周年指向变化的观察,和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上的多重文化想象,是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形成的重要的契机。
中国古代的时空认识发展过程是先有对太阳的观察确认了方位,然后有对北斗七星斗柄指向变化的发现,最后形成了对斗柄指向和季节变迁之间对应关系的认识。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文献中可见的对天廷的想象却是以星辰为主的。这主要是因为白昼太阳独行于天上,其形象尽管足以阐释“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道理,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白昼的天上根本没办法安排王以下的臣子的位置,而夜晚的星空则给了中国古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围绕固定不动的北极星,中国人把满天的繁星编织成秩序井然的序列。和季节变化同周期旋转的北斗星指向的周年变化在这个星空谱系中被赋予司时、司政以至司命的崇高位置。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察和记载天上发生的诸多变化——日食和月食、星辰移动的轨迹以及彗星的出没,但古代司天者不是按照今天科学的逻辑去观测这些现象,支撑他们观测活动的主观世界,是对各种天文现象充满想象的理解和认识。北斗七星后来被看成管理人间生命的司命之神,其影响巨大到在道教、在佛教信仰中都可以找到。从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这一文化脉络上,也生长起来一系列非常丰富的文化。可以说,古代人对于北斗七星的理解,是中国人古代时空观想象的一部分,而北斗七星斗柄指向变化与四季的同步,对古人的时空一体化观念产生提供了契机和巨大的推动力。
三、季风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季风气候,对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形成有重要影响。古代人对于风有自己的理解。《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18)周鸿飞、范涛点校:《黄帝内经素问》,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风的重要性在于将天地联系起来。古人又认为风与雨相关。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风调雨顺是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最重要的保证。中原地区处于季风带的影响之下,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东风、西风、南风、北风的变化和季节变化之间的关系。文献上有关风的知识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有关殷商时代对风的认识,胡厚宣、李学勤等先学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胡厚宣根据殷墟甲骨中刻有四方风名的卜辞提出殷人已有四时观念,且四方与四时相配。(19)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第49-51页。李学勤则提出“四方风”为“东方风曰析风曰协,南方风曰因风曰凯,西方风曰彝风曰韦,北方风曰伏风曰役”,视“四方风”的存在为殷商有四时的证据。“四方风”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殷商时代已经出现四季的重要观点。(20)李学勤:《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79-183页。同时殷商时代的先民已经将四方与四时相配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他们对风与季节之间的关系有了非常准确的认识。四方风后来被进一步细化为“八风”,即东北风、东风、东南风、南风、西南风、西风、西北风和北风。以下作为参考,我们将《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黄帝内经》《太公兵书》《易纬》以及《左传》注释中有关八风的部分史料排列成下表:

出典/八风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吕氏春秋·有始》炎风滔风熏风巨风凄风飂风厉风寒风《淮南子·天文训》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淮南子·堕形训》炎风条风景风巨风凉风飂风丽风寒风《说文解字·风部》融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吕氏春秋》高诱注炎风融风滔风明庶风勋风清明风巨风凯风凄风凉风飕风阊阖风厉风不周风寒风广漠风《灵枢·九宫八风篇》凶风婴儿风弱风大弱风谋风刚风折风大刚风
从这一表格可以看出,古代对于八风的称谓明显有不同的系统。这些不同的称谓系统告诉我们,古代认识八风路径可能不是单线的、单一起源的,而是多线索、多区域、多元的。我们知道,古代先民对于东、南、西、北“四正”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的认识确立得很早。冯时指出,测定方位的技术“至迟在公元前第五千纪,先民显然已经懂得在测定了东、西、南、北四正方向之后,可以通过平分四方而得到八方,从而完成对更为复杂的空间方位的规划。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发现契刻于陶器底部的九宫图像,与同处淮水流域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汝阴侯墓所出太一九宫式盘天盘上的九宫图如出一辙,显示出一种源远流长的时空传统”。(21)冯时:《奉时圭臬,经纬天人——圭表的作用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史知识》2015年第3期,第11页。而认识到八方、风的方位与季节之间联系的历史很可能也很古老,在神话传说中这种联系被直接上推到黄帝、颛顼的时代。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之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于戏,允哉!朕何敢与焉!”(《韩诗外传》)(22)[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278页。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鳝先为乐倡,鳝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吕氏春秋·古乐》)(23)[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仲夏纪第五》,《吕氏春秋集释》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3-124页。
这里出现的“举动八风,气应时雨”“八风之音”等观念,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断言,但在文献上至少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四方风被进一步细化为“八风”,并且已经存在相关一系列知识的记载。例如,《左传》中出现了4次“八风”:
(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24)吴闿生撰、白兆麟点校:《隐公之难》,《左传微》卷1,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3-4页。
(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25)吴闿生撰、白兆麟点校:《吴季札让国》,《左传微》卷7,第376-377页。
(昭公二十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26)吴闿生撰、白兆麟点校:《齐陈氏之大》,《左传微》卷9,第480页。
(昭公二十五年)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27)吴闿生撰、白兆麟点校:《王子朝之乱》,《左传微》卷9,第499-500页。
从隐公五年这段文字的文脉分析,对话中记载的舞乐制度并不是鲁隐公时代的独创,而是明显有更古老的传承。季札观乐这段文字里的“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显然讲的是周乐的音乐精神。后面两段引文中的“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中的“八风”,从前后文脉看也不是孤立的知识点,而是和一系列古代相关知识相互联系的。上引《韩诗外传》《吕氏春秋》中的“举动八风,气应时雨”“八风之音”也是如此。这清楚地反映出古代中国先民认识的八风,并不仅仅限于我们科学意义上来自八个方向的风,而是已经编入中国古代时空文化之中的八风,是不断被与八节、八方、八卦、与乐与时间相联系加以认识的一整套非常复杂的知识,并且是了解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极为重要的知识。沈祖绵《八风考略》在条理文献资料后,对八风与八方的关系做了提纲挈领的总结:
风应八方,诸家无异说,要皆殊途同归。有以八方解之者,有以八节八卦解之者,有以八方八卦解之者,有以八卦八音解之者,有以八方八节八卦解之者,有以卦气解之者,有以八方、十二子、二十四节中、二十八舍解之者,因人事日繁,立说亦日密,至其起原,似先由四方,及于八方,变及八卦,变由八卦而及于八音,其一说也。又有以四时及于八节,由八节而后及于十二子,二十四节中,六十卦气,七十二候,其说二也。(28)沈祖绵撰、沈廷发注释:《八风考略》,《周易研究》1995年第2期,第13页。
前文说过中国古代人对于风有自己的理解,风的重要性在于将天地联系起来。古人又认为风与雨相关。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风调雨顺,正是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最重要的保证。在中国古代世界中,季风变化不是孤单的存在,而被看成是宇宙万物变化的一部分,是被一个更高的“律”所支配的,即所谓“八风从律而不奸”。“律”乃是这个世界阴阳变化的节奏。《后汉书·律历志》云:“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也就是说,律上与太阳周年日影的变化同步,下与大地上的声音相共鸣。中国古人就这样在日影观察到的太阳周年运行的变化规律、大地上声音的变化和风之间建立了神秘的联系。有关律的产生因其内容过于丰富,需要另文专述。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季风的风向变化和农业生产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农耕生产靠天吃饭,先有风调雨顺,才有国泰民安。所以古代中原地带的季风气候,才是这一整套有关风的知识得以形成的客观基础。古代人有关“八风”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中的风认真观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之上的。这一观察和把握的原动力,是中国古代农业努力掌握季节变化规律而利用之的美好愿望。从时空观念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八风知识框架的季风与季节之间的对应关系,起到联通天地之间的作用,为中国时空一体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
四、农耕文化是最重要的基础
对于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如果说北斗七星勺柄指向与季节之间的同步性的发现是契机,八风和季节变化之间的同步性是有力的支撑,那么农耕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产生的最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发轫于农耕生产过程。考古学告诉我们,在文字出现前,南北中国已经有漫长的农业发展的历史。南方以水稻为中心、北方以黍为中心的农耕生活都有非常漫长的发展历史,最长甚至需要以万年为单位计量。如此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对这个世界一定会产生复杂而体系的认识。从时空观念的发展而言,农业生产的根本点是合理掌握农作物生长周期,按照季节的变化安排农作物的播种、照顾农作物生长和收获、储存农作物。农业生产让人们对时间的周期性变化认识越来越深刻。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间在空间中每一天都处在周期性轮转之中;这又是一个规律性变化的过程,空间随着时间的轮转而不断发生周期性变化。这里谈到的周期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具体的物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认识到天地之间的联动性。东风起处,春雷一响,万物惊蛰,土地慢慢变得松软,春天播种的季节到了。秋风起处,万物一天天变得枯黄,纷纷结实打籽,劳作者进入收获季节。这样以年为单位循环的生产生活周期中,人们与大自然密切接触,发现了很多具有时间标志性的自然变化。这不仅仅是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也是疾风的轮动,是动物的繁殖期、角、羽、毛的生长、禽鸟的迁徙、植物发芽、开花、结籽、凋落,雷、雨、霜、露、冰、雪出现的时期,等等。每一个自然年的变化,农作物每一年的生长变化,都不是抽象的四季变迁,而是一个天地联动、万物在同一时间节奏中周而复始变化的过程。从事农耕生产的劳动者每天劳作在自然之中,他们对自然一天又一天随季节迁化而出现的各种变化有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感受。这也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物候所占比例非常大的原因。
构成这个过程发生空间的天与地,在中国古代被看成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最典型地表现为天圆地方的观念。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产生得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挖掘出了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可见远古的人们就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方地为舆,圆天为盖”(宋玉《大言赋》),天地日月升降于此舆盖之间,四季轮转于此舆盖之间。流转于天地之间的季节,和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关联,构成一种将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整体性动态视角,用古代的话语,就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六合”。六合就是“宇内”,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圆地方、二绳四维、斗为帝车、八风从律,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的正是一个“六合”的宇宙想象。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化观念则是这一宇宙想象核心的组成部分。
依据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原则,天地万物的运行都在同一秩序中,都在按照同一节奏不断变化。惟其如此,“春王正月”这个简单的历法叙述,才会与“大一统”思想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背后,正是时空一体化思想观念。天地万物都在同一秩序中以同一节奏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公羊传》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9)刘尚慈译注:《隐公》,《春秋公羊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何休《公羊解诂》于“大一统也”下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30)[清]王闿运撰、黄巽斋点校:《春秋隐公经传解诂弟一》,《春秋公羊传笺》,湖南:岳麓书社,2009年,第142页。是王者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的边界,不止于人自身,而是囊括了“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沿着这一线索发展出来的古代时间,乃是政治化的时间。杨向奎指出:“何休诂‘一统’虽然与今人诂‘一统’之义有别,但其大一统实真正之大一统,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昆虫草木,莫不系于‘正月’,也就是系于‘王纲’之政令,正月为政教之始,统一于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颁布之正朔法令。”(31)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71页。年始和月始,就这样被赋予“更为初始”的特殊含义。明乎于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政权更替之后要改“正朔”。因为推动周边国家使用中国的“正朔”,不仅仅是推动一本历法的使用,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里,时间就是秩序,就是一个政权进行支配的重要象征。
五、结 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经指出:“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32)[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钱婉约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文明独特的发展进程正与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建构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先民们不仅基于对天地物象的观察和体认,对一年季节与气候的同期性变化和与之密切联系的天文与物候的同期性变化产生了规律性认识,从中抽象出一套完整的时空观念,结构出一整套世界构造和运行逻辑,从而建立起中国古代的时间文化体系。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是这一体系中一个最为鲜明的整体特征。沿着时空一体化的方向,中国古代思想进入“纳五行于四时”的结构过程中,其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月令图式的完成。
本文从北斗七星、季风和农耕文化这三个角度,对古代先民如何形成时空一体化观念进行了初步讨论,以期揭示古代中国形成时空一体化观念的主要契机、支撑和基础。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中国的时空一体化观念,是基于古人对大自然时间变化的科学观察形成的。在人类只能依靠肉眼观测世界的时代,不论是对北斗七星斗柄旋转方向与季节同步关系的认识,还是对季风与季节风向同步变化的认识,以及通过对动植物物象、物候季节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性把握,都令我们从中看到古人如何努力拓展对时间变化加以把握的维度,看到古人为把握大自然时间变化规律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与此同时,从古代中国的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得到中国古人对这个世界存在方式的神话性的浪漫想象。由天圆地方、二绳四维组合而成的六合世界的世界图式想象,是以时间文化体系为核心结构而成的。尽管这一图式与我们今天的世界存在很大距离,但却是那个时代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早期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思想底色。建立在这些观察和想象之上的古代思维方式,古代人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价值观念取向,曾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于这一时间文化体系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一直是东亚以至于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化体系之一。这一时间文化体系将四时万物变化的规律或总趋势高度概括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个阶段,对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种物候和气候都有系统的描述,并且融汇天地为一体,融汇人与自然为一体,以象数变动为基本框架,为人与人的社会给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规定。这一原生的时间文化体系,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内核,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宝贵的结晶体,其间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巨大潜力。这部分内容是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古典学的核心。
立足中西比较的立场看,时空一体化是中国古代时空观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和西方思想中的时间观念相对比,差异非常鲜明。金春峰早已注意到这种差别,并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角度做过论述:“在西方,古希腊很早就产生了纯时间与空间观念。亚里斯多德在其范畴表中,分析了时间与空间范畴,提出时间与空间本身加以界说。时空单位是客观的时空的量度。这种时空观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疑起了极其有利的作用。但在‘月令’图式中,时间却是与空间结合的。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西方与秋相结,由金主持。北方与冬相结合,由水主持。土则兼管中央与四季。作为地上及地上皇权的代表,土在天人关系中,实际是人的代表。因此,不仅没有脱离特定空间的纯时间观念,亦没有脱离特定时间的纯空间观念。”(33)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129页。到了牛顿的时代,时间与空间已经完全独立。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相信绝对时间,相信人们可以准确地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西方思想流变中,区别时间和空间,有一个清楚的发展脉络。这与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化观念的演进过程是非常不同的。
近代以来,我们经常追问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西文明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东西方文化源头的时空观上的差异,实为影响东西方文化走向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时空一体化的时空观对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举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大一统思想,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联想式思维、象数思维、在变化中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等,都与时空一体化密切相关。对古代中国人的时空一体化思想观念的考察和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认识整个中华文明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