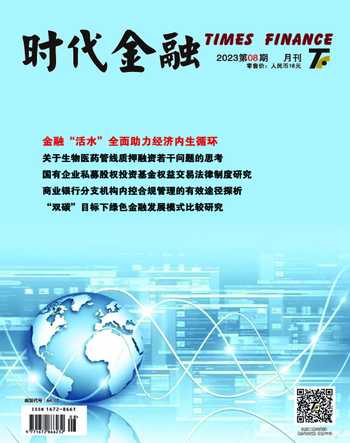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张晓 李鹏举
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包括国有企业转让其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份额,也包括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转让其对外投资所形成的企业股权(产权)。该类交易行为是否适用《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32号令”)进场交易的规制,是实务和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旨在结合实务操作,梳理相关核心问题涉及的法律制度规定,厘清基础概念,对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或国有基金对外投资所持股权转让是否应当进场交易进行分析。
一、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交易法律制度及问题提出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起步发展较晚,目前虽然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对国有私募股权基金尚未出台专门的监管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长期面临着是否适用32号令进场交易的合规困惑。
(一)国有资产交易规定
1.国有资产交易类型。国有资产(权益)交易是指依法将国家对企业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国有资产交易在法律适用和交易程序上,适用特殊的规则,除了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转让协议的约定外,还受到国资监管制度约束和规制。根据32号令的规定,现行国有资产交易行为包括“企业产权转让、企业增资、企业资产转让”三大类。
2.强制进场交易制度。国有资产交易在形式上,《企业国有资产法》、32号令等规定了“强制进场交易制度”,除了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均应进场交易。另外,在进场交易中,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国有资产交易还应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并申请评估备案。
3.有限合伙企业国有权益登记规定。2020年2月7日,国资委印发《有限合伙企业国有权益登记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登记规定》),要求国家出资企业(不含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及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各级子企业对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及其分布状况进行登记。
根据《登记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及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各级子企业对有限合伙企业形成的权益均构成国有权益,国有权益需按照该规定办理相应的有限合伙企业国有权益的占有登记、变动登记和注销登记。目前《登记规定》已经开始在国资管理体系内正式推行和实施。
(二)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权益交易是否适用32号令
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包括国有企业转让其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的权益(份额),也包括国有有限合伙企业转让其对外投资所形成的企业产权。该交易行为是否受32号令监管,目前并无统一明确的规定,现实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实践。
1.不同观点及理由。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权益(份额)交易属于国有资产交易范畴,应适用32号令的约束和规制。因为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32号令的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转让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权益的行为[1],并未明确排除合伙企业适用。对于一些不适用的情形也有明确的规定,如32号令第66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各类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形成企业产(股)权对外转让,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以及出台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国有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不作国有股东认定”。
也有观点认为应进行区别处理,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份額应当适用32号令,因为产权转让主要看转让方的性质,不考虑目标企业的性质,但对于国有性质的有限合伙企业转让其对外投资形成的企业产权,不适用32号令,因为转让方有限合伙企业不被认定为国有股东。该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国有企业性质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属于32号令第4条规定的国有企业。
2.实务操作及官方回复。该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也存在着争议,表现为部分国有企业转让所持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采取进场交易的方式,但同时也存在未进场完成交易的案例。[2]
此外,国资委也在其官网上分别于2018年12月29日、2019年5月27日、2022年4月3日以问答形式明确:32号令规范的对象是公司制企业的情形。国有企业处置其持有的有限合伙企业中的份额,不在32号令规范范围,合伙企业中合伙人的权益和义务应以合伙协议中的约定为依据,建议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履行决策批准和资产评估及备案等工作程序。同时,国资委官网问答中提及“上述回复仅供参考”,该回复不属于法律法规,回复内容不够全面、表述也不够清晰,因而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32号令第3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转让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权益的行为”属于国有资产交易行为,第4条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国有企业做了规定,但没有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属于该范围。因此,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权益交易是否适用32号令取决于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的理解。[3]
二、私募股权基金权益交易中“国有企业”的法律制度
(一)“国有企业”的概念
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进行统一的定义。在国资监管领域,与“国有企业”概念并存的,还有“国家出资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等概念,不仅增加了理解难度,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外延边界等也容易产生争议。这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识别这类公司具有法律适用上的重要意义。[4]
1.国家出资企业。《企业国有资产法》通篇没有出现“国有企业”一词,而是以资本结构为基础创造了“国家出资企业”这一新概念。结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条第2款、第11条、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仅指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如地方各级国资委、财政部门等)直接出资的“一级企业”,不包括“二级企业”及以下级别的企业。2018年,国资委在其网站“互动交流”栏目,就国家出资企业概念理解问题作出回复时指出,“由国家出资企业出资设立的子企业不属于国家直接出资的企业,但国家出资企业的国有资本出资人权益,通过国家出资企业的投资延伸到子企业”。该回复一方面明确了“国家出资企业所出资企业”不是“国家出资企业”,另一方面又明确了“国家出资企业所出资企业”应当接受监管。[5]
2.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从该规定看,国有独资公司只能是“一级企业”,且必须是“独资”“公司制”,比国家出资企业的范围还要窄,与“国有企业”涵盖的范围相去甚远。
“国有独资公司”适用公司法,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国有独资企业”一般指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调整。
3.国有资产交易中的“国有企业”。确定国有资产交易领域国有企业的内涵外延,是适用交易规则的前提,也是处理国资交易一切实务问题的基础。32号令对国有资产交易中的“国有企业”作了较为清晰的界定,32号令第4条规定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的范围,明确了国有资产交易中关于“国有企业”的判断标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目前认定国有企业的主流观点。[6]
(二)有限合伙制形式的“国有企业”能否担任普通合伙人
对于“国有企业”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从字面意思理解,“国有企业”不能担任普通合伙人,包括不能在有限合伙中担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其实是对该法律条款的误解,此处的“国有企业”应该特指国有独资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
如前文所述,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独资企业都由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通常并列出现。《合伙企业法》将国有企业与国有独资公司并列,在“国有企业”无统一确定法律法规定义的情形下,此处应做狭义理解,将其理解为国有独资企业在体系上更为合适。在实践操作中,工商登记的“国有企业”专指国家出资一级企业,不包括国有全资及控股参股子企业。[7]
因而,现行《合伙企业法》第3条之“国有企业”应采狭义之理解,即专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有独资企业,不是32号令“国有企业”的广义概念。
(三)国有有限合伙企业的认定
当前,并没有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具体界定。32号令第3条对国有资产交易的几种类型进行了规定,如前所述,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权益交易是否适用32号令取决于该合伙企业是否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实践中,可以结合该基金国有企业持股份额多少、该基金的实际控制权、国有企业是否是GP等进行综合判断。[8]
笔者认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性质认定应该按照32号令第4条的规定,优先判断持股份额。在份额单独或合计不足50%,但国有股东为第一大股东且能实际支配该合伙企业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适用32号令关于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管规定。
三、国有资产不进场交易协议的效力问题
32号令第3条、第4条界定了适用国有资产交易的“三类主体”和“三种行为”,总的来说,“三类主体”从事“三种行为”应当进场交易,并以交易为前提履行批准、审计评估、进场交易三类程序。32号令规定了“强制进场交易制度”,由此也产生了关于效力的争议,即如果未履行进场交易,其产权交易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一)协议效力的法律规范——《民法典》与《九民纪要》
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9]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該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10]该规定将合同法司法解释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上升为了法律。
2019年《九民纪要》对“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根据《九民纪要》规定内容,在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中,“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这两项,与国资交易进场交易联系最为密切,在司法实践中对违反进场交易合同效力的判定需要进行综合判断,因而,未进场交易的协议效力性问题在规范层面上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协议效力的司法实务层面——不同判例
违反进场交易是否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截然相反的判例。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4期刊载了“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纠纷案”。该案例最终以交易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交易行为违反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交易行为无效。但最高法在安联公司诉安恒达公司案例中却最终确认了场外交易协议的效力。
四、结语
按照现行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投资设立或参与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属于32号令的“国有企业”,其权益交易行为建议遵守32号令强制进场交易的规定。
与此同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频繁且对效率要求高,如果将其与一般国有企业产权交易适用相同的交易监管制度,在实务中会产生较大的困难,当下的交易合规困境即根源于此。因此,国资监管机构在制定出台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统一的管理办法时,在明确交易监管要求时,应充分考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殊性,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促进国有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交易有序开展,推动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发展。
注释:
[1]佟杉杉.国有资产法律实务与疑难问题[M],法律出版社,北京,2021年版,241页.
[2]佟杉杉.国有资产法律实务与疑难问题[M],法律出版社,北京,2021年版,241页.
[3]唐入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有权益管理法律制度的思考及重构[J],产权导刊,北京,2021年.
[4]王军.公司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9-10页.
[5]罗锋.中国法律年鉴[M],中国法律出版社,北京,2007年.
[6]佟杉杉.国有资产法律实务与疑难问题[M],法律出版社,北京,2021年版,241页.
[7]梁欣欣.有限合伙债权人利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广州,2011年.
[8]刘小进,郭晓锋.国有私募基金退出问题法律探究[J],产权导刊,北京,2022年4月.
[9]程啸.合同法一本通[M],法律出版社,北京,2019年版,121页.
[10]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M],法律出版社,北京,2020年版,36页.
作者单位: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