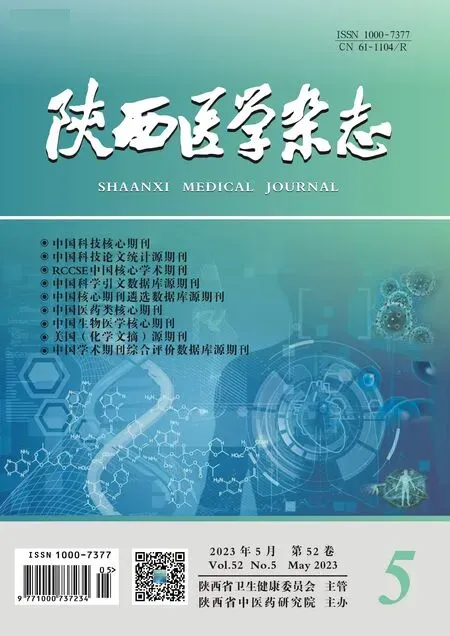产后腹直肌分离影像评估与康复治疗研究进展
谭良源,甘小凤,卢栋明,林雪婷,杨培培,王开龙
(1.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广西 南宁530200;2.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530023)
腹直肌分离(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DRA)是指以腹白线(Linea alba,LA)为轴线的左右两侧腹直肌横向距离异常延长而并非真正地分离,故DRA又可视为腹直肌间距(Iner recti distance,IRD)异常增宽[1-2],以妊娠、分娩及产后的妇女最为常见,也见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妇女、未生育的女性、男性及儿童[3-6]。其形态特征表现为腹部肌肉松弛、腹中线梭形隆起以及沿中线以异常的距离横向分开但无筋膜缺损[2,7]。尽管分娩后腹直肌在一定时期内可自行恢复至生理状态,但仍有部分女性处于持续性分离状态[4,8],同时会伴发腰-骨盆带疼痛、盆腔脏器脱垂、二便失禁及腹疝等问题,影响形体美观及生活质量[9-10]。随着人民对高质量健康生活水平的追求,逐渐意识到DRA的危害性,精准、有效、健全的现代康复诊疗技术已经成为医学界研究的热点。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发现,尽管当前对DRA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并未统一,但影像和康复技术在腹直肌分离的评估和治疗中的普遍应用为其提供了客观依据。本文从腹直肌分离的研究现状、影像和康复技术在产后腹直肌分离的评估与治疗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DRA的诊疗提供参考,构建健全有效的现代康复诊疗体系,推动影像与康复技术在DRA中的应用,加快国内外DRA诊疗共识的形成。
1 DRA研究现状
1.1 DRA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孕次、产次、多胎妊娠、年龄、体重指数(BMI)、分娩方式、激素水平、胎儿体重等因素是破坏LA正常生理结构而引发DRA的重要危险因素[4,10-13]。但因纳入研究对象的类型、数量及评估标准不同,在危险因素的研究上又各有分歧。例如Gitta等[10]发现IRD会随年龄、孕次和产次增长(加)而增宽,其中年龄可能是先导因素,同时认为体重的增加、运动减少及腹部脂肪量增加会升高BMI进而导致DRA。Werner等[14]和Sperstad等[15]一致认为托举婴儿(重物)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但因证据不充分仍需进一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LA是由参与形成腹直肌鞘的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腱膜向腹中线移行而成且位于剑突和耻骨联合之间的网状纤维结缔组织,对维持腹部肌肉处于正常解剖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Cavalli等[3]在尸体解剖中发现腹内斜肌的解剖结构变异可能是引起DRA的重要危险因素,此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此外,国内相关研究表明高BMI、孕次和糖尿病是改变肌肉结构和功能、降低腹壁肌肉力量及增大腹壁张力而导致DRA的重要因素,但年龄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16]。Wang等[17]却认为由于无法准确评估腹部脂肪对腹直肌的作用或腹部的脂肪不会增加腹直肌的负荷,提出低BMI的女性更容易出现DRA;另外,邓炳俊等[18]和焦子珊等[19]还提出了阴道前壁脱垂和喂养方式也是诱发DRA的重要危险因素。
1.2 DRA的危害 目前,国内外专家关于DRA的危害研究持有不同的观点。相关研究表明,LA受到过度拉伸会出现腹部肌肉形态结构及功能异常[20],而腹壁肌肉连接腹中线的角度也随之改变,以致肌肉的作力线偏移而产生扭矩能力[10,14],进而影响腹壁肌群维持脊柱的稳定、完成脊柱的屈曲和旋转运动及保护、固定腹腔脏器和维持、增加腹内压等功能。另有研究发现腹部与盆底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其共同生理病理的基础,伴随DRA的发生,除了腹直肌鞘会出现机械损伤,腰-骨盆带疼痛、盆底功能障碍和外观形象等问题也会随之发生[10,21-23]。然而,Bo等[24]研究发现DRA与盆底功能障碍(PFD)、尿失禁(UI)及盆腔脏器脱垂(POP)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随后,相关学者采用超声成像(USI)评估了DRA与PFD、UI和POP之间的关系[25-26],进一步证实了Bo等的结论。有研究表明上腹疝或脐疝可能与DRA同时存在,其原因可能是既往接受过腹部手术[6,27]。
1.3 DRA的评估标准 因人群类型、测量方法、测量部位和判断标准不同[3],从而无法判断IRD增宽至何种程度属于异常,故DRA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者通过总结实验资料提出了相对有价值的评估建议。Sperstad等[15]采用指腹触诊法测量脐上4.5 cm、脐部以及脐下4.5 cm处的IRD,并将其测量结果分成四类:①非病理性DRA为<2指宽;②轻度分离为2~3指宽;③中度分离为3~4指宽;④严重分离为≥4指宽。德国疝学会(DHG)和国际内镜疝学会(IEHS)提出了一种中线切口疝分型标准[2],根据DRA长度(剑突下、上腹、脐部、脐下和耻骨上)和DRA宽度(W1<3 cm,W2=3~5 cm,W3>5 cm)对IRD进行评估,笔者认为此标准更直观且有助于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标准。Reinpold等[2]认为IRD的临界值为2 cm,若两侧腹直肌横向分离超过2 cm,则判定为病理性分离,而Mota等[28]认为该标准会高估DRA的患病率。Qu等[25]建立了DRA的超声诊断标准:①脐下3 cm处IRD>2 mm,②脐部IRD>20 mm,③脐上3 cm处IRD>14 mm。作者基于以上标准将产后DRA分为六类:①脐下分离型,②脐部分离型,③脐上分离型,脐部和脐下分离型(①+②),脐部和脐上分离型(②+③)以及完全分离型(①+②+③)。笔者认为该评估标准所选择的测量部位全面、分类诊断层次清晰,且又有超声的介入增加了该标准的可信度,故有助于实施个性化管理策略,可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和标准化研究。
2 现代影像技术在产后DRA评估中的应用
如前述,国内外学者对病理性DRA的诊断并不统一,因此,实现对DRA的量化诊断是目前研究的热点。相关报道表明,以超声、CT和MRI等为代表的影像评估法广泛应用于DRA的诊断,且有效性和可靠性高[29],其中USI堪称评估DRA的金标准[21]。Hills等[30]研究发现USI具有良好动态适应性且测量精确,可有效避免超声换能器角度变化引起的误差。Joueidi等[21]在研究中发现USI具有可重复性、有效性、可靠性及无创性等优势,可作为诊断DRA的第一选择,但对设备质量和操作员专业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Barbosa等[31]和Water等[32]认为影像评估法是诊断DRA的首选方法,具有精确诊断、筛选及动态监测的优势,但CT和MRI在DRA中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反,修志刚等[33]认为CT能精准监测DRA的范围、形态、腹壁前突程度及腹壁疝等情况,以此来指导制定手术方案和评价术后效果。Wang等[1]研究发现USI的灵敏度高,可准确测量腹直肌间距离和厚度,实现从产前诊断预测到产后康复监测的一站式评估,从而在孕期进行干预,降低产后DRA的风险。此外,瑞典国家指南中还指出USI具有鉴别和筛查脐疝或上腹疝功能[29]。
3 现代康复技术在产后DRA治疗中的应用
迄今为止,对于DRA应采用何种治疗策略尚未达成共识。尽管缺少足够证据证明物理治疗的效应,但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来说,物理疗法可能是最佳的方案[34],同时还可以帮助规避手术风险[7]。
物理治疗主要包括运动训练和电刺激,且其显著的临床效应已得到证实。瑞典国家指南指出腹部核心训练能有效增强腹部核心肌肉的力量,对改善DRA的程度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该指南还建议所有患者均应接受至少6个月的核心训练计划,然后再考虑对其进行手术矫正[29]。Lee等[35]认为腹横肌激活训练在改善腹部肌肉张力和肌肉间力的传递以及防止LA因卷腹所致的变形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从而改善腹壁的外观和腹部肌肉的功能。Michalska等[36]和Depledge等[37]肯定了腹部运动疗法的显著优势,同时建议将卷腹和腹横肌激活训练相结合以发挥其最佳的治疗效应。相关研究也肯定了深层核心稳定运动训练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联合方案能增强腹部肌肉力量和重塑腹部肌肉的功能,从而改善DRA程度及其他相关症状,最终实现临床疗效的最大化[38-39]。
另外,Wei等[40]研究发现电刺激结合腹部肌肉锻炼可增加肌肉收缩强度,进而刺激MMP-2细胞内活性,防止其在骨骼肌中过度表达或增加细胞外对MMP-2的需求,最终达到改善DRA程度的目的。Jacob等[41]研究发现高强度聚焦电磁波(HIFEM)对腹部具有显著的重塑作用,与一般人群相比,HIFEM有助于减少产后妇女腹部分离、脂肪厚度以及增加腹部肌肉质量。有证据表明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结合自主收缩的可增强运动神经元和皮质脊髓兴奋性,从而提供更有效的神经肌肉刺激以改善、恢复肌肉的收缩功能[42]。此外,还有学者一致认为仿生物电刺激有助于产后DRA的恢复、缩小腹围及减轻背部疼痛,故其在产后腹直肌分离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43]。
4 结 语
DRA是妊娠期和产后妇女最常见的一种临床征象,虽有自然消退的可能,但由于个体差异、分离程度不同以及未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治疗,仍有相当部分妇女腹直肌分离状态会持续存在。正因如此,一些诸如腰背痛、盆腔脏器脱垂、二便失禁及腹疝等继发性症状也随之出现,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妇女的生活质量。目前,为了降低腹直肌分离发生的风险及寻找针对性且系统化的管理方案,国内外学者从危险因素、危害性、评估方法和治疗方案等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对于以上研究结论在国内外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我们无法开展规范化的临床诊疗,从而也无法规避诊疗风险。
毫无疑问,共识的形成对临床诊疗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笔者认为全面地认识和控制诱发DRA的危险因素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腹直肌分离的发生率和危害性的前提,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应该联合开展大样本、多种族、多中心以及跨地域的研究,以便使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和统一性,从而有利于开展科普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其次,关于病理性DRA的评估标准仍未作出统一定论,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个体差异、评估部位多样化、所选的评估方法不同及评估操作不规范;除了个体差异以外,笔者认为另外3种原因是具有可控制性:①评估部位的数量在一定意义上可影响评估的准确性,因而我们可以选择以脐为中心的上下对称性的多个部位进行测量研究,从而有助于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在评估部位选择上达成共识;②虽然指腹触诊和超声成像是临床中最常用的DRA评估手段,但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其也是褒贬不一,各有取舍,而笔者认为指腹触诊和超声成像分别是以手指宽度和IRD数值作为评估DRA的指标,且两者之间不具有同质性,故而很难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来确定相对标准化的评估指标;③指腹触诊操作简单、直观,且可及时测量及记录数据,以便被检查者更容易了解自身疾病或功能状况,故可以用于首次筛查;同时,指腹触诊具有简单、易学的特点,有利于患者学习后进行定期的自我评估,通过不断地反馈以增强个体康复治疗意识,最终达到医患协同治疗的目的。再者,超声成像被誉为评估腹直肌分离的金标准,具有可视化、动态实时监测及测量结果精准的优势,因而可在治疗中和治疗后进行精细化地评估,以反馈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及治疗效果。总之,笔者认为应该将指腹触诊和超声成像联合应用于DRA的评估,以最大化提高检测结果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关于干预方案有效性的研究并不统一,电刺激、运动疗法以及两者之间的联合方案都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并在临床治疗中都产生了显著的效应。然而,根据肌肉的力学特性以及临床实践可知,相对于被动干预,主动干预(运动)获得的临床效益可能更高,但该结论需要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